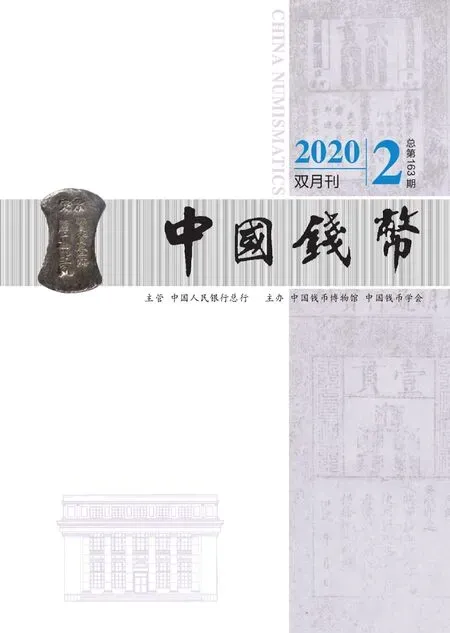《民國黃金檔案》序
(中國錢幣博物館)
戴學文先生《民國黃金檔案》即將出版,我得以先睹為快。不禁想起我與戴先生二十多年的交往,起始是我在《中國錢幣》雜志工作時。一日,收到一篇《云南牌坊錠的公估制度》的投稿,文章實物、文獻資料豐富,論述嚴密,于戳記差異中說清了云南牌坊錠的地域、時代、分型、公估者等諸問題,使我對作者的功底、水平有了深刻的認識。文章發表在1995 年第3 期。其后,又不斷見到戴先生的銀錠著作和文章。如果說開始幾年我們是作者與編者之間的文字交往的話,自我經爭取調到錢幣博物館征集保管部,得到每日半天鉆在地下庫房中整理銀錠等的機會,并逐漸嘗試據實物寫文,就開始了向戴先生的專業靠攏、學習。
進一步的文字之交是我退休之后,我被返聘參與對人民銀行歷年收兌的金銀錠的整理工作。四五年的時間奔波于多處庫房,面對成千上萬的金銀錠,先是將一枚枚錠子測量、登錄、拍照、建檔,后是出版了《中國銀錠圖錄》一書;接下來我在試圖編寫《中國金錠圖錄》一書的圖錄部分時,才倍感艱難。與銀錠書編撰不同,中國歷代金錠幾乎沒有一本圖錄或綜述的專著,面對大量金錠(絕大部分是民國金錠)如何建立一個中國金錠的框架體系,如何將幾萬枚金錠斷代、分型分類、排序、挑選適合者,并各就其位,這不是金錠圖片的簡單堆砌所能解決的,使我費盡思量。而此一階段戴學文先生正好也把關注點放到了民國金錠這片尚待耕耘的“土地”之上,我得以閱讀他的相關文章,并常向他通過郵件請教、討論,以后學者的身份與他成為了“同道”。他后來出的幾本民國金錠書,我自認為是最認真的讀者,字字讀來,受益良多。
近日讀他的《民國黃金檔案》,比之《你所不知道的國府黃金》,我能體會他又豐富了哪些內容,又解決了哪些問題,來之不易的又是哪些材料!
說說新書的引人注目之處。
民國初年黃金貨幣的興起,原因何在?戴先生把視野放在了國際錢幣的變局上,放在了中國傳統銀兩貨幣的困境上。19 世紀后期,各國紛紛實行金本位制,并拋售白銀,造成世界銀價的不斷下跌。在中外商貿交易中,中國處于不利地位,加之大量的借款、賠款,被要求還款時白銀轉換為各國指定的貨幣,更加重了中國的負擔。這是造成黃金貨幣在國內興起的一個很大推動力。
史料和資料的挖掘是錢幣研究的基礎,戴學文先生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別是他辛苦查找到近年臺灣解禁的國發會檔案管理局中的《中央造幣廠檔》等資料,解決廓清了許多以前懸而未決的問題。如中央造幣廠上海分廠自1948 年11 月17 日至1949 年2 月5 日制成與解送的金條,明確了上海廠廠條制作的時間、品種、數量,甚至使我們確知了上海廠制作過400 兩的金錠;又如中央造幣廠成都分廠1949 年8—10 月熔解金錠月報表,也提供了原資料極少的成都分廠,不為人知的3 個月中制作廠條的種類和數量。
民國黃金貨幣的一大特色是出現了一大批官方造幣廠制作的金錠—廠條,并在民間使用。廠條的制作分為四個時期:重慶(昆明)時期、上海時期、成都(重慶)時期、臺灣時期。成都時期制作時間短,制作數量少,因戰亂而留存資料少,一般人很少了解這段歷史及此時期制作的廠條;至于臺灣時期廠條由于海峽的阻隔,我們所知實物及文字資料不多,所以也多有模糊不清處。《民國黃金檔案》系統解說了這兩段歷史和相關廠條的種類,讀來使人對民國廠條有了系統完整的概念。
捧書閱讀中也感到解決了我過去的一些疑惑之處,以往有的地方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得以豁然而解。比如民國政府以兩億美元向美國購買黃金,記錄中卻還有之前兩千萬美元購金的交易,讀此書才得知:這筆交易是中國協議出口美國滇錫4 萬噸換取的,購金撥款由5 億美元中列支,購得的黃金分批運到中國。再如,1946 年初的一波黃金行市上漲,原因曾被提及是東北游資入滬炒金所致,見到書中第四章第一節注1 說明,才知炒金操作情況,據1946 年1 月8 日重慶《大公報》:“黃金價格連日上漲,關系由于陸續出關所致。每兩黃金出關私售,價值二萬偽滿幣,再易黑市法幣,可得十八萬元。故有力者已趨之若鶩,以此法幣攜至關內,可獲利一倍以上。”又如,1946 年3 月至1947 年2 月,民國政府通過中央銀行在上海發售黃金回收紙幣,所售黃金是中央銀行委托上海金號銀樓制作,但有些文章卻認為此段售出的是中央造幣廠上海分廠制作的廠條。讀此書才知當時民國財政部與中央銀行的意見相左,意圖推動由中央造幣廠來制作金錠,有人是見到財政部的文件才造成誤判。書中理清了此段的頭緒,明確了此一年左右時間發售的是交由金業同業公會理事長同豐余詹蓮生經辦改鑄的十兩烚赤金條。
總之,《民國黃金檔案》是我目前見到的論述民國黃金貨幣最系統、包含資料最豐富、且思慮嚴謹的一本書。也許今后隨著實物、文字資料的繼續發現,民國黃金檔案的內容還會進一步推進,民間黃金貨幣的內容也會進一步豐富,但是《民國黃金檔案》已為我們展示出了民國黃金的基本格局,解決了大多數的疑難。
所以,這本書值得一讀,也值得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