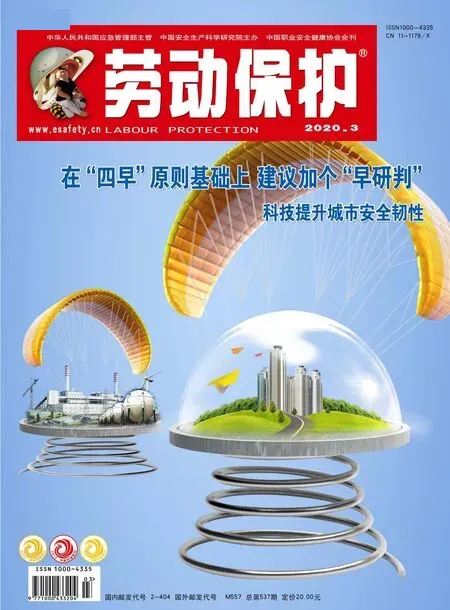非正規就業工傷保險解綁勞動關系 “現實很骨感”
文/王天玉
工傷保險到底是不是應該和勞動關系解綁,我認為應審視工傷保險制度的基礎和制度結構,分析工傷保險到底是否應該以及是否有能力承擔這一重任。
第一是保險針對的風險類型。工傷保險是典型的團體險,其以勞動關系為前提是因為勞動者對用人單位的從屬性,也就是說,勞動者自主性受到限制,在工作時間、地點和內容上受用人單位指揮監督,因此用人單位負有對勞動者的保護義務。在工傷保險制度確立之前,西方工業化過程中的職業風險分配經歷了勞動者自擔風險、雇主損害賠償責任的不同階段。雇主損害賠償責任作為一種民事責任,存在救濟成本高、程序時間長、雇主能力不足等問題,因此通過風險分配社會化的方式,以工傷保險替代了雇主責任。本質上說,工傷保險是雇主損害賠償責任的社會化產物,這也是工傷保險僅由用人單位繳費的根據。而以互聯網平臺用工為代表的非正規就業與勞動關系相異較大,難以契合工傷保險作為團體險的制度機理。
第二是工傷保險基金財務穩定方面。有觀點以德國為例,提出德國沒有固定勞動關系的人員也能享受工傷保險。對此,我們應當看到在世界范圍內,德國幾乎是獨樹一幟的特例,絕大多數實行工傷保險制度的國家沒有仿照德國,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德國社會保險制度的發達與完備。一方面,德國醫療保險制度非常發達,醫療保險已經把一部分工傷保險的問題解決了。另一方面,德國的職業安全標準實施規范性很好,工傷事故率低,以致工傷保險基金儲備充足。因此,德國學者甚至發明了一個概念:非真正保險責任,即不是以勞動關系為前提,將志愿者、學生等人員也納入進來。這是一個政策選擇,法理上很難說得通,就是因為資金非常充足,才能讓保障發揮更多社會效益。而我們的工傷保險是不是要和勞動關系解綁,涉及的最大問題就是工傷保險基金財務穩定的問題,有勞動關系就意味著要讓單位繳納工傷保險費用。如果不繳納保險費用,財務穩定從何而來?至少從現在的情況看,在很大范圍內工傷保險不能和勞動關系解綁。
第三是在制度設計方面,如何在沒有勞動關系情況下給這些勞動者提供職業傷害保障。參照我國臺灣地區的做法,自營業者通過工會強制納保,政府給補貼40%。這種做法主要難點在于政府補貼哪些人?補貼多少才合適?這也是財務可持續的問題。那么,我們需要分析一下非正規就業中最典型的平臺用工現狀。根據2018 年的統計數據,全國共享經濟服務提供者有7 000萬。這個數字不能等同于實際提供勞務的人,比如僅提供房屋用于共享經濟服務的不是實際提供勞務的人,但也屬于共享經濟服務提供者。因此這個數據涵蓋的范圍比實際勞動者大得多。進行這樣一個制度設計需要大量的前期工作,要以統計和精算為基礎。
因此我認為,要尊重現有的制度框架,不能用改變整體來解決局部問題。應制定一個相對獨立的依附于現有工傷保險制度框架下的新興業態從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制度,仍然由政府來主導,區別于商業保險。此類職業傷害保障針對的風險目前還是以交通事故為主,以現在的實際情況也難一步保障到位,但應針對最需要解決的、最急迫的情況先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