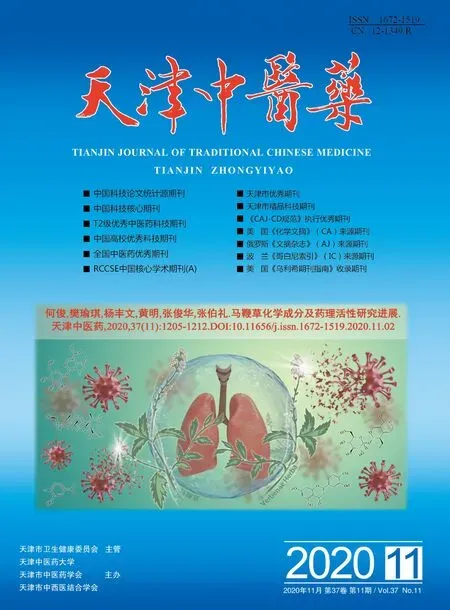三陰性乳腺癌的免疫治療研究進展*
趙偉鵬,孫琳琳,佟仲生
(天津醫科大學腫瘤醫院乳腺內科,國家腫瘤臨床醫學研究中心,乳腺癌防治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天津 300060)
三陰性乳腺癌(TNBC)作為乳腺癌的一種獨立臨床病理類型,占乳腺癌的12%~17%,其腫瘤細胞表面缺乏雌激素受體-α(ER-α)、孕激素受體(PR)及人表皮生長因子受體2(HER-2)等可用于治療特異性表面標志。TNBC相比其他的乳腺癌亞型,TNBC患者具有總生存期短、惡性程度高、侵襲能力強、早期復發率高等臨床特征[1]。TNBC因缺乏靶向性的藥物,抗內分泌和抗HER-2治療無效,化療仍是目前TNBC治療的主要方式,但臨床僅有部分化療敏感的TNBC(<18%)患者可從化療中獲益,其中仍有30%左右患者出現原發性或繼發性的耐藥[2-3]。在過去10年乳腺癌綜合治療取得了重要進展,美國國家綜合癌癥網絡(NCCN)指南不斷更新相關治療進展,隨著免疫治療的時代來臨,可能為改善TNBC患者的預后提供新的選擇[4]。目前研究者針對TNBC的免疫治療前景展開了大量的臨床試驗,見表1。
1 TNBC與免疫微環境
近代經典腫瘤免疫理論認為,腫瘤細胞表面抗原可以被抗原遞呈細胞識別,從而活化效應性T細胞,激發機體產生免疫反應,達到清除腫瘤細胞的效果。激活的效應T細胞可以直接殺傷腫瘤細胞,可以通過分泌細胞因子誘導腫瘤細胞和基質細胞凋亡,同時可以趨化巨噬細胞實現非特異性免疫殺傷。但腫瘤細胞與腫瘤免疫微環境相互作用后表面可識別的腫瘤抗原和MHC-Ⅱ類分子逐漸減少或缺失,逃避免疫系統的殺傷,從而有利于腫瘤細胞的生長與轉移,其中免疫抑制性細胞和分子如調節性T 細胞(Treg)、髓源性抑制細胞(MDSCs)、腫瘤相關巨噬細胞和白細胞介素-6(IL-6)等在這個過程中也起到相當重要的作用[5-6]。因此,促進抗原呈遞細胞(APCs)的抗原呈遞功能、T細胞的抗腫瘤效應以及抑制腫瘤相關的免疫抑制因素是免疫治療的主要策略。
MDSCs以Gr1和CD11b的表達為特征,是機體免疫耐受的主要細胞,可以通過多種途徑抑制機體的獲得性和天然性抗腫瘤免疫,使腫瘤細胞逃避機體的免疫監視和攻擊,促進腫瘤進展[7-8]。目前研究提示,荷瘤動物和患者的MDSCs從骨髓移出,被腫瘤細胞招募到周邊血、脾、淋巴結核腫瘤組織,MDSCs通過直接結合腫瘤內皮細胞,通過抑制淋巴細胞增殖、促進其凋亡,并其干擾素-γ(INF-γ)分泌、促進轉化生長因子(TGF)、白細胞介素-10(IL-10)釋放等,達到抑制先天適應性免疫的效果。而腫瘤患者血液循環中MDSs增加,與TNBC臨床腫瘤分期和轉移性腫瘤負荷有關[9]。近期研究發現MDSCs與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療效呈負相關,并由此推測MDSCs在免疫抑制性腫瘤微環境中的主導作用可能是導致免疫檢查點抑制劑耐藥的主要原因[10-12]。因此,以MDSCs為靶點并聯合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有可能成為逆轉免疫抑制性腫瘤微環境的有效策略。

表1 三陰性乳腺癌免疫治療的臨床試驗Tab.1 Clinical trial of immunotherapy for 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
乳腺癌與免疫治療相關的靶標是由于腫瘤浸潤淋巴細胞(TIL)的關聯,研究證實TILs存在于乳腺癌的所有分子亞型中,但以三陰性和HER2過表達型最為常見[13-14]。目前研究熱點在于高水平的TILs預示著新輔助化療后的病理完全應答(pCR)。德國1項納入3 771例接受新輔助化療的原發性乳腺癌患者的研究證實在所有乳腺癌分子亞型中,TILs水平是新輔助化療后pCR的預測因子并與之呈正相關。在所有納入的乳腺癌患者中,相較于低水平TILs組(0%~10%)的乳腺癌患者,中等水平(11%~59%)和高水平TILs(≥60%)組患者的pCR率分別增加7%和 24%,差異具有明顯的統計學意義(P<0.000 1)。在三陰性乳腺癌患者中也觀察到相同的趨勢,高水平TILs組的三陰性乳腺癌患者較低水平TILs組患者的pCR率增加19%[14]。此外TILs具有預后價值,TILs數目的增加提示患者預后較好。ECOP的E2197&E1199試驗入選481 TNBC患者進行10.6年隨訪,發現 iTILs(瘤內)密度 80%,sTILs(間質)密度15%,sTILs每增加10%,死亡或復發風險下降14%(P=0.002);遠處復發風險下降 18%(P=0.04)[15]。一項納入139例早期TNBC患者的研究顯示在不考慮輔助化療影響的情況下,以50%為臨界值進行二分層時,TILs是TNBC患者無病生存的有力預測因子(P=0.01)[16]。
2 TNBC與腫瘤疫苗
腫瘤疫苗指自體或異體腫瘤細胞或其提取物,經過反復凍融或輻照后失去致瘤性,但仍包含腫瘤特異性抗原(TSA)或腫瘤相關抗原(TAA),可以誘導機體產生針對腫瘤細胞的體液免疫或細胞免疫,抑制腫瘤的生長、擴散及復發。
多肽疫苗治療是根據自身存在的主動免疫為不同患者選擇不同多肽并觸發針對癌細胞的免疫反應。研究發現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GFR)家族和胰島素樣生長因子(IGF-1R)肽模擬物/雙靶向疫苗的組合,在TNBC細胞系和腫瘤患者中顯示具有抗腫瘤效果。Takahashi等[17]在18例多肽治療轉移復發性三陰性乳腺癌(mrTNBC)患者的單臂Ⅱ期試驗研究中發現,接種疫苗后的患者觀察到細胞毒性T淋巴細胞(CTL)和/或免疫球蛋白G(IgG)反應的升高。Clifton等[18]報告的一項Ⅱb期隨機試驗的結果顯示,一種靶向HER2的肽疫苗—Nelipepimut-S(NPS)與曲妥珠單抗聯合使用是安全的。但是,在TNBC患者中觀察到了顯著的臨床獲益。與對照組相比(安慰劑聯合粒細胞-巨噬細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NPS組(NPS聯合 GM-CSF)的 DFS有所改善(HR=0.26,95%CI:0.08~0.81,P=0.01)。1 項納入14例化療無效的mTNBC的Ⅱ期臨床試驗顯示疫苗誘導的免疫增強是一個有利的預后因素,在給予患者多肽疫苗單藥治療后,中位IgG滴度較高組患者的中位OS明顯高于中位IgG滴度較低組患者的中位 OS(P<0.01)[19]。
樹突狀細胞(DC)是一種骨髓來源的抗原提呈細胞(APC),它在誘導和調控免疫反應中發揮重要作用。在腫瘤疫苗的研究中,DC常作為一種天然佐劑來誘導腫瘤抗原特異性效應和記憶性細胞。腫瘤DC疫苗可分為腫瘤抗原肽負載的DC腫瘤疫苗、基因修飾的DC腫瘤疫苗和腫瘤全細胞抗原負載的DC腫瘤疫苗,TNBC免疫治療相關的腫瘤疫苗主要為基因修飾的DC腫瘤疫苗和腫瘤全細胞抗原負載的DC腫瘤疫苗。腫瘤患者體內DC細胞受化療等因素影響,其數量減少,MHC分子表達下降,降低了其抗原遞呈能力,同源異體功能活性正常的DC進行融合疫苗[20-21]。Tomasicchio等[22]在體外使用自體乳腺癌細胞作為“靶細胞”,測試了DC疫苗對自身腫瘤細胞的體外效果。DC疫苗能誘導強大的、劑量依賴性的抗原特異性細胞毒性T淋巴細胞反應(65%),其對自體乳腺癌細胞具有殺傷作用(P<0.005)。Zhang等[23]采用 MDA-MB-231 荷瘤模型,與對照組相比DC-腫瘤融合疫苗可以更好地刺激同種異體T淋巴細胞的增殖,促進乳腺癌細胞凋亡,體外引發有效的特異性抗腫瘤T細胞反應。
據既往研究發現,T細胞對腫瘤新抗原的識別在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治療中起著重要的作用,腫瘤新抗原的負荷與帕博利珠單抗的反應有關,提示疫苗和免疫檢查點抑制劑聯合治療可能是有效的[24]。Kodumudi等[25]采用臨床前模型探索了DC瘤苗序貫抗PD-1治療在HER2陽性乳腺癌中的療效。結果顯示,與對照組小鼠相比,聯合治療顯著延緩了實驗組小鼠瘤體的生長,并改善了生存率(P<0.01)。
3 TNBC與免疫檢查點藥物
腫瘤細胞可以過表達免疫檢查點相關分子,抑制T細胞活性從而逃脫機體的免疫反應而存活。免疫檢查點抑制劑(ICB)可以抑制免疫檢查點分子的活性從而釋放T細胞的活性,恢復對腫瘤細胞的殺傷作用達到抗腫瘤的目的。目前主要有CTLA-4受體抑制劑和PD-1/PD-L1抑制劑兩類。腫瘤細胞以及腫瘤周圍的免疫細胞上表達PD-L1,說明原來發生過抗腫瘤的免疫反應。腫瘤細胞微環境的細胞高表達 PD-L1、CTLA-4、TIM-3、IDO 等免疫抑制分子,就是腫瘤細胞免疫逃逸的機制之一[26-27]。PD-L1和CTLA4是分別在T細胞激活的起始和效應階段的抗原呈遞細胞表面上表達的免疫檢查點。乳腺癌約50%的PD-L1跨膜蛋白,以雄激素受體(AR)陰性多見,TNBC細胞表達PD-L1,其受體是PD-1,并且還結合PD-L2作為其它配體,同時表達CTLA4。這兩者都可能共同表達PIK3A和PTEN,這可能允許雙重阻斷這些途徑的機會更有效的腫瘤反應[26-28]。顯示PD-L1上調在基底乳腺癌中更常見,并且與更高的T細胞細胞毒性免疫應答有關。PD-L1上調與更好地生存和化療反應相關。PD-L1抑制劑對非活性TIL的再激活提示PD-L1上調可能為乳腺癌有希望的策略[29]。
阿特珠單抗是第1個獲得美國FDA批準的ICB用于治療PD-L1陽性轉移性三陰性乳腺癌(TNBC)。目前PD-1/PD-L1阻滯劑仍是TNBC免疫治療的研究熱點,初步研究顯示單一抗體的亦可有效性,以及與其他化療藥物(例如白蛋白紫杉醇)均顯示良好的效果,且在早期和晚期三陰性乳腺癌中均取得了很好的療效。在Ⅱ期KEYNOTE-086研究中,研究者分別對單藥帕博利珠單抗在PD-L1陽性轉移性TNBC(mTNBC)患者的一線和后線(二線及以上)治療中的作用進行了評估。B隊列共納入了84例未接受過系統治療的轉移性TNBC患者(患者腫瘤PD-L1的CPS評分≥1),結果顯示單藥帕博利珠單抗治療PD-L1陽性mTNBC患者的ORR為21.4%,沒有患者出現4級不良事件,單藥帕博利珠單抗具有可控的安全性,并顯示出持久的抗腫瘤活性[30]。隊列A共納入了170例既往接受過一線及以上的系統治療的mTNBC患者(61.8%患者的腫瘤呈PD-L1陽性),結果顯示在所有納入的患者中,ORR為 5.3%,在 PD-L1 陽性患者中,ORR 為 5.7%,并且有12.9%的患者出現了3或4級的不良事件。與A組患者相比,B組患者對帕博利珠單抗的反應較好。綜上所述,對于mTNBC的患者來說,尤其是PD-L1陽性的患者,早期使用帕博利珠單抗可以明顯提高藥物的反應率[31]。
幾種常用于乳腺癌的化療藥物可以促進免疫原性細胞死亡,從而釋放腫瘤細胞抗原,促進免疫應答[32]。因此化療藥物聯合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可能取得較好的治療效果。Schmid等[33]在Ⅲ期KEYNOTE-522研究中發現在早期TNBC患者中,接受帕博利珠單抗聯合新輔助化療的患者的pCR明顯高于安慰劑聯合新輔助化療組(P<0.001)。在初始Ⅰ期試驗中,MPDL3280A試驗中,PD-L1抗體在接受過多次治療的TNBC患者仍顯示出一定的效果。在復發轉移性TNBC患者中,與白蛋白紫杉醇聯用,客觀反應率為66.7%,同時該研究提示PD-L1表達狀態與PD-L1抗體治療效果無明顯相關性。在另一項Ⅱ期研究中,采用在第二和第三線治療方案與PD-L1抗體聯合使用,也顯示出良好的反應率。同時毒性曲線和藥物耐受性是可以被接受的[34]。在IMpassion130試驗中(Ⅲ期臨床試驗),研究者發現在PD-L1陽性的晚期TNBC患者中,相對于安慰劑聯合白蛋白紫杉醇組,阿特珠單抗聯合白蛋白紫杉醇組患者的PFS延長(P<0.001),且未發現新的不良反應[35]。2020 年ASCO公布的ENHANCE 1研究(摘要號:1015)探討了艾立布林聯合帕博利珠單抗的效果。截止到目前為止,該研究納入了167例轉移性TNBC患者,分為一線治療組(66例)和后線治療組(101例)。結果顯示總體ORR為23.4%,相對于PD-L1陰性患者,PD-L1陽性患者使用該聯合治療的效果更佳,但此種趨勢僅見于一線治療患者。對于mTNBC患者,艾立布林聯合ICB效果比單藥治療效果更好,尤其對于PD-L1陽性患者,早期使用可以明顯改善ORR。
除聯合化療之外,ICB聯合局部治療也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在一項單臂Ⅱ期試驗中,McArthur等[36]發現帕博利珠單抗聯合放療在轉移性TNBC患者中是可以耐受的,且3/9(33%)的患者在治療后顯示出持久的抗腫瘤反應。PARP抑制劑可以阻斷DNA修復途徑,促使胞質游離DNA增高,激活cGAS/STING通路,誘導抗腫瘤免疫反應,揭示了PARP抑制劑聯合ICB的可能性。臨床前模型顯示PARP抑制劑聯合ICB可以增強效應T細胞的功能[37-38]。1項單臂Ⅱ期臨床試驗共納入了55例晚期或轉移性TNBC患者,其中15例患者攜帶突變的BRCA基因,給予所有患者口服尼拉帕利聯合靜脈使用帕博利珠單抗。結果顯示在可評估的47例患者中,ORR為21%,DCR為49%;在15例攜帶BRCA突變基因的患者中,ORR為47%,DCR為80%,中位PFS為8.3個月;在27例攜帶野生型BRCA基因的患者中,ORR為11%,DCR為33%,中位PFS為2.1個月。尼拉帕利和帕博利珠單抗聯合應用在晚期或轉移性TNBC患者中具有很好的抗腫瘤活性,在腫瘤BRCA突變患者中有較高的應答率[39]。
4 TNBC與細胞因子類藥物
白細胞介素(IL)治療是有效的方式之一,大劑量IL免疫治療被證明在癌癥如黑素瘤中發揮關鍵性作用。TNBC的生長也依賴于ILs的炎癥信號傳導和產生。用于治療類風濕性關節炎的IL-1β受體拮抗劑在與局部晚期TNBC中的化療,與樹突細胞疫苗聯合的試驗研究表明,IL可以提高腫瘤疫苗及化療患者的療效,其機制可能是阻斷IL-6/JAK/Stat通路發揮作用[40-41]。另外,IL-6和IL-8表達的同時抑制TNBC體外的集落形成和細胞存活,同時抑制體內移植瘤的生長。患者標本的Cox多變量分析顯示IL-6和IL-8表達預測患者存活時間,可能作為獨立的預后預測因子。這些發現一起為IL-6/IL-8信號傳導的雙重抑制提供了理論依據,作為增強TNBC的免疫治療策略[42]。Qian等[43]發現IL-17在TNBC(非特殊類型)腫瘤內外的基質細胞中過度表達,另外,腫瘤內IL-17陽性細胞與腫瘤細胞血管內皮生長因子A(VEGFA)表達及腫瘤內微血管密度(MVD)呈正相關,且腫瘤內IL-17陽性的細胞是預測不良PFS的獨立預后因素。
5 TNBC與過繼細胞療法
過繼性免疫細胞治療(ACT),是指從腫瘤患者體內分離免疫活性細胞,在體外進行擴增和功能鑒定,然后向患者回輸,從而達到直接殺傷腫瘤或激發機體的免疫應答達到殺傷腫瘤細胞的目的。過繼細胞療法分為非特異性細胞治療[如細胞因子誘導的殺傷細胞(CIK),淋巴因自己活得殺傷細胞(LAK),樹突狀細胞(DC)、自熱殺傷細胞(NK)等]和特異性細胞治療[如融合抗原受體(CAR-T)],目前尚無研究證明非特異性的細胞治療對腫瘤有明確的療效。過繼性細胞免疫研究已經發展為通過基因工程技術使普通T細胞具有抗腫瘤活性。將具有高度親和力的腫瘤特異性的T細胞受體(TCR)基因通過反轉錄病毒等載體導入普通T細胞中。另一種方式是融合抗原受體(CAR)表達CAR的T細胞可以通過主要組織相容性復合體(MHC)非限制性的途徑與抗原結合。實驗動物和臨床試驗顯示,增強了抗原呈遞功能鑒于其以癌癥為中心的過表達,FRα一直是針對性的藥物傳播候選人結合FRα的葉酸綴合的治療化合物或鼠,嵌合和人源化單克隆抗體體或共軛體內的單體(mAb)克隆,T細胞和刺激性細胞因子惡性組織。另外,轉基因的T細胞以嵌合抗原受體(CAR)特異性重定向對于FRα是一個有吸引力的技術,正在積極地進行調查。CAR方法結合了具有T細胞能力的抗體的抗原特異性介導在單次融合中殺死腫瘤細胞,CAR修飾的T細胞主動和具體靶向它們具有指定的抗原并具有持續的能力記憶細胞在體內。因此,CAR修改T靶向腫瘤相關抗原(TAAs)的細胞,如作為FRα,可能比mAb在產生中更有效持久的腫瘤反應。FRα具有細胞內CD27共刺激的特異性CAR信號結構域并評估其療效T細胞被轉導以表達該CAR,人類TNBC移植模型。該研究提示,如TNBC細胞過表達表面FRα蛋白,FRα-特異性CAR-T細胞具有抑制人類的能力TNBC在體內的生長和更強的腫瘤反應[44]。Zhou等[45]使用臨床前模型證實CAR-T可以溶解腫瘤細胞,在體內和體外均能有效地抑制TNBC腫瘤的生長,阻斷PD-1信號轉導可促進CAR-T細胞在體外殺傷腫瘤。目前CAR-T細胞治療仍主要處于臨床前研究階段,可能為TNBC治療提供新的選擇。
6 TNBC與中藥免疫治療
針對三陰性乳腺癌治療的新靶點,除了熱門的免疫治療外,中醫藥的發展也很好地填補了三陰性乳腺癌目前的治療空缺。既往研究證實在乳腺癌治療的不同階段給予中藥干預,可以改善患者的免疫狀態,降低復發轉移率,延長生存期[46]。楊陽等[47]探討了中藥對腫瘤相關調節性T細胞的作用及機制。研究發現中藥可以減少調節性T細胞的數量或比例、降低調節性T細胞的活性并抑制其功能,解除免疫抑制,促進免疫應答,增強機體抗腫瘤活性,抑制腫瘤生長,改善患者預后。中藥還可以通過促進樹突狀細胞成熟,增強自然殺傷細胞的毒性,促進淋巴細胞增殖活化等起到抗腫瘤的作用。因此,中藥聯合免疫治療很有可能在未來成為TNBC新的治療策略。
目前實現乳腺癌的免疫治療還存在一些障礙。首先,目前還缺乏完善與統一的評價指標,治療早期缺乏有意義的分子標志物,因免疫治療的療效較傳統治療出現延遲,而最終的療效評價無法完全適用現行的評價系統。MHC限制性、抗原免疫原性低、腫瘤的異質性以及腫瘤微環境中的免疫抑制因素等都限制了乳腺癌免疫治療的效果。目前的免疫治療研究大多集中于局部晚期或轉移性乳腺癌的研究,如果早期乳腺癌患者也能從中受益,那么很可能將從根本上改變目前乳腺癌治療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