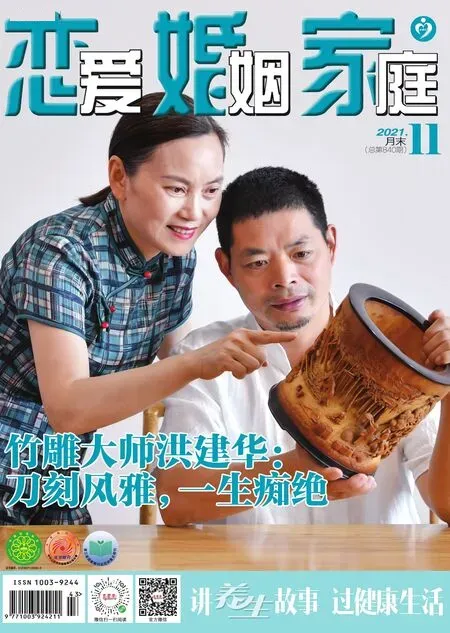我國歷史上的分餐制
◎文/孫繼蘭

今年的這場疫情,帶給人們很多警示與思考,它改變了很多人的工作、學習方式,也促進了很多業務的發展,而與飲食關聯緊密的分餐制,也被大力提倡,成為“舌尖上的新風尚”。
什么是分餐制呢?說白了就是各吃各的。雖然聚餐一直是中國傳統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從歷史上看,我國最早實行的是分餐制,甚至比西方還要早。
商周時期的分餐,是對層級地位的彰顯
我國早在商周時期,就出現了分餐的形式。但其顯著的特征是對層級地位的彰顯,是一種禮制。如周天子需“九鼎八簋”,諸侯為“七鼎六簋”等,它們共同營造出嚴整的氛圍,秩序井然。
到了春秋戰國、秦漢及三國時期,分餐制依然繼續,尊卑觀念及進餐禮儀,依舊蘊含在宴席的程序里。《禮記》中“夫禮之初,始諸飲食”的教義,人們也一直在遵守。在許多關于那些歷史時期的壁畫上,都描繪著賓客“一人一案”的情景。
戰國時的孟嘗君,就用這種方式宴請八方來客。關于他的故事傳記中,有這么一件與分餐有關的事。他的一位門客,有一回覺得自己的“伙食”比別人的檔次差,認為自己受到羞辱。孟嘗君得知此事后,便將自己的食物拿給他過目。這位門客發現,主公的飲食同自己的飲食,分明是差不多的。后來,這位門客竟因羞愧而自殺……雖然這有些極端,但這個故事也說明了那時分餐制之普遍。
比起商周時,春秋戰國至三國時期的宴會規矩,略微松動了一些,融入了一些表演活動。如《三國演義》中,周瑜在群英會上舞劍的情節、曹操在銅雀臺設宴時的“橫槊賦詩”,當屬著名的宴會“節目”。
隋唐至五代十國,具有合餐氣氛的分餐
自魏晉南北朝始,人們的用餐方式順遂社會演變,出現了較顯著的改觀。這一時期,戰亂引發民族融合,游牧文化風習漸傳至中原。游牧民族圍坐聚合、共進酒食的合餐形式,沖擊了中原飲食禮制。中華飲食文明混入北方民族血液基因,形式變得多元化,禮制更有松散傾向。
隋唐直至五代十國時期,合餐的趨勢更為明顯。大家圍坐飲食,但食物還是彼此分明,餐具也是成套分配,令人想到日本的“定食”。
這種具有合餐氣氛的分餐形式,其實是現今最值得恢復的形式。這樣做,合餐的氣氛能夠保持,又保證了分餐制的衛生標準。
宋代出現鐵鍋,合餐趨勢愈發明顯
到了宋代,合餐進一步定型,這與當時市民經濟發達有關。兩宋的都城,飲食行當極其豐富,菜品繁多、品相細膩。各品類的酒樓、食肆也不可勝數,食客很多。
當時,合餐趨勢愈發明顯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一項不得不提,宋代出現了鐵鍋。耐用結實的鐵鍋,增添了菜品的豐富性,催生了“花式炒菜”,再加上那時食物原材料的種類極其豐富,比如植物油和各類從西域引入的蔬菜,都加強了美食的豐富性,因而合餐的形式更為普遍。
當時,北方民間還出現了一種負責統籌宴會節奏、安排席間次序的職業——“白席人”,這恰恰是合餐制的產物。《東京夢華錄》中,就出現過關于這類職業的描寫。
元代時,合餐制的典型用餐方式——火鍋,愈加深入人心。時至今日,火鍋仍然是不少國人的心頭好。
明清時期,合餐制基本取代了分餐制
到了明朝,市井文化發展更為迅速,雖依然存留分餐制,但民間的合餐制,早就形成了規模。背景設置為明末清初的《紅樓夢》,其中描繪的賈府大宴上,就有眾賓團宴的場面。
清代時,合食共餐愈發成了一件尋常事。單獨桌椅的普及,清朝統治者的特定民族習慣……許多原因,都促進了合餐制的深入鞏固。
合餐為病菌擴散打開了方便之門
“混用碗筷、近距離合餐,為病菌擴散打開了方便之門。”解放軍總醫院第八醫學中心營養科主任左小霞說,除了新冠病毒和非典病毒,常見的還有以下幾種。
導致多種消化系統疾病的幽門螺桿菌,主要通過唾液傳染,以合餐為主的中國是高感染率國家;
甲型肝炎和戊型肝炎的肝炎病毒主要通過糞- 口傳播,被病毒污染過的餐具可能引發傳染;
嚴重威脅兒童健康的手足口病,也是由一種腸道病毒通過唾液、飛沫等傳播而引發的,與手足口病人合餐極易被傳染;
流感病毒、麻疹病毒、結核桿菌等也可能在合餐過程中傳染。
分餐讓疾病感染率降低25 個百分點
有研究顯示,分餐制能使疾病的感染率由合餐制的42%降為17%。
近日,杭州市疾控中心的一項實驗顯示,不使用公筷食用涼拌黃瓜的菌落總數,是使用公筷的近3 倍(對比方式下同);干鍋茶樹菇組的菌落總數是17 倍;炒蘆筍組為近18 倍;咸菜炒八爪魚組更是高達250 倍。
專家表示,不使用公筷會把自身口鼻腔攜帶的細菌通過筷子傳到菜上,同時也會導致不同菜品本身攜帶細菌的交叉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