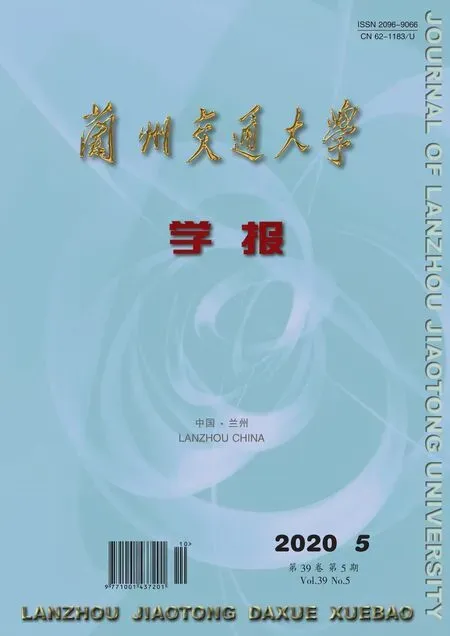深埋隧洞穿越破碎帶誘發(fā)圍巖變形特征
周吉學
(1. 武漢理工大學 土木工程與建筑學院,武漢 430070;2. 中鐵二十局集團有限公司,西安 710016)
在國家“一帶一路”戰(zhàn)略的引領下,我國公共交通建設持續(xù)發(fā)力,打通絲綢之路建立高速鐵路網(wǎng)向西延伸將成為必然,沿線必將經(jīng)過青藏高原和新疆地區(qū),將面臨海拔高、地勢起伏大、地質(zhì)條件復雜的挑戰(zhàn)與考驗.在此區(qū)域修建高鐵,所面對越嶺隧道的占比大,且多為大埋深、穿越不良地質(zhì)帶的長大隧道,施工過程中將對圍巖的穩(wěn)定性控制提出重大挑戰(zhàn).
以往施工中,此類復雜地質(zhì)條件下的大埋深長大隧道常遇到斷層破碎帶,對施工影響巨大.如世界著名的Tauem隧道和Arlberg隧道(奧地利),以及Enasan隧道(日本)等,在開挖過程中都遇到過類似問題.我國近年來隧道開挖中也常遇到斷層破碎帶問題[1-2].宋瑞剛等[3]認為破碎帶圍巖的突發(fā)失穩(wěn)與幾何-力學參數(shù)和綜合剛度比相關.
在隧道開挖變形計算方面,房倩等[4]通過收集整理大量山嶺隧道變形監(jiān)測數(shù)據(jù),統(tǒng)計分析了圍巖變形量、圍巖變形穩(wěn)定時間與圍巖級別、隧道開挖面積等因素之間的關系,提出了不同圍巖級別下,隧道變形的建議控制值以及變形穩(wěn)定時間參考值.Lisjak等[5]基于對Mont Terri地下巖體實驗室的變形監(jiān)測數(shù)據(jù)分析認為,巖體層狀特性對其近區(qū)變形特性有極大影響.Moffat等[6]則基于光纖光柵設備對巷道軸向應變變化與分布規(guī)律進行了研究.
縱剖面變形分布計算方法方面,張常光等[7]研究認為,相比支護力系數(shù)法,位移釋放系數(shù)式法適用范圍更廣,可以考慮多種因素對隧道開挖面空間效應的影響.Alejano等[8]基于理想彈塑性假定,對一定GSI(geological strength index)范圍內(nèi)的巖體進行數(shù)值分析計算,并提出一種簡化的圍巖塑性區(qū)半徑計算公式,用以優(yōu)化應變軟化巖體縱斷面變形分布計算方法.Vlachopoulos等[9]則基于對最終徑向塑性位移計算方法的進一步研究,對圍巖縱剖面變形能分析計算進行了優(yōu)化.
蘇道振等[10]對小盤嶺隧道進出口段多個監(jiān)測斷面進行現(xiàn)場試驗研究,結果表明隧道持續(xù)變形一般到48 d才能穩(wěn)定,并且累計變形量很大,且利用BP神經(jīng)網(wǎng)絡方法,能夠比較準確的預測隧道圍巖在施工過程中的拱頂沉降及圍巖收斂.王開禾等[11]應用改進的遺傳模擬退火算法提高了BP神經(jīng)網(wǎng)絡的預測精度.
數(shù)值分析方面,孫闖等[12]與Zhao等[13]均基于數(shù)值計算方法分析了軟巖隧道掘進過程中圍巖變形隨隧道軸線變化過程.Basarir等[14]則考慮了巖體特性、隧道大小和掌子面后方圍巖的受力狀態(tài)等因素的影響,利用三維有限元分析對隧道縱剖面變形分布進行了計算,并提出擬合公式.
以往的研究表明,在確定的圍巖條件下,選擇相宜的開挖與支護方法,增大成本與工期,往往能有效的控制圍巖變形.而在圍巖條件較好的情況下,開挖進尺更大,支護更簡單,對于突發(fā)性不良地質(zhì)帶的抵御能力則更弱.因此,當掌子面前方突現(xiàn)破碎帶的情況下,極有可能誘發(fā)變形突變,甚至塌方.
由于以往的研究多采用二維平面模型進行計算分析,因此所針對的問題大多也是考慮斷層破碎帶走向與隧道軸線平行的情況.本文主要針對厚度較小且走向與洞軸線垂直的斷層破碎帶,通過分析圍巖變形的現(xiàn)場實測數(shù)據(jù),并結合理論分析與數(shù)值計算,探索隧道開挖鄰近穿越破碎帶時誘發(fā)的圍巖位移演化特征規(guī)律.
1 大梁隧道開挖變形特性
1.1 工程背景
蘭新高鐵(蘭州至烏魯木齊)被稱為“鋼鐵絲綢之路”,全長1 776 km,是世界上一次性建成通車里程最長的高速鐵路.其中,大梁隧道起止里程DK328+820~DK335+370,全長6 550 m,為雙線隧道,開挖高度13 m,跨度15 m,屬特大斷面隧道.洞內(nèi)線路坡度為6‰,-9‰的人字坡,除進口端位于曲線上外,其余均位于直線上.隧道穿越了海拔超過4 000 m的祁連山,最大埋深超過600 m.隧道內(nèi)巖性變化較大,且存在多條斷層和破碎帶,風險評估中重點防范的是鄰近出口處的F5斷層,寬度約100 m(如圖1所示,如表1所列[15]).由于開挖該洞段時采取了合理的開挖方法,利用超前支護預處理安全防護措施,因此并未產(chǎn)生明顯的大變形或圍巖破壞.然而,在原設計中風險較小的洞段卻產(chǎn)生了較大的變形突變和圍巖破壞.

表1 大梁隧道圍巖分級與設計開挖方法[15]Tab.1 Classification of surrounding rock and excavation method of Daliang tunnel[15]
1.2 施工期間面臨的問題
在進行輔助正洞施工時,隧道埋深465 m的洞段,遇到了嚴重的突發(fā)大變形,最大下沉速率達41 mm/d,導致初期支護混凝土開裂和剝落,變形不收斂.設計報告表明,該洞段本應為IV級圍巖,而實際揭示圍巖則為節(jié)理發(fā)育的黑色板巖,并且呈薄層壓碎狀,圍巖構造擠壓特征突出,穩(wěn)定性差,導致采用原來設計的施工方法作業(yè)后產(chǎn)生了較大的圍巖變形.
DK331+885單日最大沉降量為56 mm,單日最大收斂值為30.8 mm;DK331+766測點4 d累計最大沉降量和收斂值分別高達197.5 mm、151.3 mm,其中單日最大沉降量和收斂值則分別為45.8 mm、29.9 mm.
2012年10月11日下午2時,當開挖至DK334+241樁號時,距掌子面17~24 m處出現(xiàn)坍塌,初支鋼架受擠壓脫落,約185 m3破碎松散體失穩(wěn)涌入坑道(如圖2所示),塌腔深3.5 m,高6 m,縱向長7 m.塌方區(qū)圍巖內(nèi)存在明顯呈碎塊狀壓碎結構的碳質(zhì)板巖夾層,受構造作用強烈,不斷塌滑,圍巖處失穩(wěn)狀態(tài).塌方區(qū)周邊約10 m內(nèi)圍巖初支噴層多處開裂,拱頂噴層掉快嚴重,邊墻部分最大收斂值為1 m,初支侵限.圍巖監(jiān)控量測顯示,圍巖塌方使得該部位及周邊圍巖產(chǎn)生了較大變形,距塌方區(qū)5 m部位,當天沉降值和收斂值分別高達36.4 mm和57.6 mm.
對該洞段及周邊圍巖的長期累積沉降與收斂變形值進行觀察(如圖3所示),可見該部位累積變形遠大于周邊圍巖,原設計為III級圍巖,實際趨于穩(wěn)定時間更長.可見,準確判斷前方圍巖級別,識別潛在的破碎帶,對于選擇合理的開挖方法,施加超前支護,主動控制圍巖變形及穩(wěn)定,有著較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2 臨近破碎帶的圍巖位移特征分析
2.1 巖體物理力學參數(shù)與地應力場
對現(xiàn)場獲取的破碎帶巖體樣本進行室內(nèi)試驗分析,結果表明,破碎帶巖體多為原生巖體在地質(zhì)作用下形成,其重度介于18.2~19.6 kN/m3,級配較均勻,顆粒較粗,同時又得到足量細顆粒填充,因此內(nèi)摩擦角與粘聚力均較高,其原生穩(wěn)定狀態(tài)下可視作等效彈塑性體,故采用了Drucker-Prager屈服準則進行計算,巖體物理力學參數(shù)如表2所列.

表2 圍巖與破碎帶物理力學參數(shù)Tab.2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surrounding rock and fracture zone
基于現(xiàn)場測試,在斜井輔助正洞孔深15.0 m、18.5 m、19.0 m和27.0 m得到有效地應力測試數(shù)據(jù),如表3所列.表明,在所測深度內(nèi)最大水平主應力最大值為25.14 MPa,方向近似垂直于洞軸線;最小水平主應力13.77 MPa;垂直應力最大值為12.30 MPa;側(cè)壓力系數(shù)介于1.89~2.08之間,且與掌子面開挖斷面上觀測到的巖層彎曲現(xiàn)象一致.故基于測試結果將地應力施加到計算模型中.

表3 鉛直鉆孔水壓致裂成果表[16]Tab.3 Result table of vertical drilling hydraulic fracturing[16]
2.2 破碎帶周邊位移有限元分析與對比
參考實際工程建立三維有限元計算模型,模型長寬均為100 m,深200 m.采用8節(jié)點單元進行網(wǎng)格劃分,共劃分為117 872個單元和120 098個節(jié)點,結構面采用加密網(wǎng)格劃分,如圖4所示.利用單元生死技術模擬開挖過程,每次進尺為1 m,計算朝向破碎帶掘進過程中各測點圍巖變形演化過程.
對大梁隧道塌方區(qū)周邊開挖過程進行分析,按照塌方區(qū)寬度及巖層傾角判斷破碎帶寬度約為7 m,傾角約為66°,走向與開挖方向垂直,傾向于開挖方向一致.參考實際開挖過程進行計算,開挖速率為1 m/d,計算朝向破碎帶掘進過程中各測點圍巖變形演化過程,并與實測數(shù)據(jù)進行對比,如圖5所示.
通過對比距離破碎帶38 m的測點頂拱沉降變形計算結果與實測數(shù)據(jù)發(fā)現(xiàn),計算值與實測值存在一定差別.一方面,計算所得變形曲線中,在測點開挖出露后1 d左右可見明顯的變形速率增大,即可見明顯的變形拐點,但在實測曲線中卻并未體現(xiàn);另一方面,兩條曲線在第31 d的累積位移值大小存在高達10 mm的差別.然而,考慮到實際工程中,測點剛剛揭露時,緊貼掌子面附近作業(yè)往往存在較大安全風險,因此,實際監(jiān)測過程通常在開挖出露后1 d甚至數(shù)天后才開始.故此,將監(jiān)測滯后的因素考慮進來,將計算所得開挖曲線進行左向平移,得到新的曲線.對比發(fā)現(xiàn),考慮監(jiān)測滯后的變形曲線與實測曲線,無論是在變形趨勢上還是具體數(shù)值上均較為契合.
對向破碎帶掘進過程中,周邊洞段各測點的頂拱沉降變化規(guī)律,進行進一步分析,并繪制三維曲面圖如圖6所示.
掌子面推進到不同位置時,各測點累計沉降分布如圖6所示,其中測點與破碎帶距離為負值則表示測點位于破碎帶后方,掌子面與破碎帶距離從開挖后相距48 m一直到開挖后剛好揭露破碎帶(相距0 m)變化.可見當掌子面不斷向破碎帶推進時,各部位圍巖沉降變形差異較大.在遠離破碎帶的洞段,圍巖變形隨開挖過程的變化速率先增大,后逐漸減小;破碎帶后方的測點由于距離開挖面較遠,故變形相對較小;而當掌子面靠近距離破碎帶不足20 m時,破碎帶附近區(qū)域的巖體內(nèi)部變形則已經(jīng)非.
考慮到實際監(jiān)測中的理想情況,即開挖揭露測點位置的同時開始變形監(jiān)測,其中距離破碎帶不同距離的測點沉降變化作為單獨的曲線進行繪制,各測點累計沉降變形如圖6所示.可見,從測點暴露后開始計算,反而距離破碎帶51 m處的測點,其15 d內(nèi)所產(chǎn)生的累計變形值最大,距離破碎帶21 m的卻最小.如圖7所示進行分析可知,距離破碎帶較近的測點,其總體累計變形能更大(含測點出露前產(chǎn)生的變形).因此,在一定范圍內(nèi),距離破碎帶越近的測點在出露前(即位于掌子面之后時)會產(chǎn)生更大的變形.從圍巖受力分析,則是由于破碎帶自身剛度較小,距離破碎帶越近的圍巖受到的約束約弱,故前期變形越大.
另一方面,測點的完整變形時間曲線應有一個拐點,即從開始變形時的加速變形區(qū),變形速率不斷增大,而在經(jīng)過拐點后,變形速率不斷減小.若將距破碎帶不同距離的測點變形曲線寫作時間的函數(shù),如公式1所示.
δ(x)=f(x,t).
(1)
則,當x確定時,函數(shù)應在t>0處有1個拐點,而在前方一定距離存在破碎帶時,則拐點消失.考慮到常規(guī)條件下隧道圍巖變形監(jiān)測時測點布設的滯后性房倩等[4],監(jiān)測到的隧道圍巖變形量并不是隧道圍巖總變形,也不是測點出露后的變形,而是測點出露后一段時間開始的累計變形,因此往往難以觀察到變形曲線中的拐點.
對圍巖質(zhì)量變化較小其周邊無破碎帶的洞段(DK330+029~DK330+115)2013年2月18日的實測數(shù)據(jù)進行綜合分析,將不同部位測點按照其監(jiān)測天數(shù)和累計沉降變形的相互關系如圖8所示,可見頂拱累計沉降值與監(jiān)測天數(shù)的擬合曲線存在明顯拐點.
為進一步研究變形曲線拐點的位置,利用三次多項式進行擬合,如公式2所示.
y=-0.001 2x3+0.111 7x2+0.186 6x.
(2)
相關系數(shù)R=98.6%
令y(x)的二階導數(shù)為0,可求得拐點位置為:x拐≈31.0 d,即在曲線中第31 d左右可見變形速率由不斷增大變化為不斷減小.然而對比圖6發(fā)現(xiàn),在破碎帶周圍的測點在被揭露后觀測到的變形時間曲線中并未觀測到拐點,說明該點在開挖揭露前已經(jīng)受到開挖區(qū)的影響,原本應較大的開挖卸荷變形,在揭露前已經(jīng)逐步發(fā)生,而在實際揭露后則變形速率逐漸減小.從圖6中也可觀察到,破碎帶周邊更近的部位,其變形時間曲線中的拐點出現(xiàn)在開挖暴露之前,即x拐<0.
2.3 破碎帶傾角對圍巖變形曲線的影響
對隧道掘進穿越不同傾角破碎帶所誘發(fā)的圍巖變形進行了分析.用如圖8所示的方法進行分析,可得距破碎帶不同距離處測點的沉降變化曲線拐點位置分別如表4所列.在特定傾角的破碎帶影響下,距離破碎帶越近的部位,其變形時間曲線拐點出現(xiàn)的越早,而破碎帶傾角的變化對拐點位置也有較大影響.在傾角較小時,傾角變化對拐點位置變化影響更大,而在傾角90°左右時,其變化對拐點位置影響較小.比如在傾角為100°時,若測點在開挖揭露的同時開始變形監(jiān)測,則尚能在監(jiān)測幾天或十幾天后觀測到拐點,從而判斷前方幾十米處是否存在破碎帶,可以考慮適時調(diào)整開挖和支護參數(shù),避免之后出現(xiàn)大規(guī)模施工災害.

表4 圍巖傾角變化導致的不同測點拐點位置變化Tab.4 Change of inflection point of different measuring points caused by variation of surrounding rock inclination angle
3 結論
通過分析蘭新高鐵大梁隧道開挖過程中破碎帶塌方災害,基于對隧洞不同部位圍巖變形監(jiān)測數(shù)據(jù)的理論與數(shù)值分析,得到以下結論:
1) 在周邊無破碎帶且圍巖條件較好的洞段,隧道縱斷面的圍巖變形速率先增大后減小,圍巖變形曲線存在1個拐點,通過觀察其他洞段變形曲線拐點的出現(xiàn)時間,可以估計前方是否有破碎帶,從而選擇合適的開挖參數(shù)避免施工災害.
2) 圍巖變形過程受到周邊破碎帶的顯著影響,使得圍巖變形時間曲線中拐點出現(xiàn)時間提前,距離破碎帶更近的圍巖在開挖揭露前就可能產(chǎn)生大量變形,并且在開挖揭露后變形速率始終減小,無法觀測到拐點.
3) 破碎帶傾角較小時,傾角變化對拐點位置變化影響更大,在傾角90°左右時,其變化對拐點位置影響較小.
在具體工程中,一方面需通過及時開展監(jiān)控量測工作更為準確的獲取巖體在未受到破碎帶影響下變形時間曲線中拐點的出現(xiàn)時間;另一方面則有賴于更為先進的技術手段更早的對圍巖測點開展變形觀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