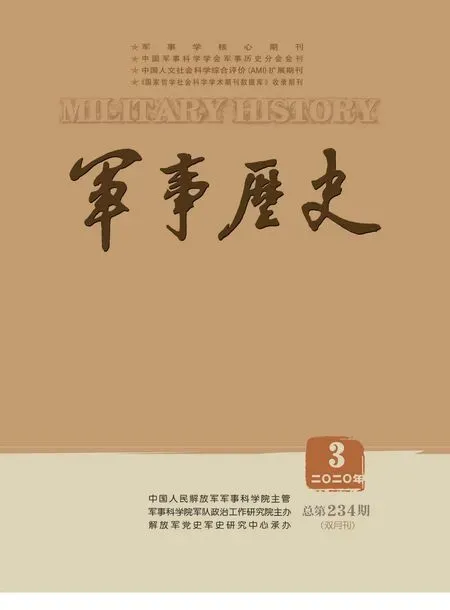對“任務式指揮”的溯源、辨析與思考
“任務式指揮”(mission-command)是美國陸軍從20世紀80年代初提出“空地一體戰”以來,在作戰指揮領域的一項重要改革成果。此后各個版本的美國陸軍野戰條令FM3-0 一直強調,“任務式指揮是美國陸軍首選的指揮方法”。2012年9月,美軍參聯會公布的《聯合作戰頂層概念:2020年的聯合部隊》,將“任務式指揮”放在構成“全球一體化聯合作戰”概念的八大要素的第一位。在新近提出的“多域戰”中,“任務式指揮”仍赫然在目。那么,究竟什么是“任務式指揮”,為什么美軍對這一指揮方式在幾十年內一直“念念不忘”呢?要解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從“任務式指揮”的概念源頭談起。
一、“任務式指揮”溯源
從美軍現行條令對“任務式指揮”的表述來看,“任務式指揮”可以歸結為如下幾方面:
“任務式指揮”是進行戰斗指揮的首選方式;在實施“任務式指揮”的過程中,指揮官只規定任務和完成時限,提供完成的條件,但并不規定下屬完成任務的方式;指揮官鼓勵下級在完成任務的過程中采取主動,甚至冒險;指揮官要諒解下屬在執行任務過程中可能所犯的錯誤;指揮官要提供明確的意圖并在確保下屬行動自由的情況下進行控制。之所以強調“任務式指揮”,是因為美軍認為地面作戰中情況復雜多變,難以預測,所以需要各級積極發揮主動性。
美軍認為,“任務式指揮”是德國軍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普遍采用的指揮方式,并認為這種指揮方式是德國陸軍在二戰中表現出眾的重要因素。在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美國陸軍理論界掀起了一股“德國熱”,古德里安、曼斯坦因等著名德國將領的回憶錄廣泛流傳,德國陸軍在二戰中高效的“機動戰”成為美國陸軍和海軍陸戰隊的效仿對象。德軍將領對指揮方式的描述也自然成為美軍制定條令的重要參考材料。在《失去的勝利》一書中,馮·曼斯坦因指出:“德軍軍事領導體系中經常強調的一點是,希望各級指揮官都能發揮主動精神,并敢于負責任,所以從原則上來講,較高指揮機構的指令和中、下級指揮機構的命令,對其下級單位都是只以制定任務為限度。至于如何執行,那是下級指揮官本身的事情,上級不應干涉。”①參見戴耀先:《德意志軍事思想》,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423 頁。這一表述同美軍現行條令里的論述基本一致。
問題在于,據考證,“任務式指揮”(Auftragstaktik)一詞最早出現在1906年符騰堡一位將軍撰寫的文獻中,直到1977年才正式編入聯邦德國國防軍的《軍語集》,并于1979年寫入了當時的《國防白皮書》。與“任務式指揮”相對應的是“命令式指揮”(Befehlstaktik)①參見戴耀先:《德意志軍事思想》,第423 ~425 頁。。二戰中德國軍隊的作戰條令中未曾見到正式使用過這個詞匯,特別是用于指導二戰德國陸軍作戰的重要條令——1933年編寫的《部隊指揮》中,根本就沒有將“任務式指揮”作為專門的一種指揮方式列出,全文中也沒有“任務式指揮”一詞。
可見,所謂“任務式指揮”,是美軍和聯邦德國軍隊根據自己的理解,對二戰中(美軍有的文獻追溯到老毛奇乃至弗里德里希二世時代,并把老毛奇奉為“任務式指揮”的鼻祖)②魯登道夫在《總體戰》“統帥”一章中,也根據自己的實踐經驗,對指揮方式有類似的總結和論述,但美軍的文獻中很少提及他的觀點。德國陸軍指揮藝術的總結,并非德國陸軍當年官方認可推廣,并在二戰中執行的某種具體的、程式化的方法。那么,美軍這種概括和總結是否準確呢?
二、對“任務式指揮”的辨析
實際上,美軍提出的“任務式指揮”是為了強調發揮下級的主觀能動性,這與二戰德軍所強調的并不矛盾。不過,如果按美軍這種概念化的理解方式,“任務式指揮”僅將焦點聚集到“任務”,也只局限在指揮領域,這就與當年德國軍隊的本意相去甚遠。
(一)“任務式指揮”并不僅僅局限于“任務”。對于發揮各級勇于承擔責任、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德軍在《部隊指揮》一書的《前言》中就做了大量論述:
“戰場的‘空白’要求軍人能夠獨立的思考和行動,他要能夠進行計算,作出決定,敢于利用任何態勢,理解勝利依賴于每個人。訓練、良好的體能、無私、果決、自信和勇氣將賦予他駕馭任何形勢的能力。”
“任何一個領導在任何時候都必須全力以赴、不推脫責任。勇于承擔責任的意愿是一個領導者最重要的素質。不過,對責任的承擔不應該建立不考慮全體的個人主義的基礎上,也不應該作為對沒能執行命令的辯解理由,如果服從命令能夠產生更好的效果。獨立的精神不能放任自流,但另一方面,在允許范圍內的自由行動是取得巨大勝利的關鍵所在。”
香豆素對小麥發芽指數、種子萌發、幼苗生長及根系活力有抑制作用,且隨處理濃度的增加而增強,肉桂酸、羥基苯甲酸和苜蓿素在處理濃度大于0.010 g/L之后抑制作用逐漸明顯。
“軍隊的指揮官和他的下級單位需要領導者具有這樣的能力:判斷力,清晰的視野和遠見,能夠做出獨立的、決定性的決定,并積極地、毫不動搖地執行決定。”
“在決定性的行動中,部隊的良好戰備狀態和力量要得到高超的指揮才能發揮作用。指揮官對部隊不必要的約束將影響勝利的取得,指揮官必須為這樣的后果負責。
部隊一旦部署到戰場上,就要根據情況隨機應變。那些不可能執行的命令將有損于對領導素質的信心,打擊士氣。”③Bruce Condell&David T.Zabecki:On the German Art of War:Truppenführung,Lynne Rienner Publishers,Inc.2001,pp.17-19.
顯然,這些論述涵蓋的意義比美軍現行條令中所理解的“任務式指揮”要豐富,表述也更加詳細、辯證和準確。同時,在《部隊指揮》的第二章《指揮》中,德軍也沒有拘泥于在執行具體任務(mission)的時候應該如何指揮,而是反復強調如何靈活地貫徹執行指揮官的意圖(intent)。例如:在第36 條中指出,“在沒有明顯影響到他的整體意圖(Absicht)的情況下,指揮官必須允許他的下屬自由行動。盡管如此,他也許不能妥協于他下屬的決定,即便是下屬獨自擔當責任。”④Bruce Condell&David T.Zabecki:On the German Art of War:Truppenführung,Lynne Rienner Publishers,Inc.2001,p.23.在第80 條中也指出,“作戰命令(Operationsbefehle)應該采用以下順序:……指揮官的意圖,這一信息是完成任務所需要的……”①Bruce Condell&David T.Zabecki:On the German Art of War:Truppenführung,Lynne Rienner Publishers,Inc.2001,p.31.“意圖”的內涵比“任務”要寬泛。為了貫徹意圖,下級指揮官可以選擇性地執行任務(misson),甚至自己為自己創造任務。不過,無論怎樣創造“任務”,都要符合上級取得更大勝利的“意圖”。埃爾溫·隆美爾撰寫的《步兵攻擊》中,專門記述了一個下級違反上級命令卻取得勝利的“任務式指揮”典型案例:
“當我們與敵軍在皮亞韋河西岸激烈交戰時,營里的其他部隊也曾試圖支援我們。在越過埃爾托成功奪取奇莫拉伊斯以西的敵軍陣地后,營長(史普約瑟少校,筆者注)立即指揮山地通信營的通信連以及第26 皇家步兵團第1 營對敵展開追擊,但是這項計劃卻違背了第43 步兵旅的命令,由于地形本身和作戰形態的限制,要其他部隊來增援我們是不可能的。在抵達圣馬蒂諾時,營長又一次接到第43 步兵旅的命令,‘符騰堡山地營必須原地待命,并在埃爾托的磨坊宿營,改由第26 皇家步兵團擔任前衛’。而營長的回復是:‘獲得加強的符騰堡山地營正在隆加羅內與敵軍交戰,請求步兵部隊對隘口公路進行增援,并將第377 帝國皇家戰炮隊前進部署’。
營長斷然拒絕了第43 步兵旅的命令,這使得第26 皇家步兵團第1 營營長克里姆林上尉如此地評價他:‘我不知道該佩服你在敵軍面前表現出來的勇氣,還是欣賞你在上級面前展現出來的魄力!’”②[德]埃爾溫·隆美爾:《步兵攻擊》,曹磊譯,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14年,第307 ~308 頁。
正是因為史普約瑟少校的“抗命”,隆美爾指揮的連隊得到了及時增援,在隆加羅內合圍了大批意軍,贏得了重大勝利,史普約瑟也沒有因為抗命受到任何懲罰。從此可以看出,德軍并非鼓勵為了完成任務而戰場抗命,更不是鼓勵上級為下級的錯誤買單,因為畢竟服從命令是軍人的天職,也是確保軍隊令行禁止、統一行動的基礎,如果不服從命令造成重大損失,一樣會被嚴懲。但是,德軍同時強調,下級軍官可以根據自己對態勢的判斷做出更有利于實現總體作戰意圖的決定,如果這一決定最終取得了更好的效果,那么下級也不會因為“抗命”受到懲罰。這種良性導向是顯而易見的:畢竟下級軍官在作戰中比上級能夠更直接、更真切地感受到戰場態勢變化,尤其是在通信手段有限的條件下,這種主動性更是搶得制勝先機的重要因素。
(二)“任務式指揮”也不僅僅局限于“指揮”。如果說“意圖”和“任務”之間的區別只是理解問題的角度不同,美軍試圖通過在條令中強調一個新概念,就把德軍的先進指揮模式復刻到自己軍隊的指揮過程中,無異于緣木求魚。因為想達到指揮上積極主動的目的,絕非發布一本條令就能實現,需要經過長時間的制度、人才建設和文化熏陶,是涉及多個領域的系統工程,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是“總參謀部—下級參謀部”制度的建立。德軍總參謀部并非一個單獨的高級領導指揮機構,而是一套完整的制度。其精髓在于“總、分一體”:總參謀部的人員和下級部隊(集團軍、軍、師三級)參謀部的人員是全軍按照同樣的標準一體選拔、按照同樣的模式一體培養、按照統一的成長路徑一體統籌任免的。總參謀部不僅是軍隊的“大腦”,而且與各級軍隊參謀部有效銜接,確保各級的“大腦”和“神經”緊密聯系。在這種模式下,各級的作戰參謀都是一起在柏林戰爭學院的同學或者學長、學弟,相互之間熟悉,思維方式基本一致,溝通交流順暢,這就搭建了上下級相互信任的基礎。總參謀部中崗位設置也別出心裁,上校處長之上就是副總參謀長(中將以上),沒有中間級別可供晉升,如此就確保了在總參謀部工作到上校級別就必然需要到部隊任職,比如擔任師參謀長或者集團軍參謀部作戰處長,晉升的話就必須去部隊任旅長或者軍參謀長。換言之,下級各作戰部隊的參謀部,人事任免和總參謀部一體統籌安排,最終決定權在總參謀部,這樣保證從上到下政令暢通、令行一致。如此設置的另一個優點是上校以下的軍官普遍年富力強,精力旺盛,能夠適應繁忙的工作。這一安排的前提是總參謀部系統的高度精英化,人事任免調配相對簡單,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軍總參謀部系統軍官共有200 人左右,二戰中德軍步兵師機關僅編配39 人。為保證精干機關的高效工作,總參謀部系統配屬的警勤保障力量也很扎實。師、團都編有司令部連,公勤雜務大多由士兵或文職人員負責,將參謀從繁雜瑣事中解放出來,集中精力研究作戰。
二是長期的平等、務實的氛圍熏陶。19世紀初,沙恩霍斯特改革就倡導軍事學術面前人人平等的良好作風。老毛奇時代的總參謀部里,少尉參謀和上將參謀長之間為某個作戰問題爭論得面紅耳赤并不鮮見。這也是普魯士軍事改革以來一直強調的作風:參謀不是首長的附庸,必須能獨立思考,以確保首長定下正確的決心;在軍隊的特殊環境中,盲從是容易的也是輕松的,獨立思考則需要勇氣和智慧。還有就是務實的風格。無論是作戰報告還是訓練考核,對部隊士氣、食物補給、裝備性能問題等直言不諱,這有利于上下級之間有效溝通,實現共同作戰意圖。
三是長期扎實、認真的演習演練。德軍格外注重演習演練。德意志帝國時期每年舉行一次全軍性的秋季演習,推演重要方向作戰方案,德國皇帝或者總參謀長親自指揮組織,各級指揮機構在演練中都要按照實戰要求運作。如此,一方面極大加快了德軍戰法的創新。以裝甲戰為例,從20世紀30年代初開始發展連級規模的裝甲力量起,德軍裝甲部隊就頻繁用于各種演習,哪怕是只能用紙箱模擬坦克時也沒有打折扣。另一方面,在長期的演練中,上下級指揮官和指揮機構也能反復交流碰撞,磨合協同,錘煉作風。柏林戰爭學院畢業的“準參謀”能否留在總參謀部系統工作,在年度演習中的表現是一個重要衡量標準。
三、思考與啟示
綜上所述,“任務式指揮”既不僅僅關于“任務”,也不局限在“指揮”領域。美國陸軍只是照搬了這一概念,并沒有對軍官培養、作風養成和演習進行針對性的、全面的設計改進。無怪乎美籍德國軍事史專家克羅姆諷刺說:美國陸軍只是把“任務式指揮”掛在嘴上,而從來沒有真正理解它的精神實質。對這一問題的辨析,有以下幾點思考與啟示。
(一)注重鑒別美國軍事思想的不足和缺陷。總體上看,由于文化傳統、政治體制等因素,與蘇(俄)、德的軍事思想相比較,美軍軍事思想比較缺乏深邃的哲學思考和嚴謹的理論體系,其實用主義、唯技術論色彩比較濃,但其學術思想活躍,理論研究觀點爭鳴多,“拿來主義”盛行,一直重視從兵學積淀深厚的蘇(俄)、德軍事理論中汲取先進思想。一些看似美軍的創新,其實是美軍對蘇(俄)、德經驗的理解總結,這就需要在研究與借鑒過程中找到理論源頭,研清本旨,避免“跟著錯”。
(二)加強對人民軍隊優良經驗的總結吸收。“任務式指揮”中強調的指揮理念,其實并不“新鮮”,中國古代兵法中“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即含有其中之意;而人民軍隊強調的軍事民主、上下一致、積極主動等理念,也走在了同時代的前列。聶榮臻在回憶毛澤東的指揮時指出,“毛澤東同志對下面的事情從來不規定得很死,作戰呀、部署呀、戰役戰術上的組織等等,都是如此,因為他要給下面機動,充分發揮大家的主觀能動性”,但“蘇聯顧問不懂得我們的做法”,反問我們“這是命令嗎?”①參見《聶榮臻元帥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第582 頁。。
(三)及時開展新概念的配套政策的研究。任何一個概念的存在都需要有配套支撐的制度機制,單單提出一個概念,不進行相應的制度改革和配套設計,只能是無源之水。德軍指揮理念能一直保持先進,就得益于其統帥機關的“部(局)—處”兩級架構帶來的人員精英化和高活力,否則一個臃腫的、缺乏體系化流動晉升渠道的指揮機構必然陷入人浮于事、推諉扯皮、效率低下的困境。因此,提出新的概念不易,配套政策制度構建完善更難,落到實處尤難,需要全面、長遠的思考和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