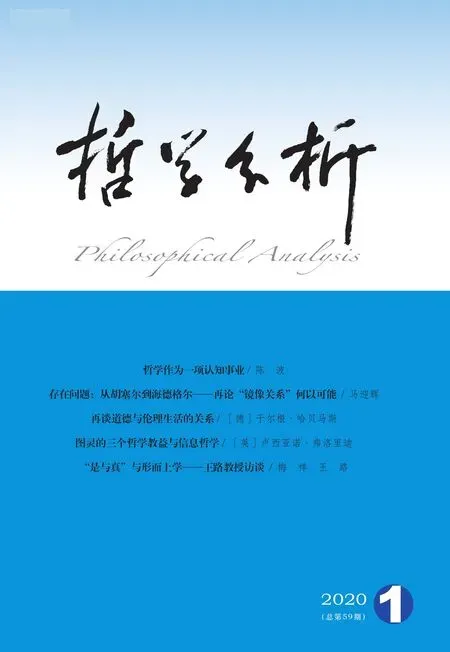圖靈的三個哲學教益與信息哲學①
[英]盧西亞諾·弗洛里迪/文
姜晨程/譯
一、引 言
當一個人研究圖靈的哲學遺產時,可能存在兩種危險。一種危險是將其歸納為他最著名的測試②A. M. Turing, “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 Mind, Vol. 59, 1950, pp. 433—460.,這樣做的好處是清晰。任何人都能在討論中將它辨識出來,并找到它在相關爭論或人工智能哲學中的位置。另一種危險是將其削弱成一種無所不包的敘事,將圖靈的觀點視為我們今天所做和所知的任何事物的來源。這樣做的好處是承認了這個天才的偉 大。
然而,在這兩種情況下,我們都將不太可能識別出,圖靈的哪些概念貢獻已經在我們當代的哲學討論的形成中發揮了作用,哪些又會指導它們的未來發展。為了避免這兩種風險,在下文中我會專注于三個特定的哲學教益,考慮到信息哲學的出現和其后續的發展,這三個教益看來是特別重要的。我將提供的不是一種文獻學或博學(scholarly)的分析,而是一種極簡主義的、解釋學的實踐。圖靈非凡天才的一部分,就是不同的解釋者會從他的智識遺產(intellectual legacy)中得到更多的和不同的教 益。
我希望引起讀者注意的三個哲學教益是:圖靈有關抽象層次的方法(levels of abstraction,LoA)的工作,是如何教導我們合適地提出一個哲學問題的;作為對圖靈工作的推論,什么哲學問題在今天是最緊迫的;以及,圖靈對塑造我們的新的哲學人類學的影響,我將這種新的哲學人類學稱為第四次革命;最后,我會將這些教益聯系到信息哲學的發展 中。
二、教益一:錨定(fixing)抽象層次/如何問哲學問題
想象如下場景。你詢問一個物品的價格,如一輛二手車,然后收到如下回復:5000。這個問題牽涉一個變量,即這輛車的價格x,但當你收到了一個精確的數值x時,這里仍然漏掉了一些東西。你仍然不知道價格,因為你不知道變量x的類型——它是英鎊、美元、歐元或是別的什么?當然,語境通常有所幫助。如果你在英國問一個汽車商,那么你的問題就應該被理解為按英鎊計算的價格,回復也是如此。你可能認為這不過是雞毛蒜皮,格賴斯①即保羅·格賴斯(Herbert Paul Grice),英國著名語言哲學家。——譯者的會話規則(conversational rules)顯然適用。這確實是雞毛蒜皮,那些規則也的確適用。但是它依然是一個容易被遺忘的重要假設。在1999年11月,NASA損失了價值1.25億美元的火星氣候軌道探測器(Mars Climate Orbiter, MCO),只是因為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 Martin)公司工程團隊使用了英國測量單位,而其代理商的團隊卻在宇宙飛船的一個關鍵操作上使用了米制計量法。從而導致MCO在火星墜毀了。②《火星氣候軌道探測器事故調查委員會第一階段報告(新聞稿)》,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參見ftp://ftp.hq.nasa.gov/pub/pao/reports/1999/MCO_report.pdf。總是假設語境能消除你所使用的變量類型的歧義,無異于為昂貴的錯誤鋪路。不過這一切和圖靈有什么關系呢?事實證明:有,而且很大。為了說明這一點,讓我介紹一個略微抽象些的模型。③對 此 的一個簡 介,參見L. Floridi, Informatio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一個完整的哲學分析,參見L. Floridi,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我們可以將這類事實信息視為問題+回答的復合(compound),它由上述二手車價格的例子所描述。如果允許一些理論上的簡化,問題可以被簡化為布爾型(Boolean)的,即由“是”或“否”來回答。于是在最初版本的例子中,二手車的價格變成了:這輛車的價格是5000嗎?回復:是的。你能立即看到出錯的不是回答,而是問題:它不包含對目前處理的變量類型的指示。正確的信息當然應該是:這輛車的價格是5000£嗎?回復:是的。這里剛剛介紹了一種正確的抽象層次,或者說LoA,它由英鎊的符號£而不是由歐元的符號€所表征。而圖靈是第一個理解這一做法的至關重要性的人,即表達出一個合理問題(sensible questions)所在的LoA。它可能看上去令人驚訝地明顯,但上述第二個關于MCO的例子,展示了忘記隱含的LoA是多么的容易和危險。清楚自己的抽象層次的重要性就像地球是圓的一樣明顯,而美洲正是由于后者才被發現。現在,我們用了圖靈的天才智慧才將它揭示出來。當然,圖靈的貢獻不是介紹了“有類型的變量”(typed variables)這個概念,也不是確立了對參照系的需要。這些觀念在他的時代就早已很常見了。他的教益是第一次澄清了哲學的和概念的問題只能在錨定的LoA中才能得到有意義的回答。這是他那個著名測試的最偉大和持久的貢獻之一。遠比那些對“機器什么時候會通過這個測試”,還有“如果機器的確通過它了能從中得出什么結論”的錯誤預言重要。①L. Floridi, M. Taddeo & M. Turilli, “Turing’s Imitation Game: Still a Challenge for Any Machine and Some Judges”, Minds, Mach. 19, 2009, pp. 145—150.有一件事時常會被遺忘,即圖靈拒絕哪怕是嘗試性地給“機器能思考嗎?”(can a machine think?)這個問題提供一個回答,因為他認為這個問題“過于無意義以致不值得被討論”。用我們的簡單例子,它就像完全在數字上問這輛二手車的價格,并堅持不用任何貨幣來表征它。這毫無意義。同樣,圖靈反對包含了諸如“機器”和“思考”這樣的模糊概念的問題。換句話說,它缺乏一個清晰的抽象層次。因此他建議將其替換成模擬游戲(the Imitation Game),后者是更易管理的和更少苛求的,因為它錨定了一個基于規則的,易于執行和控制的情境。②J. Moor, The Turing Test: The Elusive Standar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3.通過這樣做,他制訂了一個LoA——他為這個游戲選擇的“貨幣”是人類智能,但這也可以是別的,如從動物智能到人類創造性,就像許多其他版本的圖靈模擬游戲的所展示的那樣——并且提出了一個新問題,這個問題可以被概括為:“在由模擬游戲所表征的抽象層次上,一個人可以斷定一個機器正在思考嗎?”經過了半個世紀,哲學依然在學習如此重要的一課。③關于抽象層次的方法的使用,參見L.Floridi, Informatio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和L. Floridi, “The Method of Levels of Abstraction”, Minds, Mach 18, 2008, pp. 303—329。關于圖靈在這個方法的發展上的關鍵性角色,參見L. Floridi, “Turing Test and the Method of Levels of Abstraction”, in Alan Turing: His Work and Impact, S. B. Cooper & J. van Leeuwen eds,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Elsevier (in press)。第二個教益將會需要一個更長的前提。
三、教益二:專注于最重要的問題/問哪個哲學問題
在2010年4月23日,比爾·蓋茨在馬薩諸塞州劍橋市的麻省理工學院作了一個演講,其中他問道:“最聰明的頭腦們在致力于最重要的問題嗎?”這里“最重要的問題”指的是“改善最貧困人口的生活;提升教育、健康、營養”。不過,這個清單可能還應該包括促進和平互動,人權、環境、生活標準,等等,并且這些僅僅只是開始。①L. Floridi, “Information Ethics”, in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Information and Computer Ethics, L. Floridi(ed.), Ch. 5,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無疑,最聰明的哲學頭腦們不應成為例外,而是應該將他們的注意力放到這些緊迫的挑戰上去。當然,有的人可能會停止哲學思索,并開始為這個混亂的世界做些什么。換句話說,我們可以關閉我們的哲學系,絕不用哲學來腐化我們最聰明的年輕人們。然而這樣的解決方案有點自我挫敗(self-defeat)的意味。它就像因為熱氣球下降得太快了,而決定燒掉我們在其中旅行的柳條筐。哲學是那種你會在一個好的世界中想要保留下來的東西,而不是你會在一個壞的世界中想要擺脫的東西。有蘇格拉底的雅典是一個更好的雅典。因此這里必須有一條不同的前進道路。事實上哲學可以變得極為有幫助,因為正是被理解為概念之設計的哲學,鍛造出了新的概念、理論、觀點以及更一般的智識框架(intellectual framework),這種智識框架可以被用于理解和處理那些對我們最具緊迫性和挑戰性的根本問題。在最聰明的頭腦們的團隊合作中,哲學工作者可以貢獻洞察和遠見、分析和綜合、啟發式思路和解決方案,它們能使我們有能力去處理“最重要的問題”。每一個小的努力都能夠在對抗愚蠢、蒙昧主義、褊狹、狂熱和所有類型的原教旨主義、盲從、偏見和純粹的無知的更大戰場上幫助我們。如果這聽起來像是自利的(self-serving),那就想想向前跳躍的距離越長,助跑的距離也就相應越長。或者,用一個不同的比喻,哲學照顧根部,以便植物的其他部分可以更為健康地成長。假如我們接受了所有這些作為一個合理的預設,那么哪些概念、理論、觀點以及更一般的智識框架是哲學家們應該在現在或在可見的將來進行設計,以便能夠及時而有益地作出他們的貢獻?哪些哲學問題又是他們應該處理的?如果這個回答中缺少了圖靈的遺產,那將會是難以想象的,因為它所位于的概念路線穿過了如此多我們最重要的問題。在一個全球性的信息社會,事實上我們面臨的任何重要挑戰都與信息和通訊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相關,并由原因、結果、解決方案、科學研究、真實的改進等術語所描述,因此概念資源對于理解這些挑戰是必要的,甚或是處理它們所必需的資產,就像比爾·蓋茨的例子所清晰的展示的那樣。顯然,信息資源、技術以及科學并不是萬能藥,但它們在我們與這么多困難的戰斗中是一種重要而強大的武器。因而,從圖靈那里獲得的第二個教益是關于最聰明的哲學頭腦們應該處理的問題的類型。我們生活在每個最重要的問題背后都躺著一臺圖靈機的信息圈(infosphere)。這是一個我們開始重新概念化人類自身的新世界,這也是我們從圖靈那里獲得的第三個教益,我將在第四節中討論 它。
四、教益三:發展一種新的哲學人類學/從哪個視角來切入哲學問題
極度簡化地說,科學有兩個改變我們的理解的基礎方式。一個可以被稱為外向的(extrovert),或者說關于世界的,而另一個可以被稱為內向的(introvert),或者關于我們自身的。三次科學革命已經同時通過外向和內向的方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改變我們對外部世界的理解,以及我們與其互動的方式的過程中,它們也修改了我們關于我們是誰和希望成為誰的概念。在哥白尼之后,日心宇宙學取代了地心說,也因此將人類從宇宙中心的位置上拉了下來。達爾文展示了所有的生命都源于共同的祖先,并通過自然選擇隨著時間進化,因而將人類從生物王國中心的位置上拉了下來。接著是弗洛伊德,我們今天已經承認了心智也包含潛意識,并且受制于對壓抑的防御機制,并因此也將人類從純粹理性的中心的位置上拉了下來,這個位置至少從笛卡爾開始就被假定為是無可爭議的。即使像波普爾和我這樣的,會對遵循弗洛伊德并將精神分析視為一種像天文學或進化論一樣嚴格的科學事業表現出不情愿的讀者,現在也會愿意承認當代神經科學是對這一革命性角色的很有希望的候選者。不管怎樣,結果就是現今我們承認我們不再是固定的位于宇宙的中心(哥白尼革命),我們不再是不自然地與動物王國里的其他生命不同的(達爾文革命),而且我們也遠不是那種對自己完全透明的笛卡爾式的心智(弗洛伊德或神經科學革 命)。
對于這個經典圖景,人們往往會質疑它是否有存在價值。畢竟,弗洛伊德①S. Freud, A Difficulty in the Path of Psycho-analysis, in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the Standard Edition, Vol. XVII, J. Strachey (ed.), London, UK: Hogarth Press,1917, pp. 135—144.自己就是第一個將這三次革命解釋為重新評估人類本質這一單一過程的一部分的人。②F. Weinert, Copernicus, Darwin, and Freud: Revolutions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Oxford, UK:Blackwell, 2009.他的解釋學策略被公認是自利的,但這確實是一個合理的觀點。在計算機革命之后,當我們現在感知到一些非常重要和意義深遠的事已經發生于人類生活之中,我將要以一種相似的方式,論證我們的直覺又一次是敏銳的,因為在對人類的本質及其在宇宙中的角色進行脫位(dislocation)和重新評估的過程中,我們正在經歷第四次革命。這個進程從19世紀50年代開始就在持續進行著,而圖靈無疑是這次革命的代表性人物。計算機科學及其不斷發行的技術應用已經在其內部和外部都產生了影響。它們不僅提供了對自然以及人工實體的史無前例的認知以及工程力量,還已經通過這一過程使我們對“我們是誰”“我們如何與這個世界相互聯系”以及從而“我們如何理解我們自身”有了新的認識。今天,我們正慢慢接受我們不是獨一無二的存在這一觀念,我們更像是以信息方式具身的有機體(informationally embodied organisms,簡稱infrogs,即信息體),在一個信息化環境(也就是信息圈)中相互連接和嵌入,我們跟在許多方面與我們相似的自然以及人工能動者(agent)共享這個信息圈。圖靈已經像哥白尼、達爾文以及弗洛伊德一樣深刻地改變了我們的哲學人類學。這已經對在圖靈之后做哲學意味著什么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以上就是我想引起讀者關注的最后一個教 益。
五、教益的總結:建立一種新的信息哲學/如何理解當今世界
什么能賦予人類理解、尊重并且負責任地改善當代世界的能力,并從而在解決“最重要的問題”上有所助益?答案看起來很簡單——一種新的信息哲學。在我們日常的和技術的概念中,信息是當前最重要的、被廣泛地使用的卻最少被理解的概念之一。最聰明的哲學頭腦應該將注意力轉向它,以便設計我們時代的,并為這個時代而合適地概念化了的哲學。不過,將信息哲學作為一個在哲學史上非常必要的發展來介紹也只是一個粗糙的權宜之計。現在,讓我來概述一個將其與圖靈相聯系的更久遠的脈絡。
的確,將一種新的信息哲學的基礎甚或其創建歸因于圖靈,似乎延伸得太過分了。畢竟圖靈從未專注于信息這個概念本身,也從未專注于被理解為信息流動或傳輸的通訊問題(盡管他和香農事實上了解彼此的工作)。因此圖靈的《圖靈精義:計算、邏輯、哲學、人工智能和人工生命的重要著作,以及恩尼格瑪的秘密》①A. M. Turing, The Essential Turing: Seminal Writings in Computing, Logic, Philosoph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Artificial Life, Plus the Secrets of Enigma, Oxford, UK: Clarendon Press, 2004.甚至沒有包含“信息”這個條目,而龍貝格②D. G. Luenberger, Information Sci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寫的另一本類似的書也僅僅在說到布萊切利園③布萊切利園(Bletchley Park)位于英國,它曾經是二戰期間英國政府進行密碼解讀的主要場所,軸心國的密碼與密碼文件,如恩尼格瑪密碼機等,一般都會送到那里進行解碼。——譯者時提到了圖靈一次。然而,我將論證,沒有圖靈和他在信息處理上的開創性的工作及其在科學和技術上的影響,以及上面已經勾勒出的三條教益的輪廓,當代對信息哲學的關心將會難以解釋。圖靈、香農和維納共享了喚起我們對信息世界及其動力學的哲學關注的功績。沒有他的三個教益,就沒有信息哲學。今天我們更傾向于把電腦作為通訊機而不是強大的計算機這一事實,只是表明了圖靈的工作對我們的世界造成了多么深的影 響。
六、結 論
新的哲學觀念的發展和經濟創新有相似之處。因為,當熊彼得用“創造性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來說明經濟創新,他也許同樣在說智識的發展。哲學是通過持續地重建自身來獲得繁榮的。現在,它的創新引力(pulling force)是由信息、計算和通訊現象——以及相應的科學、技術、新環境、社會生活,包括它們帶來的關于存在的、文化的、經濟的和教育的問題——的世界所表征的。這是一個要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圖靈的工作和智識遺產的新情境。在前文中,我已經概括了我們應該從圖靈那里獲得的三個哲學教益。我認為信息哲學——在它實現圖靈遺產的范圍內——可以將自身呈現為一個創新范式,這個范式打開了一個非常豐富、有助益并且適時的概念研究領域。從學術上說,信息哲學是一個哲學領域,它涉及對信息的概念本質和基本原則的批判性調查,這包括它的動力學、利用以及科學,還包括對信息理論和計算方法論在哲學問題上的詳細闡釋和應用。更具體地說,信息哲學致力于給出一個明確的、清晰的、精密的對于經典的“是什么”(ti esti)問題,即“信息是什么?”的闡釋,而這個問題是一個新領域的最清晰的標志。但和其他領域問題(field-question)一樣,這也僅能供一個研究領域的劃界之用,而不能詳細確定它的特定問題的位置。信息哲學力求通過提供創新的方法論來處理在當代視角下最重要的那些問題,擴展我們哲學理解的邊界。它依賴于圖靈的這一直覺——以抽象方法來確保問題在正確的層次上被處理,是至關重要 的。
科學革命使得十七世紀的哲學家們將他們的注意力,從可知對象的本性上(因此也從認識論的形而上學上)轉移到了它和認識主體之間的認識關系中。信息社會的后續發展和信息圈——也就是如今數以百萬計的人們在其中度過他們的生活的環境——的出現,已經將當代哲學的批判性反思優先引向了一個領域,這個領域由組織知識的記憶和語言,以及信息圈賴以管理的工具——哲學也因此從認識論轉到語言哲學和邏輯學——所表征,同時也優先引向了它們所特有的結構和實在的本質,還有信息本身以及它的動力學、通訊、流動和處理。信息因此成為了一個和存在(Being)、知識、生活、智能、意義、善和惡——還有所有與它們相互依賴的關鍵概念——一樣重要而根本的概念,而且同等地值得自發的研究。但這也是一個相較更為貧乏的概念,因為其他概念在沒被明確定義時,也能被表達和相互聯系。這就是為什么信息哲學可以解釋和指導對我們的智識環境的有目的的建設,并為當代社會的概念基礎提供一個系統性的處理方案。信息哲學的未來取決于我們如何與圖靈的智識遺產、與我們時代“最重要的問題”,以及與經典哲學問題打交道。對此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還要感謝圖靈的是,理解和處理宇宙的基本知識的培根—伽利略工程已經開始在計算機的和信息的革命中找到了自己的實現方法,它對我們關于實在的知識,對我們概念化實在的方式,和在對其中的我們自身都產生了意義深遠的影響。信息的敘述擁有一種本體上的力量,而不是一些迷人的閑談、神學的邏各斯(logos)或者神秘的規則,而是內在的,就像可以描述、修改和實現我們的環境和我們自身的建筑工具。從這個角度,信息哲學可以被表征為對信息活動——自然的和人工的,物理的和人類學的——的研究,這些活動使對實在的建設、概念化、語義化和道德上的管理成為可能。信息哲學使人類能夠理解世界,并且負責任地建設它。它有望成為最令人興奮和最有益于我們時代的哲學研究領域。它的發展將會成為在哲學中繼承圖靈的工作和尊敬他的遺產的合適方 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