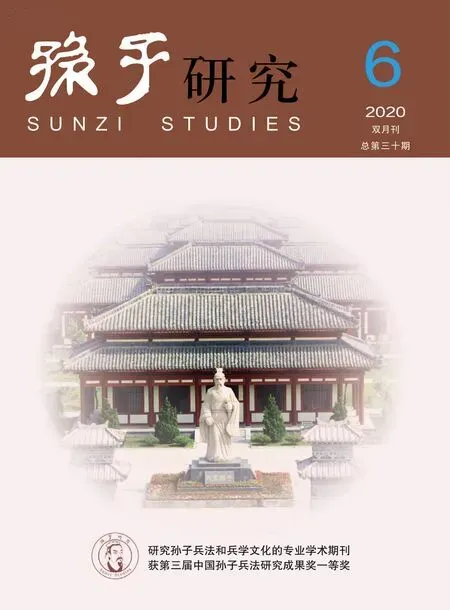蘇洵對孫子反情報思想的繼承與發展
梁 舟
現代情報學認為,情報與反情報之間的關系看似相互對立,但實際上不可分割、相輔相成。美國學者艾布拉姆·舒爾斯基(Abram N.Shulsky)認為,反情報在廣義上是指為保衛本國免受敵方情報機構侵害而搜集和分析的信息,以及為此目的而開展的行動;狹義上則專指防備對方獲取對其有利的信息的行動。[1]《中國軍事百科全書》認為,反情報是對對方情報活動或意圖采取的反制措施。[2]上述認識無疑都認同反情報是情報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情報斗爭的重要內容,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手段。[3]
反情報一貫是中國古代兵家學者研究兵學、探討軍事戰爭問題時的重要內容。春秋晚期的孫子當屬中國歷史上論述反情報問題的先驅,其代表作《孫子兵法》中蘊含著豐富而深刻的反情報思想,對后世歷代影響深遠。兩宋時期,基于“崇文抑武”“以文制武”的特殊國策及內憂外患的時代背景,文人論兵風尚凸顯。“頗喜言兵,慨然有志于功名者也”[4]的蘇洵通過《權書》《幾策》等論兵之作,深刻剖析了北宋的軍事問題,同時也在反情報領域頗有建樹。蘇洵的反情報思想,既有繼承孫子反情報思想的顯著特征,同時更凸顯了他的獨特思考。
一、拒止:在重視保密方面與孫子一脈相承
學界認為,所有的反情報措施都可以歸結為拒止(denial)、偵查(detection)和欺騙(deception)三類。其中,“拒止”,即防止敵對情報機構接觸敏感信息,以及敵方的策反及滲透行為。[5]這一概念實際上等同于保密。保密事關軍事活動成敗乃至國家存亡,自古便被視為政軍活動中的重要議題。早在先秦時期,就已涌現出大量關于保密的認識。《易經》指出:“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6]道家代表人物老子有言:“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7]法家代表人物韓非子則有“事以密成,語以泄敗”[8]的名言。“兵家鼻祖”孫子深刻揭示了保密之于軍事的重要性,在《孫子兵法》十三篇中較為系統全面地論述了保密問題,這確立了他在中國保密思想史上舉足輕重的重要地位。
(一)高度重視戰略決策及戰術設計過程中的保密工作
蘇洵所處的時代,正是北宋與契丹政權相互承認、維持和平的階段。在宋初對遼戰爭失利之后,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宋、遼通過澶淵之盟結為兄弟之國。這種外交為主、軍事為輔,“以金錢換和平”的方式確實為北宋創造了較長時期的和平,“絕口不談兵”由此成為北宋統治集團的主流觀點。在此背景下,蘇洵對北宋與契丹的局勢進行了較為透徹的分析。在專門分析宋遼關系的《審敵》篇,蘇洵直指“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9],意即當時普遍未引起重視的契丹實際將是北宋的一大勁敵。“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10],契丹的志向遠不止于“小利”,它是有“大欲”和“遠謀”的。契丹并不滿足于北宋的巨額歲貢,它的真實意圖在于借助歲貢實現自身強大,同時通過澶淵之盟使得北宋忘戰去兵、武備皆廢,最終達到“滅宋”的目的。北宋統治者之所以還沉醉于歌舞升平,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與警惕,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便在于契丹具有很強的保密意識,善于隱藏自己的真實意圖。對此,蘇洵指出,“鷙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11]。蘇洵借用冒頓隱藏攻漢動機的史例,直指契丹也在隱藏其狼子野心。能對宋遼局勢及契丹真實意圖進行如此透徹的分析,已經凸顯出蘇洵對于保密的重視,他深深懂得在戰略決策階段做好保密工作的重要性,意識到保密是隱藏己方真實意圖、奪取制勝先機、贏得戰爭主動權的重要手段。蘇洵探討了敵方在戰略決策階段的保密工作,孫子則更多集中于己方在此階段的保密工作。“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12],意即保守作戰意圖及作戰方案是確保戰爭勝利的前提條件。孫子同時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夷關折符,無通其使;厲于廊廟之上,以誅其事。”[13]可見,做好戰略決策階段的保密工作是戰爭行為的本質要求,這是敵我雙方都無法忽視的。
戰爭一旦打響,敵方便會用盡一切手段來窺探我方軍事機密,以掌握我軍下一步計劃部署。因此蘇洵強調在作戰過程中也時刻不能放松保密要求。尤其是在開展隱秘行動時,注重保密便顯得尤為重要。“大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撾鼓,突出乎平川以沖敵人腹心者,曰伏道。”[14]這強調了在運用“伏道”進攻敵人時,部隊潛行于高山峽谷中,必須禁止敲鑼擊鼓,有效地隱匿行蹤,如此才能達到出其不意沖擊敵方腹心要地的效果。一旦沒有做好保密措施,就很可能遭到敵方埋伏、偷襲,甚至于全軍覆沒。孫子也有類似的看法,“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15]。無論進攻或是防守,做好保密工作都是軍事行動取得勝利的重要前提。在防守時做好保密工作,才能有效隱匿己方兵力,使敵方找不到進攻突破口;做好進攻時的保密工作,便能實現如天降神兵的絕佳效果,讓敵人猝不及防。
(二)在開展軍事行動前后嚴格控制知密范圍
軍事機密事關己方軍事行動及戰略部署全局,若不慎泄露戰爭局勢便可能瞬間逆轉,甚至導致滿盤皆輸。導致失泄密發生的原因有很多,除了敵方的刺探竊密外,己方內部人員也會因為一己私利或其他各種原因有意無意地泄密。嚴格的保密措施能較好地防備敵方的竊密,卻難以阻遏己方人員的泄密,可謂防不勝防。為從源頭上降低己方人員泄密的可能性,蘇洵提出了他的思考:“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故士皆委己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后可與之皆死。”[16]這里強調要使士兵愚昧無知,實際就是指不要向士兵透露過多信息,只能將部分無關緊要的信息選擇性地告知他們。將核心機密的知悉范圍限定在部分高級將領內部,普通士兵無權知曉這些重要信息,就能有效地降低失泄密的可能性,確保己方機密安全,同時也能驅使士兵別無二心積極參戰。蘇洵的這一思考,與孫子的愚兵之術如出一轍:“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17]孫子早已指出將帥在必要之時要學會蒙蔽士卒的耳目,不能讓他們知曉軍機要事。[18]他甚至強調要達到“驅趕羊群”的效果,士兵只需聽從指揮前進,而不知道將帥的真實目的。
這種愚兵的方式在學界引起不小爭議,很多人將之視為中國古代兵學思想的糟粕。但也有更多人從不同角度,將“愚”字解讀為“保密”。例如,李筌曰“不欲令士卒知之”,王皙曰“情泄則謀乖”,張預曰“前所行之事,舊所發之謀,皆變易之,使人不可知也”[19]。這些注家都認同孫子愚兵之術對于保守軍事機密的重要作用。郭化若則以更為宏觀的視角看待這一問題:“這種保密工作古今中外都一樣,決不能作欺騙士兵解釋。”[20]人類的軍事斗爭史上確實廣泛存在這一現象,長期以來被古今中外將領視為保守軍事機密的必要舉措,因此不能將之簡單地理解成欺騙士兵。也許正是這一措施,才啟發了現代保密工作中的秘密分級管理制度,并得到進一步深入細化發展。
(三)制定嚴厲法制嚴懲失泄密人員
人是軍事活動中最為活躍、最不可控的因素。因此,盡管將帥三令五申一再強調重視保密,并運用愚兵之術來嚴格限定知密范圍,失泄密問題還是難以完全禁絕。蘇洵對失泄密行為的本質及危害有著清醒認知,將保密視為全軍上下不可逾越的底線問題,因此主張必須采取強硬舉措嚴厲懲治失泄密人員。“偃旗仆鼓,寂若無氣。嚴戟兵士,敢嘩者斬”[21],這里的敢于喧嘩者,不僅是違背了上級命令,同時更是保密意識淡薄、嚴重違反保密紀律的行為,對于己方軍事行動造成了嚴重損失。蘇洵主張以死罪論處,絕不姑息,以達到殺一儆百、堅決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的效果。蘇洵的這一觀點最早還是要追溯到孫子這里。對于間諜人員的泄密,孫子的態度非常嚴厲:“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22]他不僅主張要殺泄密者,還要斬殺所有知曉秘密的人員。孫子的觀點得到后世廣泛認同,唐代陳皞肯定其“俱殺以滅口”的作用,何氏則強調了“兵謀大事,泄者當誅”這一合法性。[23]這種舉措看似非常冷酷無情,但實際非常必要且效果顯著,一方面可以防止失泄密范圍進一步擴大,盡最大可能降低損失,另一方面以此警示他人,起到威懾警戒和強化保密思想的作用。
孫子、蘇洵等古人對待失泄密問題的嚴厲態度,對于今天開展保密工作及應對失泄密問題仍有很強的警醒作用。軍事保密本質上處理的是敵我矛盾,實際體現了對敵斗爭的態度、立場及行動,體現的是對黨忠誠、為國盡忠的職責。[24]一個在軍事保密上出問題的人,是談不上對黨和國家忠誠的。正如鄧小平同志曾經指出的:“泄密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嚴格說起來,都等于是叛國行為。”因此,對待失泄密問題,我們必須采取零容忍態度,要以嚴格的條令法規為保密工作劃定不可逾越的紅線,一如既往地強調“有密必保、保密必慎、泄密必究”的原則。
二、欺騙:靈活化用孫子的“形人之術”
敵我對抗不僅體現為戰場廝殺、刀光劍影,隱蔽戰線的斗爭也一直非常激烈。除了采取被動的保密措施保守機密以外,敵我雙方都在極盡所能地使用欺騙等更加積極主動的手段。這有助于實現反情報的最終目的,即操控敵方情報機構,向對方傳遞虛假信息,進而誤導對方做出錯誤判斷。[25]
蘇洵清楚地認識到敵我雙方一直處于對抗博弈的激烈狀態,欺騙是掌握戰爭制勝權的重要手段,因此他分別從敵我雙方的角度展開了分析。他明確指出,“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26]。為了實現“滅宋”目標的契丹當前實力尚且薄弱,希望通過暫時維持與北宋和平局面來積蓄力量,它深知不能被看穿底細,否則便難以與實力尚存的北宋維持戰略平衡。契丹由此展開戰略欺騙,通過虛張聲勢來釋放自己實力強大的假信息,希望使北宋信以為真而有所顧忌。蘇洵透過現象看本質,一針見血地揭露了契丹處心積慮的騙術。此外,他還預測了雙方一旦開戰,契丹將會采取的戰術,即“一聲二形三實”[27]。所謂“聲”,即繼續虛張聲勢來威脅北宋,使北宋感到畏懼而被迫求和。若不奏效,便進一步施展“形”術,“除道翦棘,多為疑兵以臨吾城”[28],佯裝契丹將大兵壓境攻打北宋。最后的“實”,便是被逼無奈與北宋展開正面對抗。“聲”和“形”這兩種戰術,其中的核心都是情報欺騙,體現了敵方試圖通過制造和釋放假情報來誤導北宋做出錯誤判斷,進而喪失勝機。
北宋部隊也必須善于在作戰中廣泛施展騙術,要做到“吾之所短,我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卻;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29]。這種故意暴露己方不足之處,隱藏己方優勢的做法,就是為防范敵方刺探情報而展開的欺騙之術。這一方式可以有效欺騙迷惑敵方,轉移敵人注意力,達到讓敵方因懷疑而退卻甚至落入己方圈套的效果。在論述守城之法時,蘇洵提出的一個方法是:“令老弱登埤示怯,乘懈突擊,其眾可走,夫何患城小?”[30]讓老弱士兵登上城頭向對方示弱,目的是故意制造我軍疲弱的假象來迷惑敵方,使得敵人信以為然而放松警惕。這樣一方面可以掩蓋己方真實實力及意圖,很好地保護己方軍事機密,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尋找戰機,掌握主動,對敵人發起出其不意的攻擊。在蘇洵看來,這實乃屢試不爽的一大妙招,他甚至發出了“何患城小”的感嘆。
作為一位尊崇仁義的儒者,蘇洵對于戰爭中的欺詐理解得如此透徹,實際上反映出欺詐是客觀、廣泛存在于軍事斗爭全過程的,這早已為世人所公認。所謂“兵者,詭道也”[31],孫子最先揭示了這一真理,標志著西周以來“以禮為固”的戰爭觀念向“兵以詐立”演變,這在中國戰爭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對后世的戰爭觀都產生了深遠影響。與此同時,孫子基于“兵以詐立”的戰爭觀設計探討了各種旨在欺騙敵方、贏得戰爭主動權的詭詐之術,尤其是圍繞情報活動、以欺騙為中心內容的“形人之術”,在情報學術史上也具有引領風氣的作用。[32]蘇洵所理解的欺詐之術明顯地與孫子提出的“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33]有異曲同工之妙,可以說是他對孫子的靈活化用。此外,他的分析范圍不僅限于己方,也對敵方可能的意圖及計劃部署進行了合情合理的分析,是相較于孫子的“形人之術”的一大發展,更加符合孫子提出的“知彼知己”的思想。這對于我們打贏未來戰爭仍有很強的借鑒意義與運用價值,啟示我們不僅要善于使用欺騙開展反情報工作,同時也要留意敵方可能對我們開展的欺騙活動,提高警惕,避免陷入敵方故意設下的陷阱。
三、偵察:針對孫子用間觀提出新思考
在技術手段落后的古代,間諜是突破敵方保密防線、刺探敵方軍事機密的重要手段。因此孫子高度重視用間,將用間視為兵家必備之利器,對“五間”推崇備至,提出“三軍之事,莫親于間,賞莫厚于間,事莫密于間”[34]。在“五間”之中,孫子尤為重視“反間”,即策反敵方間諜為我所用,“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35]。從反情報角度,我們或許能理解孫子如此重視反間的原因。傳統的情報斗爭主要表現為間諜與反間諜斗爭,反情報活動的對象是敵方情報機構及情報人員,因此反間諜始終是反情報的一個方面。[36]反間的運用貫穿于從偵察到欺騙的全過程,不僅在偵察敵情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更在粉碎敵方情報活動方面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37]面對敵方的刺探偵察活動,依靠被動的拒止措施難以確保萬無一失。通過運用反間,便可以提前偵察并破壞敵方的情報偵察活動,有效地降低我方損失。如此看來,反間應當屬于現代反情報理論中的進攻型措施,對于反情報活動不可或缺。
孫子的用間理論對于中國古代情報思想史及古代諜戰史影響深遠,重視情報工作及用間,自此成為中國古典兵學的一個重要特征。[38]直至清代,朱逢甲在其所著《間書》中評述歷代間諜活動實踐時,相關的理論基礎和結構框架還基本依據《孫子兵法·用間篇》的有關論述。[39]蘇洵無疑也深受孫子用間思想的影響,例如他認可用間可以發揮顯著成效,甚至是贏得戰爭勝利的一個重要因素。但他并不完全贊同孫子“無所不用間”的觀點,而是更多看到了用間失敗的可能性。蘇洵認為,“故能以間勝者,亦或以間敗。吾間不忠,反為敵用,一敗也;不得敵之實,而得敵之所偽示者以為信,二敗也;受吾財而不能得敵之陰計,懼而以偽告我,三敗也”[40]。他不無憂慮地指出,用間可能會有三種失敗情況,不論是己方間諜不忠誠反被敵方策反,還是對敵方故意釋放的假情報信以為真,抑或是因不能獲取敵方情報而故意偽造假情報,都會對己方造成嚴重負面影響。其中的第一種失敗情況,即己方間諜不忠反被敵方策反,實際就是敵方成功對我方實施了反間,不但會嚴重破壞己方情報偵察活動,更可能會對己方辛苦打入敵方的其他間諜人員及組織帶來毀滅性打擊,使得己方情報機構花費大量時間、精力部署經營的一切都付之一炬。第二、三種失敗情況,更多是因己方間諜人員能力素質及心理素質欠缺而導致的。相較而言,第一種情況無疑是性質最為惡劣,后果最為嚴重的。正如上文對失泄密人員的評價,被敵方策反的間諜必須以叛國罪處之。相較于孫子最為推崇反間,蘇洵卻反其道而行之,他指出敵方也如同己方一樣重視反間,而這是孫子并未引起重視,或者至少是沒有過多著墨的。蘇洵并非是第一個對孫子用間觀提出異議的,杜牧在注解《孫子兵法》時曾有言:“間亦有利于財寶,不得敵之實情,但將虛辭以赴我約,此須用心淵妙,乃能酌其情偽虛實也。”梅堯臣指出:“防間反為敵所使,思慮故宜幾微臻妙。”[41]蘇洵雖然“務一出己見,不肯躡故跡”[42],但同時也具有博采眾長的精神,在用間問題上或多或少受到了前人影響。
蘇洵采取一分為二的辯證分析法,在繼承孫子的同時也對他的不足之處進行了批評,可以視為中國古代情報史上的一大進步。為盡量規避用間的不利影響,蘇洵主張必須使用“上智之間”,即有足夠聰明才智及能力素質的間諜。蘇洵的用間觀,讓我們意識到情報及反情報工作中人的重要性,必須要把提高相關人員的政治信仰、能力素質作為當務之急,同時始終確保人員管理及防范工作不松懈。今天情報機構開展人事安全(personal security)調查也正是出于這一考慮,該調查主要是判斷潛在雇員保守秘密的意志和能力,其中的關鍵因素是潛在雇員的性格和忠誠度,同時必須考慮個人的心理穩定性,以及其是否有被敵方情報機構敲詐利用或策反的弱點。[43]
四、結語
身為儒者的蘇洵,心懷家國,致力于鉆研兵學,以求為救國救民貢獻一份心力,他的兵學作品充分顯示出深邃的思想、遠見的卓識,包括審思明辨的這種精神,非常值得敬仰。毫無疑問,蘇洵在反情報等領域受到了孫子的深刻影響,基本繼承了孫子所構建的反情報理論體系,體現了孫子反情報思想具有超越時代的前瞻性及旺盛生命力。與此同時,蘇洵在充分吸收借鑒前人思想精髓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獨立思考,對孫子等前人的反情報思想進行了有益補充與發展。他突出強調了敵我反情報活動的互動及對抗,更加注重反
情報工作中人的重要性,對于今天的情報工作及反情報工作仍然具有極強的現實指導意義及應用價值。研究蘇洵對孫子反情報思想的繼承與發展,不僅有助于加深今人對先輩反情報思想的理解認識,厘清中國兵學思想及反情報思想的變遷發展;同時更有助于實現古為今用。我們要在立足國情的基礎上,充分吸收借鑒孫子及蘇洵反情報思想中的精華,加速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情報及反情報理論,為推動我國建設成為情報大國、情報強國添磚加瓦。
【注釋】
[1][美]艾布拉姆·N.舒爾斯基著,高金虎審校:《無聲的戰爭》,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159 頁。
[2]劉宗和主編:《中國軍事百科全書·軍事情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7年版,第198頁。
[3]高金虎:《試論反情報》,《保密科學技術》2013年第9 期,第23 頁。
[4]曾鞏:《曾鞏集》,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561 頁。
[5]高金虎:《反情報措施研究》,《保密科學技術》2014年第6 期,第4 頁。
[6]郭彧:《周易譯注》,中華書局2010年,第295 頁。
[7]陳鼓應:《老子今注今譯》,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207 頁。
[8]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56 頁。
[9]〔宋〕蘇洵撰,杜澤遜審定:《宋本嘉祐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版,第17 頁。
[10] 〔宋〕蘇洵撰,杜澤遜審定:《宋本嘉祐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版,第19 頁。
[11]〔宋〕蘇洵撰,杜澤遜審定:《宋本嘉祐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版,第19 頁。
[12]楊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孫子校理》,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19 頁。
[13]楊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孫子校理》,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264~265 頁。
[14]〔宋〕蘇洵撰,杜澤遜審定:《宋本嘉祐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版,第31 頁。
[15]楊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孫子校理》,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71 頁。
[16]〔宋〕蘇洵撰,杜澤遜審定:《宋本嘉祐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版,第25 至26 頁。
[17]楊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孫子校理》,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253~254 頁。
[18]熊劍平、梁舟:《孫子反情報思想研究》,《情報雜志》2020年第39 卷第2 期,第2 頁。
[19]楊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孫子校理》,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253-298 頁。
[20]郭化若:《孫子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93 頁。
[21]〔宋〕蘇洵撰,杜澤遜審定:《宋本嘉祐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版,第28 頁。
[22]楊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孫子校理》,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298 頁。
[23]楊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孫子校理》,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298 頁。
[24]孫劍波:《關于軍事保密本質問題的思考》,《保密工作》2018年第12 期,第44 頁。
[25]高金虎:《反情報措施研究》,《保密科學技術》2014年第6 期,第8 頁。
[26]〔宋〕蘇洵撰,杜澤遜審定:《宋本嘉祐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版,第20 頁。
[27]〔宋〕蘇洵撰,杜澤遜審定:《宋本嘉祐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版,第23 頁。
[28]〔宋〕蘇洵撰,杜澤遜審定:《宋本嘉祐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版,第23 頁。
[29]〔宋〕蘇洵撰,杜澤遜審定:《宋本嘉祐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版,第26 頁。
[30]〔宋〕蘇洵撰,杜澤遜審定:《宋本嘉祐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版,第28 頁。
[31]楊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孫子校理》,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12 頁。
[32]熊劍平、梁舟:《孫子反情報思想研究》,《情報雜志》2020年第39 卷第2 期,第3 頁。
[33]楊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孫子校理》,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12~13 頁。
[34]楊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孫子校理》,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296 頁。
[35]楊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孫子校理》,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300 頁。
[36]戴艷梅:《當代反情報活動概念的拓展研究》,《現代情報》2005年第11 期,第216~218 頁。
[37]熊劍平、梁舟:《孫子反情報思想研究》,《情報雜志》2020年第39 卷第2 期,第4 頁。
[38]熊劍平:《〈孫子兵法〉情報思想研究》,金城出版社2019年版,第113 頁。
[39]儲道立:《〈間書〉述評》,《軍事歷史研究》1992年第2 期,第124 頁。
[40]〔宋〕蘇洵撰,杜澤遜審定:《宋本嘉祐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版,第34 頁。
[41]楊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孫子校理》,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297 頁。
[42]曾鞏:《曾鞏集》,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561 頁。
[43]高金虎:《反情報措施研究》,《保密科學技術》2014年第6 期,第5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