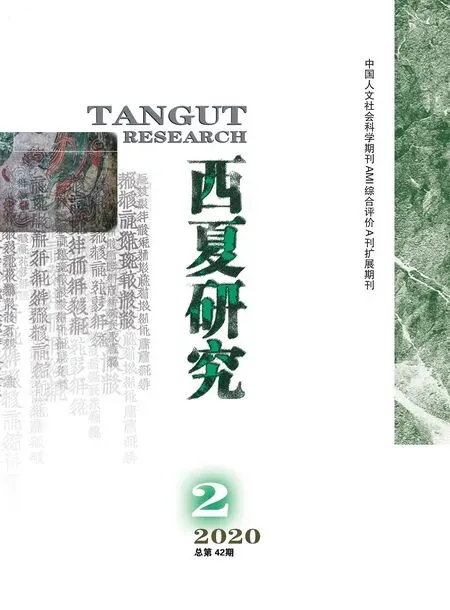西夏使臣群體小考
□劉維棟
西夏是一個以黨項為主體,包括漢、回鶻、吐蕃等族在內的多民族政權。黨項作為西夏政權的主體,憑借其出身優勢在交聘出使過程中往往占有主導地位,而其他民族在西夏出使活動中的作用與地位也是我們觀察西夏與周邊政權交往活動的重要角度。對于西夏與周邊政權交往的研究已有賢見①,但對于使臣群體的研究則鮮有論及。筆者不揣淺陋,希冀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西夏出使官員群體及其與周邊政權交往活動進行更細致地探究。
一、定難軍時期的官員出使
黨項定難軍政權時期就不斷派出使臣與遼、宋進行交聘往來,漢人擔任出使官員事例屢見不鮮。其中以張浦、劉仁勖二人具有代表性。宋淳化五年(994)“八月癸卯,(李繼遷)遣其將佐趙光祚、張浦詣綏州見黃門押班真定張崇貴,求納款。崇貴會浦等于石堡寨,椎牛釃酒犒諭,仍給錦袍、銀帶”[1]793;宋至道元年(995)正月二十八,又遣左押衛張浦“以良馬、橐駝來貢”[2]9941;至道三年(997)甲寅,“宋又以張浦為鄭州防御使,遣還”[1]896。作為漢人的張浦,在李繼遷時期深受重用,《東都事略》稱張浦為繼遷親校[3]1099-1100,宋朝宰輔也認為正是李繼遷“引親校張浦為謀主,軍中動靜一以諮之,遂能倔強窮廬茍延歲月者”[4]51。
劉仁勖也是繼遷時期重要的使臣。遼統和二十年(1002)六月,李繼遷派遣劉仁勖使遼通報其占領靈州[5]1531;宋景德元年(1004)正月,李德明任命劉仁勖為右都押牙[6]100;景德三年(1006)九月,李德明遣劉仁勖使宋奉誓表[1]1427;大中祥符五年(1012),劉仁勖建議李德明為先祖立尊號[7];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李德明“遣牙校劉仁勖貢馬二十匹”[1]2022。在西夏政權建立后,《大夏國葬舍利碣銘》碑陰刻有“尚書右仆射中書侍郎平章事、監藏舍利臣劉仁勖”[8]340,碑文為張陟所書,由此可見,劉仁勖從定難軍時期到西夏政權時期,歷仕三朝。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漢人擔任了定難軍政權的使臣官員。如:遼統和十九年(1001),“繼遷遣李文冀使遼進貢”,此李文冀當為李文貴之誤[5]1525,且有宋景祐四年(1037)“元昊遣李文貴赍野利旺榮書來送款”[9]10200。宋景德二年(1005)六月丁亥,“夏州趙德明遣牙將王旻奉表歸款,宋賜旻錦袍、銀帶,遣侍禁夏居厚赍詔答之”[1]1345;九月“趙德明始遣其都知兵馬使白文壽來貢”[1]1364;十二月“趙德明又遣其教練使郝貴來貢”[1]1380;次年五月,相繼遣“兵馬使賀永珍”、“遣兵馬使賀守文來貢”[1]1398,數次遣使來往是因向敏中、張崇貴與德明訂立誓約之故。
從現有的資料來看,定難軍時期的出使官員以漢人官員為主。如張浦等多次出使,既間接反映出定難軍政權內的官員構成,也能說明當時其受到了強大的外部壓力需要頻繁派出使臣斡旋捭闔。以漢人官員為主體的使臣群體與李繼遷時期就廣泛招募漢族儒士有直接的關系,時宋朝兵部尚書張齊賢向真宗諫言:
遷賊包藏兇逆,招納盤亡,建立州城,創制軍額,有歸明、歸順之號,且耕且戰之基,仍聞潛設中官,全異羌夷之體,曲延儒士,漸行中國之風。[1]1099-1100
雖此奏疏對黨項李繼遷充滿敵視,但從另一方面可以表明定難軍政權人才政策的成功。作為“對手”的評價,從反面可以觀察出當時漢人官員的顯要地位與發揮的關鍵作用。漢人儒士持續進入與被重用也對西夏建立后的官員結構形成重要影響。
二、西夏政權中的出使官員
在定難軍政權中擔任過使臣的官員,在西夏建立后,自然也隨之入仕西夏政權。如前文之李文貴,慶歷元年(1041)“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城”;次年宋朝令龐籍與西夏議和,“元昊使文貴與王嵩以其臣旺榮、其弟旺令、嵬名環、臥譽諍三人書議和”;三年,元昊“遣六宅使伊州刺史賀從勖與文貴俱來。”[9]13996
投奔西夏的漢人也曾擔任出使任務。西夏天授禮法延祚三年(1040)五月“取塞門砦執砦主高延德,遂破安遠諸砦”[6]162。其后,西夏遣“前所執塞門砦主高延德求通和”[3]1101。任得敬“本西安州判,夏兵取西安,率兵民出降,乾順命權知州事”[6]402。西夏仁宗時期任得敬及其家族備受重用,權傾一時,西夏天盛十九年(1168),因金朝御醫醫治好任得敬之病,西夏遣“謝恩使任得聰來”[10]2869,任得聰為任得敬之弟,也屬于投奔西夏的漢人群體。
通過對西夏出使遼、宋、金使臣的統計,按照學術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將出使官員大致可分為番姓官員和漢姓官員兩大類[11]。
(一)使遼官員群體
囿于資料的限制,西夏出使遼的使臣姓名大多數沒有記錄,統計西夏使臣一共出使遼朝66次,記載姓名者14人次,其中漢姓官員為12人次,占比為85.7%②。
依據記錄使臣的官職分析,漢姓使臣的官職有御史中丞、殿前太尉、秘書監等,是明顯具有中原王朝特點的官職稱謂,而同在乾順時期出使宋朝官員的官職稱謂則多是番語官職。
從出使的目的來看,除請師、入貢、進表等任務外,夏使赴遼請婚也是使臣的重要任務。元昊與遼興平公主有婚在前,且自崇宗乾順即位后,夏遼關系明顯緩和且有復盟趨勢[12]97,因而乾順把迎娶遼朝公主的重任交給了李至忠、梁世顯二人。李至忠官職為殿前太尉,而梁世顯則供職于秘書監,二人一文一武,顯然是獨具用心之選。遼主曾問乾順為人,李至忠對曰:
“秉性英明,處事謹慎,守成令主也。”遼主善其對,命徐議之。[6]360
這次奏對雖沒有得到肯定的答復,但博得了遼主的好感,使臣之使命也算是有始終焉。在宋攻西夏的情勢危急之際,夏崇宗派李造福三次入遼乞援,把軍國重事系于李造福一身,最終求得遼朝從中斡旋,使得宋朝罷兵。后在遼朝生死存亡的時刻,西夏又派遣大將李良輔率兵救遼,李良輔消滅了金將婁室的斥候兩百騎,后戰敗退走[10]1650。漢姓官員在夏遼關系中作用可見一斑。
(二)使宋官員群體
首先,據現有的資料統計得出西夏官員共出使宋121次,其中未記錄或記載不清使臣姓名的次數為65人次,有記錄使臣姓名的56人次,其中漢姓官員為36人次,在有記錄的使臣中占比為64.3%。這一數據說明漢姓官員在西夏出使宋朝官員群體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并且是延續了定難軍時期漢人官員出使的規律與傳統。
其次,漢人官員在西夏建立初期的對外交往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通過統計可知,西夏建立初始有記錄的使宋使臣為26人次,漢人官員人數為20人次,占比高達76.9%。雖在此較為有限的數據內,也可窺測一二。張延壽、楊守素、張文顯這些有相當職位的顯宦重臣及李文貴、賀從勖等元昊親信頻頻出使,說明了漢人官員在出使任務中具有明顯優勢,出使目的是在夏、遼、宋復雜的政權關系中為西夏爭取較為有利的外部環境。如:楊守素在1044年至1046年先后五次出使宋,究竟是何原因呢?遼興宗在重熙十三年(1044)九月,以皇太弟重元、北院樞密使韓國王蕭惠將先鋒兵西征西夏[10]231,原因是原遼屬呆兒部叛逃西夏,遼興宗遣使要求西夏歸還,元昊不聽,所以遼興宗遣三路大軍征西夏[9]13999,這次征伐在此年八月之前。在同一時期,西夏與宋也多有爭端,同時與兩大政權交惡,西夏定無法承受此等壓力。所以,在此時派遣楊守素使宋上誓表、請誓詔,再進行談判,是緩和夏宋關系的重要環節。如此頻繁出使是希望能在此時期迅速解決宋夏爭端,減輕宋朝對西夏的壓力。
再次,統計使臣出使宋時的所帶官銜有“供備庫使、牙校、教練使、六宅使、伊州刺史、呂則依、慶唐、樞銘、宣徽南院使、河北轉運使、刑部郎中、呂寧、呂則、昂聶、廣樂、謨程”等。其中“供備庫使、牙校、教練使、六宅使”等明顯是繼承了唐宋以來職官名稱稱謂,“呂則依、慶唐”等則是番官名號,不同語言稱謂的職官名號顯示了西夏文化和民族政策的包容性與開放性。
(三)使金官員群體
西夏自崇宗乾順元德六年(1124)派使臣出使金至末帝睍乾定四年(1227),計103年,使臣出使次數為198次,每次派遣使臣一般為2人,除了少數年份因夏金爭端沒有通使外,基本每年都有派使臣前往。其中有使臣姓名記錄的為253人次,漢姓官員187人次,占比為73.9%。
從總體來看,自崇宗乾順后期到神宗遵頊,西夏使金逐漸制度化。出使人員與次數并沒有像入遼、宋使臣那樣同一人連續多次出使。蓋是這一時期西夏官制已日趨成熟,并且有相應的制度規范。且祝賀的使臣的職位基本固定,有特殊如告哀、賀即位、謝賜等派出的特使,職位較一般節日祝賀使臣要高。出使官員所帶官銜一般為唐宋官制名稱,并無番官名號。
由于出使次數和使臣姓名記錄較為完整,可以從使臣姓名中發現一些線索,即:家族式參與外交出使活動。如:出使的番姓官員中“芭里公亮、芭里昌祖、芭里慶祖”可能三人是同屬一個家族,家庭地位相仿。同樣,在出使的漢官中也存在此現象,如“蘇執義、蘇執禮”、“劉進忠、劉思忠、劉執忠”、“楊彥敬、楊彥和、楊彥直”等諸多案例。《西夏書事》記錄楊彥和是楊彥敬之弟,梁宇是梁元輔之侄,劉進忠是劉思忠之弟,劉志直是劉志真之弟。如若書中所說關系不誤,這種家族式充任出使官員的情形,不但表明了西夏內部原針對非黨項官員限制的政策被打破,而且漢姓官員與番姓官員在任職、任務、家族入仕等方面可能享有同等權力,西夏政治中后期整體呈現一種具有廣泛性與包容性的番漢一體的特色。
從出使官員任職來看,西夏政權內部官制構成逐漸豐富完善。在出使遼、宋時曾見到金吾衛上將軍、匭匣使、翰林學士等官職多次出現,說明西夏政權內部的職官體系化、制度化,逐漸臻于完善。而且,在西夏末期出現了“光祿大夫吏部尚書、徽猷閣學士、尚書省左司郎中”等并不見于前朝的官職,更能說明西夏此時的職官制度與中原王朝趨于一致。
從出使的目的來看,大部分漢姓官員出使的目的都是日常的節日祝賀,如賀正旦、萬壽節、萬春節等,夾雜特殊使命,比如賀即位、謝封冊、謝橫賜、告哀、乞免索人口等。尤其是西夏仁宗到神宗期間,基本沒有發生過停派使臣的情況,這種長時間的交聘往來,表明了雙方關系的穩定。但是在乾順二十年、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金世宗殂,章宗即位,禁停了與西夏的使館貿易,西夏與金關系緊張,并發生沖突[10]2870,在次年的賀正旦中,西夏正使所攜官銜由原先之“武功大夫”改降為“武節大夫”,這種兩國關系的變化,在使臣及其身份中得以充分地體現。
特殊任務的出使還能反映出西夏內部權力斗爭的變化。天盛十九年到乾祐元年(1167—1170)三年四次關于任得敬的出使可謂是有力證明。天盛十九年(1167)為任得敬請醫時派出了殿前太尉芭里昌祖、樞密都承旨趙衍組成的使團,專派使團為大臣請醫治病,既是對大臣的重視,也可能是大臣權力熾盛,皇帝對權臣失去了約束能力。任得敬病愈后,西夏派出任得聰使金謝恩,任得敬也附表貢物謝恩,但金世宗下詔拒絕其禮物[10]1425。這一舉動能坐實了仁孝事實上已經失去了對任得敬的控制,而任得敬派遣任得聰附表謝恩,其意在揣測金對其態度。但正是金世宗的拒絕,逼迫任得敬轉而尋求另援,當年五月,派人入四川向南宋示好結援[9]643。乾祐元年,仁孝派左樞密浪訛進忠、翰林學士焦景顏為得敬請封,這次派出的使臣更是耐人尋味,焦景顏曾面斥任純忠奸仁[6]430,意味著其對任得敬家族并無好感,且金世宗再次拒絕此次冊封任得敬[10]2869。筆者認為實際上是仁孝一開始本就不希望金冊封任得敬,苦于無奈而不得不妥協允許任得敬派人使金。仁孝誅殺任得敬后,又立即派殿前太尉芭里昌祖、樞密直學士高岳入貢謝恩。四次出使,將任得敬集團與仁孝的雙方角逐較為完整地反映出來,可見使臣群體、出使任務與西夏政治之關系。
三、余論
漢姓官員并不一定就是漢人,我們對此有清楚地認知。例如西夏的李氏有三類:一是西夏皇帝的姓氏;二是李姓的黨項人,如“李顯忠、李訛移巖名”等,李顯忠是黨項九尾族的首領;三是生活在西夏的漢族,如“李青、李良輔”等[13]174-175。但從使臣群體姓名統計來看,漢姓使臣官員占據了絕大多數,并呈現家族式擔任使臣的現象,漢姓在西夏使臣群體的流行也體現了其社會漢化、儒化的程度不斷加深。從漢人到漢姓,群體范圍由單一的漢人逐漸發展為以漢姓為標志的西夏各族,究其根本,則是西夏域內各族群對以漢文化為核心的中華文化的一種認同。
西夏使臣群體,展現了突厥、粟特與黨項、漢等多族群交融的趨勢。鐵勒渾部自唐代開始就逐漸自漠北南遷之靈鹽與河西地區[14],且其首領屬眾同許多突厥部落一樣多以部名為姓。以此為線索,考得西夏仁宗天盛二十一年(1169)使金賀正旦的武功大夫“渾進忠”、襄宗應天三年(1208)武節大夫“渾光中”二人。渾部本就活動在漠南、河西地區,其后裔入仕西夏自然也是順理成章,但囿于資料所限,有待進一步考索。西夏重鎮靈州、夏州自隋唐以來就是西域粟特人居住、停留的重鎮,因此西夏境內有粟特人后裔更是自然之事[15]。有學者考證在定難軍時期就有粟特人后裔及其家族人員在政權內擔任官職③,米、康、安三姓一般比較容易理解為粟特后裔,且“由于粟特人的語言天才,自北朝以來,入華粟特人的一個重要角色就是充當不同國家、民族間的使者和翻譯”。[16]235-240金世宗大定六年(1166)正月丙午朔,“夏武功大夫高遵義、宣德郎安世等賀正旦”[10]1422。且俄藏TK142《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愿品發愿文》中記載,施主安亮為了紀念母親,“特命工印《普賢行愿品經》一萬有八卷,給彌陀主伴尊容七十有二楨”[17]174,可證粟特后裔安氏在西夏并不鮮見。金泰和五年(1205)八月“夏遣武節大夫趙公良、宣德郎米元懿賀天壽節”[10]1474,泰和八年(1208)十月“夏武節大夫李世昌、宣德郎米元杰賀天壽節”[10]1480。《西夏書事》載“元杰,秘書少監元懿弟”[6]466。若所說不誤,可推測粟特人后裔及其家族在西夏外交中繼續發揮著重要作用。
注釋:
①李華瑞《宋夏關系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328-369頁;楊浣《遼夏關系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05-240頁;馬旭俊《金夏關系研究》,吉林大學文學院博士論文,2017年;杜建錄《西夏與周邊民族關系》,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7年。
②本文所得使臣出使數據是基于《遼史》、《宋史》、《金史》、《續資治通鑒長編》、《西夏書事》、《西夏與周邊民族關系》等文獻與研究著作綜合統計而成,統計指標依據為《西夏姓氏輯考》中所列漢姓部分。由于能力有限,難免掛一漏萬,敬請方家指正。
③陳瑋《后晉夏銀綏宥等州觀察支使何德璘墓志銘考釋》,《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年第3期;戴應新先生在對康成墓志考釋時未指出康氏粟特后裔的族屬身份,見戴應新《有關黨項夏州政權的真實記錄——〈記故大宋國定難軍管內都指揮使康公墓志銘〉》,《寧夏社會科學》,1999年第2期;榮新江先生認為康成為粟特人,其應為當地的胡人領袖,見榮新江《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
A Study of the Diplomatic Community in Xix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