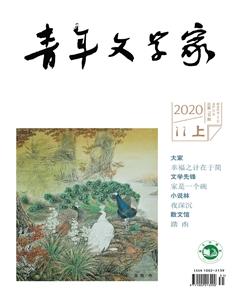家的感覺
翟穆峰

在外打拼久了,便想回家保養一下自己的心靈。
每次回家,我總感覺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人,父母健康使我安然釋懷。盡管父母親年歲已高,但他們能相互照顧地生活著,也能安度晚年,我沉浸在一種滿足感之中。
每次回到農村,雖沒有城里的人氣與喧囂,但鄰居們都喜歡來我們家嘮嘮家常,也驅散了老屋長期的寂寞和冷清,鄉親鄰居們的和睦相處,讓常年不在他們身邊的我有了一份放心和慰藉。
在家里,父母的愛讓我內心充滿溫馨。他們總是做我最喜歡吃的飯菜,喝最好的茶。其實回到家里,簡單的生活才是我的追求,一是怕勞累他們,二是現在生活水平提高,魚肉葷菜吃多了對身體也是負擔。但母親總要做幾道菜,看著我高興地吃著,總要輕輕地問一下,可口嗎?有味嗎?咸淡如何?我總會說,非常好吃!她的臉上溢滿了笑容。在家里,什么都不用想,那種“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感覺,讓在外工作的我緊張的神經一下松懈了許多,因為哪怕天塌下來,我也用不著擔憂,父母在,就有靠山,就有歸宿。
老家屋前屋后種著各種各樣的新鮮蔬菜,美味可口。在城里無法購買到,每次回城市總要帶上家產的蔬菜,可惜蔬菜保鮮期有限,不能帶得太多。每次回到城里,又分享一部分給鄰居,農村的蔬菜新鮮、干爽、可口,比城里的蔬菜不知好吃多少。
生活在農村,不用考慮交通和工廠造成的大氣污染,在城里待久了總想去農村住住,而生活在農村的人總想到城市打拼,這也是圍城心理。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城市化進程加快,年輕人不再守著鄉村,留守在農村的均是父母輩老人,他們守候著日夜依戀的家園。每當回到老家,一張張被歲月侵蝕的面孔,飽含著世間的滄桑,有時我都認不出他們,一陣寒暄之后才恍然大悟。
初秋時節,走進田野,遠遠看去壟上像是飄雪,哪怕是夜晚,那白色的熒光也能遠遠朦朧地看到,走近仔細一瞧才知道那是芝麻花。這讓我想起杜甫的《江畔獨步尋花》: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
農村人有早睡早起的習慣,天還沒有亮,家家雄雞就競相報曉,這種脫離工業化的農村,一種自然的天籟打開新的一天。難得在家過一宿,聽著它們的聲音,仿佛時間還停留在七十年代,仿佛沒有了時間追趕的速度,安詳、柔順、按部就班迎來村民的開門聲。
看著家,想著過去的熱鬧,河東學校每天瑯瑯的讀書聲,下課孩子們在操場上的歡笑,那種歡樂不時地侵襲著我。而現在只是深沉,看著地磚上的青苔,總覺得有一種看不見的底蘊。
家給我力量,給我智慧,給我人生的希望。在我受到挫折時,最能醫治我內心的傷痛。它又是心靈的港灣,每次回家后,都好像重新獲得動力,好像又年輕幾歲。父母健康地生活著,是我平凡生活創造不平凡成就的堅強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