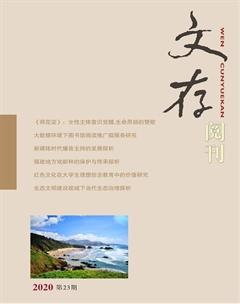主體意識哲學范式的式微與轉向研究
摘要:歐洲主體意識哲學主客體關系中只能生發出工具理性,主體意識哲學范式已然過時。維特根斯坦認為,傳統形而上學所追求的“存在”或最高的目的在理論策略建構中很難以達成一致,其最重要的原因是用語言來論證、描述的,我們應該暫且不要去探討對象本身,而是應當回頭探究對此問題的闡釋或表述。哈貝馬斯認為,我們應在體現于“生活世界”行為、認識和語言中的合理性去將其認識和把握,程序合理性基礎上的普遍達成共識則成為人們追求美好生活的必要前提。
關鍵詞:形而上學;主體意識哲學;范式式微與范式轉向;生活世界;合理性
一、主體意識哲學范式的式微
面對哈貝馬斯之前歐洲哲學家們理論研究時所遭遇的理論困境或達到了某種無法超越的極限,我們可以得出此“水到渠成”的結論:主體哲學、主體意識哲學這種范式已然不符合當代歐洲的要求,傳統主體哲學范式須要進行范式轉向。有學者認為,康德是歐洲現代哲學的開端,黑格爾是古典哲學的終結,此種理論判斷是合理的。古典哲學康德哲學的理論傾向是更多的從理性的形式上和程序上對哲學進行的考察。譬如,人類對經驗的認識,康德考察的是人類的經驗怎樣才能被建構起來,經驗作為每個人都有的現實的東西,他要考察的是我們經驗的構成如何可能。經驗要有感覺,感覺要有現象,通過感性直觀形式的滲入且進行整合。無論是直觀形式還是知性認識中的先天范疇,都是形式,其實踐理性也是形式。理論理性是確定的,因為,我們在理論理性此意義上得到的先天綜合判斷、科學知識,它就是通過我們知性的范疇建構起來的現象領域。康德認為,科學知識是關于對象的,此對象需要一個物自體但不是物自體,不是自然本身,而是自然呈現給我們的現象,因為,此領域就是我們主體構造起來的,知性為自然立法。因此,我們可以對此加以確定。這個領域是有限的,但人類的精神則是在追求無限,追求無限就意味著須超出必然性,超出必然性就為自由留有空間,可以選擇。可以選擇就是人類這個特殊的有限存在者的基本特點,有限的人類不甘心于自己的有限。人類又是理性存在者,其理性可以追求無限。在理論史的考察中,某位理論家的理論在歷史上被留存和反復被談及,其中的關鍵緣由是其理論在某個視角、方面或層面拓展了一定的理論范圍或空間,這個視角、方面或層面在理論研究中還是有其重要意義,只是此意義未曾被人們看清楚或者被人們遺忘了,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之中。亦或是,今天在理論研究中,又重新發現其重要性而再次探究和挖掘其研究價值。費爾巴哈從身體的角度,生物學的角度來看待人,其理論相對于觀念論而言則是異類,在觀念論研究氛圍內就很快被淹沒。到20世紀40-50年代,人們發現身體這個維度很重要,就又被重新挖掘出來進行研究。在哲學史或理論史中,某位哲學家或理論家的為論證理論觀點或自成的理論體系,其內容很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從其內容中去體會或提煉出其開創的某個維度或某個方法論的創造性。今天來講,歷史中有很多理論內容(不是全部)略顯過時。比如,泰勒斯認為,水是世界的本原,其內容上早已過時,但人們仍在研究的重要原因是,他開創了哲學這個新的維度:跳過神話解釋而通過自然本身解釋自然,哲學的開創是按照事物本身的原理去說明事物。歐洲哲學史到了近代,因眾所周知的緣由,歐洲人文主義精神興起,強調人的主體性就成為近現代歐洲哲學的核心思想或核心觀念,理論上、哲學上為了論證此核心觀念,以人的主體、人類主體為基礎的這種理論建構方法就比較高度契合人文主義精神,人文主義精神在近代就表現為主體哲學形式,這種理論策略。就此以后,哲學家們就在主體這個意義上進行了哲學建構。而“人”在笛卡爾二元論那里則表現為物質實體和人類所特有的精神實體,“我思”意識實體,他所奠定的那個主體基礎,以“我思”以意識為基礎的哲學。這僅僅是基礎,它又要解釋心與外在自然這個物質的關系,其心物二元論只是搭建了一個架構,且存在此架構,欲建構主體意識哲學就必然會有主客體關系。笛卡爾沒有解決好主客體關系或者他未曾想到要解決主客體關系的問題。主體怎樣去把握客體以及客體如何進入主體,他對此關系的處理或解決實則是失敗的。上帝設定了客體的規律和主體“我思”的規律是一樣的,先定和諧。因此,我們通過主體的自我意識能發掘主體或客體的規律,以此解決二者關系問題,此問題到康德那里得到了解決:知性為自然立法。黑格爾將笛卡爾開創的主體意識哲學推向了極致,從主體哲學策略和框架中最后達致總體,總體即本原,解決了現代性的所有哲學問題。《精神現象學》導論中,黑格爾用辯證法論證了實體即主體,從主體出發來建構一個包羅萬象。形而上學所追求是“實體”而非其他,“實體”是自己成為自己的原因,而“實體”不是顯現的事物。在黑格爾眼中,“實體”不是某個東西,而是全過程的整體,現成事物只是片段或階段,它要轉變為其他事物,它和另外的事物構成一個全體才是實體本身。主體處于變化之中,每個階段或層面的的變化到最后則構成整個人類的存在和知識的全體,是主體哲學的完成。阿多諾他們對這種主體為前提的哲學同一性批判,揭示出了這種理論策略最根本的局限性。主體哲學到最后即是自我捍衛的概念,主體是“自我捍衛” [1]自我捍衛是黑格爾的判斷:主體即實體,主體就是自我捍衛,自己成為自己的原因,它即是目的本身。
“阿多諾恰恰說明,如果我們只用意識哲學所提供的十分激進的范疇來考察,‘有意識生活的基本過程,我們所堅持下來的也就不過是工具理性”。[2]意識哲學的基本架構為主客體,而主客體關系中能生發出來的不過是工具理性,只能生發出工具理性,而工具理性此概念在法蘭克福學派理論中是批判性的概念系統。由康德奠定的現代性人類理性其他方面則無法進入這種主客體關系之中,用主客體關系意識哲學架構無法推出或論證其他理性。
二、語言學轉向
20世紀以來,歐洲社會批判理論存在一些理論轉向,其常見的是語言轉向、后現代轉向、社會批判理論轉向和倫理學轉向等,這些理論建構策略發生的轉向,究其目的而言是為了解決歐洲社會問題、人的生存問題、認識論問題以及其他的傳統哲學問題等等。語言轉向被認為是具有某種根本意義上的轉向。在傳統語境中,人類所面對的被認為是面對知識本身,我們可以談論或者探究對象本身,在后來,人們發現對這些傳統的哲學對象的討論或探究何以存在諸多重大分歧?傳統形而上學所追求的“存在”或最高的目的在理論策略建構中為什么難以達成一致?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們沒有直接對此對象加以討論,而是用語言來論證、描述或表達的。“在傳統的概念范圍內,導致非同一性悖論或反思性意識悖論的那些現象,只有用語言分析的方法才能得以克服”。[3]這種轉向,究其基本思路上,構造理論的基本策略思路上發生的巨變,在哈貝馬斯眼中,它發生了什么變化?傳統哲學所探究的對象,理念、實體、自我意識等通常是經語言理論論證所建構起來的,譬如,同樣都探討或使用“實體”這個哲學概念,無法通過感性直觀此抽象的“實體”,這是不同的哲學家通過抽象思維構想出來的或者被設定出來的,關于此形而上學“實體”對象的設定,哲學家們就會根據其不同視角、背景等用其自身的獨特語言對此加以論證或描述。因此,語言學轉向以后,哲學家們回過頭來面對和研究自身的語言的使用問題,暫且不去談論此探究兩千多年仍未認識清楚的對象本身,其中以維特根斯坦是其重要理論代表。維特根斯坦將哲學首先稱謂為“治療”的一種方法,哲學是治療語言表述的“病”,大量語言在他看來,都是有病的,有矛盾,不成立的,因而是毫無意義的。對此,他認為,我們應該暫且不要去探討對象本身,而是應當回過頭來探究我們對此問題的闡釋或表述,在語言方面是不是存在問題。
結語:
哈貝馬斯站在現代性立場接受和認可了前人的一些觀念與理論論證,比如,康德對現代性理性重要的三個層面區分,而當前的理論任務是按照黑格爾、馬克思等等理論家的方案去論證此三方面如何可能,或者建構某個系統方案去更好地解決歐洲現代性所存在的問題,以達致最終的解決。哈貝馬斯對這些現代性哲學問題的思考,采用了“合理性”而不是歐洲傳統的理性概念。由柏拉圖劃分的理念世界即是形而上學意義上的理性概念,它是實體性的,“實體性”是自主自為的存在,它構成了一個自主自為的可以和現實世界區分開來的理念世界。而社會學意義上的合理性概念則不能與人的存在以及人的行為分開,它是人的社會性存在的功能或能力而不是一個構成實體性存在。這種作為功能的合理性則體現于人存在本身的行為、認識和語言之中。在人的此活動中,不符合合理性的即是奇怪的,理所當然應被拋棄或批判。合理性概念也就而成為評判人社會存在與社會行為的重要標準或規范基礎,而此規范基礎就不再是實體性領域,不認為有個最高的形而上學實體的存在而去將其把握。形而上學的方法已然不符合當今歐洲的要求,我們應在體現于行為、認識和語言中的合理性去把握和認識它。后形而上學以后,歐洲社會理論或社會批判理論的典型表達為重建,重建科學就要從理論上去把握行為、認識或語言過程的合理性,后形而上學以后,這種重建就要求將其內部發展的邏輯表述清楚。重建科學應同自然科學的實證科學有所區別,具體的實證科學有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等各種存在者或對象,這些對象是存在者,很容易通過實證的方式得以把握。重建科學也要和形而上學區分開來,形而上學追求的相當于自然科學,它追求無限的最高的本質性對象。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既非自然科學,也非對傳統形而上學“存在”追溯和糾纏。哈貝馬斯認為,傳統形而上學“存在”是不存在的,轉而立足于人類社會“存在”生存本身,將人類的生存本身作為考察對象,人類生存應以合理性概念作為標準對其進行批判性考察。合理性概念不是科學與傳統形而上學認識和研究的對象,而是需要理性重建或重構的對象,這些理性重構的對象是動態的形式標準,它與康德的“靜態”標準有著較大差異,我們的知識認識從感性直觀到知性的結構描述是怎樣的,康德給出了重要的哲學理論闡發。哈貝馬斯對“合理性”能力的產生還要進行批判性考察,原有傳統世界觀存在許多不合理之處,今天對作為現代世界觀內涵的合理世界觀的產生須進行追問和探究,傳統世界觀向現代世界觀的轉向成為重要的理論命題。合理性不再是傳統實體性理性概念,而是體現于人們的行為、語言和認識之中,這就有四個不同的種類,這四個不同種類(目的行為、規范行為、戲劇行為與交往行為)就有與其相對應的不同的合理性標準。哈貝馬斯將自己的重建理論從以主客體為理論架構的主體意識哲學轉向以主體間性為規范原則的“生活世界”的合理化過程研究。“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就使得“生活世界”中最主要的金錢系統和權力系統間矛盾的整合與調節成為可能。主客體架構的反思被主體間交往中介的程序合理性所代替,承認基礎上普遍達成同意共識則成為人們追求美好生活的必要前提條件。
參考文獻:
[1][2][3]哈貝馬斯. 交往行為理論[M]. 曹衛東 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379.
作者簡介:
岳勝(1980— ),男,四川遂寧人,法學碩士,講師,川南幼兒師范高等專科學校思政部教師。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