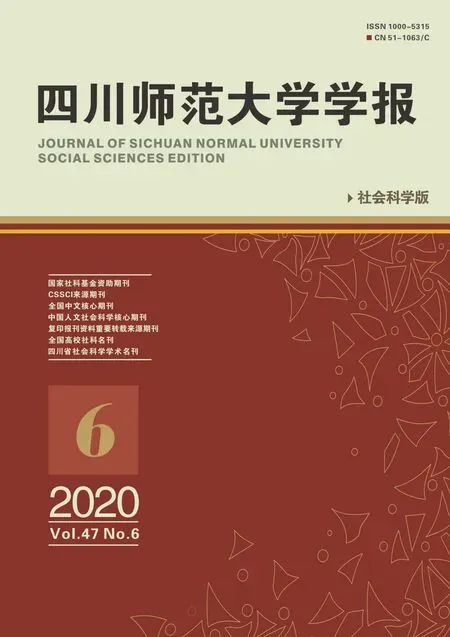客觀本真與存在本真的互動:川藏線騎行旅游研究
王汝輝,馬志新
(1.四川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成都610066;2.暨南大學 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處,廣州510632)
“我看到了川藏線……沿途的山山水水,風土人情……騎行,像夢境一樣吸引著我。我要騎行川藏線!時光推移,更多深陷繁華城市的你我,也許早已忘記了當初的夢想……你要翻過的,只是心中的那一座山!”這段內容節選自川藏線騎行旅游知名旅游指南《波爾攻略》扉頁,恰如其分地表達出旅游者對川藏線騎行旅游的期待與向往。被譽為“中國最美景觀大道”的川藏線(G318)是中國目前最受歡迎的騎行路線之一,但騎行川藏線更意味著艱巨的考驗。川藏線全程2142公里,騎行途中需翻越海拔5000米以上高山2座、4000米以上高山12座,還需面對高原缺氧、天氣復雜多變、地質災害及次生災害頻發等諸多困難。川藏線騎行旅游融合自然和人文景觀體驗與高難度自我挑戰于一體,可以稱得上國內難度系數最高、騎行強度最大的線路,然而不少旅游者仍表現出極大的熱誠,甚至將騎行川藏線視為生命歷程中的重要里程碑。透過這個現象,我們不難看出,川藏線騎行旅游者真正追尋的絕非僅僅是外在客觀的“新奇特”自然和人文景觀,更多地發自旅游者內心的挑戰和感悟:“騎行到后半段,每天已不再關注景觀,重要的是騎行過程本身以及騎行所帶來的震撼、洗禮和感悟。”(CZX-07)(1)CZX表示受訪者具有川藏線騎行旅游經歷;07對應表1訪談對象基本信息中的編號。下文訪談編號類似。由此,一個極富理論價值的問題浮現在我們腦海中,騎行者“心中的那座山”是什么?旅程中“客觀存在的山”與旅游者“心中的那座山”到底存在什么樣的關系?促使川藏線騎行旅游者由外而內轉向的動力機制是什么以及是如何建構的?探討這些問題,本文認為有必要回到本真性旅游體驗理論框架內進行思考。
一 文獻回顧與述評
(一)客觀本真與存在本真
本真性是旅游體驗和旅游動機中的一個核心問題(2)王寧《旅游中的互動本真性:好客旅游研究》,《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6期,第18頁。。它既是解釋旅游動機的一個重要范疇,也是描述旅游體驗的一種重要感知(3)焦彥、臧德霞《現代性與真實性的結合:入境游客對旅游配套設施的體驗研究》,《旅游學刊》2015年第10期,第28頁。。其概念的發展歷經客觀本真性、建構本真性、后現代本真性和存在本真性四個階段。客觀本真性將本真體驗視為游客對旅游客體“原作品”真實性的認知體驗,其衡量標準為旅游客體自身的真實是否得到呈現(4)Dean Maccannell, “Staged authenticity: Arrangement of social space in tourist setting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9, no.3 (November 1973): 595-599.。建構主義則將旅游者的本真性體驗看作是游客對客體真實性的社會建構過程和結果,同一個旅游客體的真實性在不同旅游者眼中具有多種形態(5)Erik Cohen, “Traditions in the qualitative sociology of 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5, no.1 (January 1988): 36-37.。后現代主義學者認為,基于人們想象、幻想創造出來的迪斯尼樂園,受游客追捧,充分說明原物與仿造、符號與真實已無差別,因此旅游者并不在乎“原作品”真實與否,他們追求的是一種超現實的“逼真”(6)科恩《旅游社會學縱論》,巫寧、馬聰玲、陳立平譯,南開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頁。。存在主義論者鮮明指出,旅游者并不關心旅游客體真實與否,他們只是借助旅游活動和旅游客體尋找本真的自我,存在本真包含自我內在本真性和人際本真性(7)Ning Wang, “Rethinking authenticity in tourism experience,”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6, no.2 (April 1999): 361-365.。由于客觀本真性、建構本真性和后現代本真性均將旅游體驗的本真性與旅游客體的本真性相聯系,沒有脫離對象化的客體而存在,本質上皆屬客觀本真性范疇(8)趙紅梅、李慶雷《回望“真實性”(authenticity) (上) ——一個旅游研究的熱點》,《旅游學刊》2012年第4期,第17頁。;而基于存在主義哲學視角的存在本真性,揭示了不依賴于客體真實與否,經由旅游活動激發旅游者存在本真體驗的重要性(9)Ning Wang, “Rethinking authenticity in tourism experience,”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6, no.2 (April 1999): 361-365.。綜上可知,存在本真性與客觀本真性的核心區別在于是否依賴對象化客體,存在論者認為本真體驗的獲得與客體本真毫無關聯,旅游客體和旅游活動僅僅是旅游者獲得本真體驗的工具或手段而已。
(二)本真性旅游體驗研究
早期本真性體驗研究集中在作為旅游吸引物和產品的本真性(10)盧天玲《社區居民對九寨溝民族歌舞表演的真實性認知》,《旅游學刊》2007年第10期,第89頁。、旅游活動的本真性(11)高燕、鄭焱《鳳凰古城景觀真實性感知比較研究——基于居民和旅游者視角》,《旅游學刊》2010年第12期,第44-46頁。,甚至注意到旅游者對配套設施和服務的本真體驗(12)Muchazondida Mkono, “A netnographic examination of constructive authenticity in victoria falls tourist (restaurant) experien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31, no.2 (June 2012): 391-392.。后續研究表明,旅游體驗不僅僅涉及到旅游者對吃住行游購娛等要素的客觀本真體驗,經由旅游活動激發出來的旅游者內在的存在本真體驗已然成為旅游體驗的重要組成部分。(13)Ning Wang, “Rethinking authenticity in tourism experience,”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6, no.2 (April 1999): 361-365.以此為基礎,少數學者初步觸及客觀本真和存在本真之間的聯系,并基本達成共識:客體本真與主體本真確存聯系,單純存在本真性難以完全解釋文化旅游尤其是民族旅游的動機(14)李旭東《民族旅游的真實性探析》,《桂林旅游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8年第1期,第17頁。。有學者以志工旅游者為例,發現客觀本真性是重要的,或至少有助于追求自我內在本真和人際本真,客觀本真實際上促進了存在本真體驗的獲得。(15)Nick Kontogeorgopoulos, “Finding oneself while discovering others: An existential perspective on volunteer tourism in Thailand,”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65, no.4 (July 2017): 5-8.伴隨研究的深入,少數學者嘗試探索客體本真對存在本真的作用機理,以麗江納西家庭旅館為例,發現游客經由家庭旅館的客觀本真,進而體驗到“家”的感覺和本真自我,提出客觀本真是溝通客體和存在本真的某種“中介”(16)Yu Wang, “Customized authenticity begins at home,”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34, no.3 (July 2007): 800.。北美游客赴蘇格蘭的尋根旅游中,作為個人起源證實之地的目的地,在彌補傳統與命運之間的鴻溝中扮演了促發因素,目的地被尋根游客集體式地重新發現,并從中獲得一種“真實存在著的自我”感覺。(17)Derek Bryce, Samantha Murdy, Matthew Alexander, “Diaspora, authenticity and the imagined past,”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66, no.5 (September 2017): 51.
(三)騎行旅游體驗研究
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發達國家因公眾健康意識和環保意識的提升,大力宣傳推廣自行車綠色出行,騎行社會實踐得以持續推進,并逐步促生騎行成為一種專項旅游形式。(18)鄧冰、陳玲玲、張翾《國外自行車旅游研究綜述》,《旅游學刊》2015年第3期,第116頁。在國外,有關騎行旅游體驗研究主要從騎行設施、配套服務、空間設計、景觀營造和道路規劃等產品供給視角,通過改善旅行空間、道路安全、觀光質量、空氣質量、路況和通達性等為旅游者提供更滿意的旅游體驗(19)Ye Gordon, et al, “Bicycle tourism: On the trail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Prairie Perspectives: Geographical Essays 9, no.1 (October 2006): 71-77.。從微觀層面開展騎行旅游體驗研究仍處于初期階段,僅見少數學者轉向關注騎行旅游動機、出行模式選擇、重游意愿等(20)John C. Whitehead, Pamela Wicker, “Estimating willingness to pay for a cycling event using a willingness to travel approach,” Tourism Management 65, no.2 (April 2018): 165-166.。如里奇以新西蘭南島騎行旅游為例,將動機歸納為自主與成就、獨處、探索、身體挑戰、尋找類似或避免類似、社會交往和逃避社會七類(21)Brent W. Ritchie, “Bicycle tourism in the South Island of New Zealand: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ssues,” Tourism Management 19, no.6 (December 1998): 578.。國內學者傾向從旅游者行為視角探討騎行旅游體驗,關注城市騎行體驗休閑效益(22)余勇、田金霞《騎乘者休閑涉入、休閑效益與幸福感結構關系研究——以肇慶星湖自行車綠道為例》,《旅游學刊》2013年第2期,第67頁。和環境偏好(23)萬亞軍、蒙睿《昆明市自行車旅游愛好者行為特征及其環境偏好分析》,《旅游研究》2011年第4期,第14頁。等問題。值得一提的是,川藏線騎行旅游體驗研究受學界關注最多。苗鳳祥認為,騎行西藏旅游體驗呈現追求自我實現,尋求出走與自由欲望等特征(24)苗鳳祥《自由的出走——自行車愛好者騎行西藏行為研究》,《長春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期,第35頁。;胡傳東等運用內容分析法,進一步將騎游川藏線體驗分為景觀感知、自我體驗和自我超越三個層面以及自然、挑戰、暢爽、美麗、傳奇和升華六個維度(25)胡傳東、李露苗、羅尚焜《基于網絡游記內容分析的風景道騎行體驗研究——以318國道川藏線為例》,《旅游學刊》2015年第11期,第99頁。;張朝枝和張鑫則以流動性為視角,認為騎行入藏旅游體驗由行為情境、氛圍情境與情感情境構成,建構了“行為-氛圍-情感” 三維體驗模型(26)張朝枝、張鑫《流動性的旅游體驗模型建構——基于騎行入藏者的研究》,《地理研究》2017年第12期,第2332頁。。
綜上所述,一方面,現有本真性旅游體驗研究,更多的是將客觀本真和存在本真視作一個整體概念,側重思辨討論和概念對話,對某一具體情境下客觀本真性和存在本真性范疇的內在結構維度的探索尚未引起關注;并且,絕大多數研究將客觀本真性視為存在本真性的促發因素,客觀本真經由“再生產”或“舞臺化”使旅游者在某種程度上獲得存在本真性體驗,而存在本真對客觀本真有無影響、兩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如何等問題仍有待開展系統而深入的探討。另一方面,現有川藏線騎行旅游體驗研究素材主要來自網絡游記等二手資料,受資料的針對性和聚焦性不足等因素制約,研究成果的概念化、理論化程度亟待提升;并且,已有川藏線騎行旅游體驗研究聚焦認同、審美、流動性及朝圣等視角,尚未出現從本真性理論視角關注川藏線騎行體驗的專項研究。毋庸置疑,川藏線騎行涵蓋旅游吸引物、游客內部互動和主客互動等本真性體驗要素,集旅游體驗的豐富性、復雜性和過程性于一體,基于本真性理論視角對川藏線騎行這一特殊情境下的旅游體驗開展系統而深入的研究,有助于激發學界對本真性旅游體驗理論的新思考。基于此,本文通過參與觀察和深入訪談獲取原始一手資料,運用扎根理論深入挖掘文本,嘗試窺見本真性旅游體驗相關范疇及內部關系的規律,探索客觀本真體驗和存在本真體驗二者雙向互動影響機制,以期豐富本真性旅游體驗理論結構的完整性。
二 研究方法與數據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探討川藏線騎行旅游者的本真性體驗內容及規律,嘗試建構川藏線騎行旅游這一特殊情境下的客觀本真性和存在本真性之間結構性關系的理論認知,屬于探索性研究,適合采取質性研究方法。質性研究作為一套方法系統,要求研究者遵循規范的分析步驟,強調研究問題產生的背景,認為概念、范疇及理論的形成是自然顯現的過程,最終通過文獻回顧使研究理論達到飽和。扎根理論強調系統收集、整理和分析原始資料,從經驗資料中生成理論,其核心是對質性資料進行分析處理,而編碼正是對質性資料進行處理以及標簽化的動態過程,一般將編碼分成開放性編碼、主軸編碼和選擇性編碼。(27)Barney G. Glaser, Anselm L. Strauss,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Nursing Research 17, no.4 (June 1968): 364-365.本文通過深度訪談和參與式觀察收集文本資料,采取三角鑒定的方法對信息的真實性進行驗證。訪談資料的編碼和范疇化均使用三角檢驗法完成,即兩組研究團隊同時各自完成編碼和范疇化,針對編碼的結果進行商討達成共識后,最后交由一位從事旅游者行為研究的學者加以判別修正,以此確保本研究的理論飽和度。(28)凱西·卡麥茲《建構扎根理論:質性研究實踐指南》,邊國英譯,重慶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44-146頁。
(二)數據收集
本研究以川藏線騎行旅游者為研究對象,原始資料來自對川藏線騎行旅游者的深入訪談。資料收集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課題成員親自騎行川藏線,并實地調研訪談騎游川藏線旅游者;第二階段,在課題成員實地調研返回后,持續跟蹤訪談川藏線騎行旅游者。本文還采取通過熟人結識潛在訪談對象,并以滾雪球方式逐步擴大樣本量的目的性抽樣方式。課題組訪談川藏線騎行旅游者數量為 30人,總計形成訪談文本資料近14萬字。其中,面對面訪談20人,電話訪談10人,訪談時長20-120分鐘。訪談錄音征得受訪者同意,訪談結束后對錄音文件進行逐文逐句整理,轉錄形成文本資料。受訪者人口統計特征見表1。

表1 訪談對象基本信息
三 扎根編碼結果
(一)開放性編碼
開放性編碼是對原始資料逐字逐句進行分析、標簽、登錄及編碼,進而實現原始資料初始概念化、概念范疇化的過程。(29)陳向明《扎根理論的思路和方法》,《教育研究與實驗》1999年第4期, 第58-60頁。本文通過對30份訪談文本資料加以逐詞、逐行、逐段的屬性分析,進行初始概念化,進而實現范疇化。第一輪開放性編碼后,共識別出24個初始概念及11個對應范疇。開放性編碼示例見表2。

表2 開放性編碼分析
(二)主軸編碼
主軸編碼是基于初步范疇化的眾多子范疇的內在含義,反復進行邏輯關聯的比較、分類和歸納,逐步提煉并自然浮現出能夠統屬開放式編碼的主范疇。通過進一步分析和總結,研究者共識別出兩個主范疇:川藏線騎行旅游者的客觀本真性體驗和存在本真性體驗(見表3)。

表3 主軸編碼分析
1.客觀本真性體驗
川藏線騎行旅游者的客觀本真性體驗指向旅游客體相關的本真性體驗內容,包括川藏線自然景觀本真和人文景觀本真。川藏線騎行旅游者普遍認為,眼前的客體自然景觀迥異于大眾旅游景區的游人如織與高度商業化,其未經人工雕琢修飾的原真自然景觀與艱險的自然環境構成了川藏線騎行旅游者自然景觀本真體驗。正如現有研究結論,川藏線騎行旅游者的人文景觀本真感知不僅僅局限于對民族文化遺跡和遺產等具有明顯物質載體的客體本真體驗(30)Muchazondida Mkono, “A netnographic examination of constructive authenticity in Victoria Falls tourist (restaurant) experien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31, no.2 (June 2012): 391-392.,沿線的虔誠信仰景觀、獨特民俗風情與民族特色人文風貌亦是構成旅游者人文景觀本真體驗的重要組成部分,兩者共同構成了客觀本真的整體圖景。這與麥坎內爾提出的“他人的生活為旅游者提供了一種真實”(31)Dean Maccannell, “Staged authenticity: Arrangement of social space in tourist setting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9, no.3 (November 1973): 595-599.相吻合,同時也深化拓展了該觀點。概言之,川藏線未經破壞的原真自然景觀及神秘淳樸的人文景觀與旅游者慣常的生活環境形成強烈的反差,這正是他們眼中殊為難得的客觀本真體驗。
2.存在本真性體驗
川藏線騎行旅游者的存在本真性體驗指向旅游者主體內部本真與主體間本真,由騎行旅游者自我內部本真體驗和人際本真體驗構成。自我內部本真體驗表現為川藏線騎行旅游者從瑣碎日常生活中解脫出來,通過川藏線騎行這種具身性實踐獲得自我實現和自我超越層面的自我認同。人際本真體驗又可分為騎行旅游者群體內部人際本真體驗及騎行者與東道主之間人際互動本真體驗。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川藏線騎行旅游者之間生發出強烈的群體認同感,群體內部表現出極強的目標一致性,彼此之間雖素昧平生,但群體內部團結友好、互幫互助,進而獲得基于共同經歷和價值認同的群體內部本真體驗。川藏線旅游者與東道主之間主客交往的頻率和強度遠超傳統大眾旅游淺嘗輒止的主客關系,旅游者通過與東道主之間頻繁地溝通交流等互動,獲得不同于一般“商業化好客”的人際本真體驗。
(三)選擇性編碼和理論構建

圖1 川藏線騎行旅游者本真性體驗規律
1.客觀本真與存在本真共同構成川藏線騎行旅游動機
川藏線騎行旅游者不但關注川藏線沿途客觀本真,更看重通過客觀本真體會騎行旅游方式帶來的自我放松、自我實現和自我超越等存在本真體驗,客觀本真與存在本真共同構成川藏線騎行旅游動機。一方面,川藏線主要路段地處西南藏區,由于交通條件限制以及地理位置偏僻,作為旅游客體的川藏線,最大程度地保留著自然和人文景觀的原真,與旅游者慣常生活環境存在明顯的空間和文化落差,也與大眾旅游景區的商業化形成鮮明對比,而這些恰好成為旅游者眼中獨具魅力的客觀本真。另一方面,川藏線海拔、地形地貌及路程等客觀因素,使得騎游進藏難度系數高,騎行速度慢,但摒棄現代交通工具,轉向依賴自身的能力,通過騎行川藏線這一獨特的具身性實踐完成旅游行程,讓旅游者獲得了大眾旅游者可望而不可及的自我實現和自我超越等存在本真體驗:“一點點的,用車輪去丈量整個路程,慢慢走、細細看,比起大眾旅游‘麥當勞’式的走馬觀花,更能體會這一路的艱辛,是一種很難得的經歷,比單純搭車或者自駕更有意義。”(CZX-18)
2.客觀本真是存在本真性體驗的重要來源
客觀本真是存在本真體驗的重要來源,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川藏線原始淳真的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深深地觸動了騎行旅游者內心的種種感悟,沿途一望無際的草原、浩瀚明朗的星空、藏民虔誠的信仰和悠閑的生活方式,讓川藏線騎行旅游者充分感受到大城市可望而不可及的原真,觸景生情,心靈受到震撼和洗禮,激發了自我反思,進而找尋到在繁忙瑣碎的現代生活中遺失的本真自我。“在海拔5000m的浩瀚星空下,覺得自己非常渺小,以前覺得很在意的事情、煩心的事情,覺得非常不值得。每個人要走的路和浩瀚宇宙相比實在太渺小了,星空陶冶了我,讓我更大氣、更開闊。”(CZX-09)二是多變的天氣、復雜的地形地貌及高反缺氧等川藏線艱難險阻本真無時不刻地考驗著騎行旅游者的身心承受能力,正是這種艱巨的挑戰激發了騎行旅游者的昂揚斗志,錘煉著他們矢志不移的意志品質,使之實現了自我超越。“騎行川藏線就是一場磨練,一次修行,更是人生的一筆寶貴財富。路上經歷了很多困難、辛苦和痛苦才獲得成功,那么艱苦的環境都能堅持下來,以后面對人生中其他困難時,想下當時那么難我都過來了,今天這個困難我會過不去?”(CZX-11)更有意思的是,正是川藏線的艱難險阻本真讓騎行旅游者之間更易形成團結和睦、友善互助的人際關系氛圍。騎行旅游者面臨共同目標,也經常面臨修車、摔車、掉隊和高反等諸多共同問題的困擾,加之相關保障設施的滯后,使得素不相識的騎友間互幫互助更為純粹和珍貴,騎友間互訴衷腸、互相勉勵成為川藏線上另一道靚麗的“風景”,“大家有共同目標,共同努力、互相幫助,相互像戰友之間的共患難那種感覺,為一個共同的方向,互相鼓勵,互相幫助。”(CZX-07)
3.存在本真性體驗強化了對客觀本真的認同
旅游經歷的真實與否,重要的是“整體的游客體驗”以及這種旅游體驗之于個體旅游者的意義(32)鄧小艷《基于建構主義原真性理論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旅游開發的解讀》,《貴州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第91頁。。這里的“整體的游客體驗”,既包括客觀本真“景”的體驗,也含有發自旅游者內心之“情”的存在本真體驗。觸景生情,折射出“客觀本真是川藏線騎行旅游者獲得存在本真體驗的重要來源”。筆者認為,“情景交融”同樣蘊含著對“情”“景”的認知的升華作用。換句話說,存在本真性體驗也反向強化川藏線騎行旅游者對客觀本真的認同,加深旅游者對客體本真的認同。旅游者通過騎行方式穿越艱難險阻的川藏線,經由旅游客體的本真找尋到遺落在單調瑣碎的重復式日常生活之外的本真自我和人際關系,獲得了大眾旅游方式無法體會的“暢爽”體驗。基于“暢爽”的存在本真性體驗,旅游者轉身含情“凝視”沿途“客觀存在的山”,發現它們不再是單純冰冷的旅游客體,而是被賦予了旅游者的心靈感悟和價值認同的旅游客體,使得本真客體與旅游者個體間建立起了某種意義上的聯結。這個意義聯結強化了旅游者對眼前客觀本真的理解與認同,這可以從很多旅游者心目中川藏線被“神圣化”得以印證,恰如學者描述的“世俗的朝圣”(33)崔慶明、徐紅罡、楊楊《世俗的朝圣:西藏旅游體驗研究》,《旅游學刊》2014年第2期,第110頁。,因心中的“神圣”進而體悟到川藏線沿途自然和人文景觀的“神圣”。難怪有游客如此描述:“大部分人都是愿意去幫助別人、愿意與人為善,但要在一個合適的環境當中。失去了川藏線那樣一個特殊的環境,回到了原本的生活當中,回到了現實生活當中去,又重新戴上了面具。”(CZX-16)在游客眼中,人際本真體驗的獲得源于川藏線的特定環境,這反過來也加深了旅游者對川藏線客觀本真的認同。
4.本真性判斷呈現主位化特征
旅游研究中本真性的含義肇始于博物館情境,最初用于判斷某種旅游產品如手工藝品、節慶、服裝等的本真與否,此處“本真性意味著傳統的文化及其起源,意味著一種純真(genuine)、真實(real)與獨特(unique)”(34)馬凌《本真性理論在旅游研究中的應用》,《旅游學刊》2007年第10期,第77頁。。麥坎內爾等客觀本真性論者認為,客體本真與否的判斷標準在專家學者及權威手中(35)Dean Maccannell, “Staged authenticity: Arrangement of social space in tourist setting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9, no.3 (November 1973): 595-599.。科恩等建構本真性論者則認為,本真性的判斷標準處于變動之中,一件產品、節事或者手工藝產品最初不被認可,但隨時間演進,有可能被接受為“本真”,本真性的判斷標準是“漸變”的。(36)Erik Cohen, “Traditions in the qualitative sociology of 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5, no.1 (January 1988): 36-37.王寧等則將存在本真性的判斷標準交由旅游者判定,即使在人工打造的迪斯尼游樂園,旅游者也可獲得經由旅游活動激發的本真自我。(37)Ning Wang, “Rethinking authenticity in tourism experience,”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6, no.2 (April 1999): 361-365.不難發現,學界傾向于將存在本真性的判定交給旅游者,而客觀本真性的判定仍保留在專家學者手中。但在川藏線騎行旅游情境中,我們發現,無論是對客觀本真性還是對存在本真性的判斷,旅游者都不再是不明就里的接受者,而表現出強烈的內生自主意識和主動性,彰顯出本真性判斷的主位化特征。換言之,旅游者成為牢牢掌握標準的“仲裁員”,其主觀評判成為判別自身動機和體驗本真與否的決定因素。正如一位游客的評價:“川藏線與國內其他旅游景區的區別在于,這里的是未經人工雕琢修飾,特別原始淳樸,是原生態的,而騎行旅游川藏線比之大眾旅游方式更能讓我感受到挑戰自我的暢爽。”(CZX-29)存在本真性判定主位化無需論述,而川藏線旅游客體本真性的判定亦呈現主位化特征,則有必要做簡單闡釋。現有資料顯示,尚未有官方渠道正式宣稱川藏線這一客體本真與否,但在大眾看來,川藏線作為旅游客體的本真性卻毋庸置疑,川藏線旅游客體本真性的判定來自游客游前對游記和影視作品中原始野性、未經雕琢的總體印象,而游中存在本真體驗的獲得則印證并強化了游前客觀本真的認知,游后通過游記和交流等主動推薦方式進一步傳播其對川藏線客觀本真形象升華后的理解和認同。
五 結論和討論
(一)結論
第一,研究發現,川藏線未經人工雕琢修飾的原真自然與渾厚淳樸的人文風貌恰好是旅游者心目中的獨特價值所在,旅游者通過騎行方式這種具身性實踐,獲得對客體本真自然和人文景觀的別樣的領悟和認同,由此彰顯旅游者自我挑戰、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的價值與意義。由此看出,川藏線騎行旅游者的本真性旅游體驗并未囿于麥坎內爾等客觀本真論者的“旅游者本真體驗是對旅游客體本真的觀光游憩體驗”(38)Dean Maccannell, “Staged authenticity: Arrangement of social space in tourist setting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9, no.3 (November 1973): 595-599.之觀點,亦非持存在本真性觀點學者的“旅游者并不在乎客體本真與否,只借助旅游活動與旅游客體尋找本真自我”(39)Ning Wang, “Rethinking authenticity in tourism experience,”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6, no.2 (April 1999): 349-370.之觀點,而是由客觀本真性體驗與存在本真性體驗二者共同構成。
第二,川藏線騎行旅游客體本真體驗方面,通過扎根理論挖掘發現,不限于對沿途文化遺產和文化遺跡等“原作品”本真的欣賞,還自然浮現出了“自然環境的艱險體驗”“虔誠信仰景觀”等新范疇。這由此拓展了客觀本真體驗范疇。這給我們的啟發是,特殊情景下的小眾專項旅游產品,不僅僅意指對旅游吸引物的審美愉悅,也內含著艱險的旅游經歷本身和旅游過程獲得感。川藏線騎行旅游存在本真性體驗方面,總體結論與王寧等學者提出的“包含自我內部本真和人際本真兩個結構維度”的觀點一致,但我們進一步提煉出了“騎程中身體知覺的挑戰”“騎程中意志品質的磨練”“騎游旅途中的自我成長”三個內部本真體驗范疇,同時還挖掘出“與東道主之間人際互動本真體驗”這一人際本真體驗的新范疇。由此觀之,川藏線騎行旅游者摒棄現代化交通工具,從實現旅游方式的艱險歷程視角看,類似于謝彥君先生筆下的“苦行型”;其旅游動機遠遠超越了游樂場情景下沉浸式體驗帶來的“自我放松”,更蘊含著磨練、自我挑戰和自我實現,從找尋精神意義層面上,他們體現出深思熟慮的謹慎嚴肅、很強的目的性和虔誠性,可視為謝彥君先生筆下的“朝圣者”,只不過他們朝圣的不是宗教,而是自己內心信仰中的“那座山”而已。(40)謝彥君等《西藏宗教朝圣旅游場中的邊緣人現象及其邊緣性體驗》,《旅游學刊》2020年第6期,第51-57頁。
第三,研究發現,川藏線騎行旅游者一般不會停留在欣賞川藏線沿線瑰麗雄奇的自然和人文景觀本真,亦不止于客觀本真的艱險漫長帶來的自我反思,川藏線客觀本真的諸方面內在地促使他們選擇以騎行這種具身性實踐的方式,以找尋遠方存在的“心中的那座山”,旅游結束也許正是其人生旅途上自我完善和自我實現的另一個新開始,同時也賦予他們轉身“凝視” “客觀存在眼前的這座山”的新認知。也就是說,川藏線騎行旅游的客觀本真性不再僅僅是以往研究中對存在本真性的單向度促發因素(41)Nick Kontogeorgopoulos, “Finding oneself while discovering others: An existential perspective on volunteer tourism in Thailand,”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65, no.4 (July 2017): 5-8.,還呈現出“存在本真體驗強化了對客觀本真的認同,本真性判斷標準呈現主位化”等特征。這進一步拓展了李旭東、王瑜、陳享爾等以民族文化(42)李旭東《民族旅游的真實性探析》,《桂林旅游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8年第1期,第17頁。、歷史遺跡(43)Yu Wang, “Customized authenticity begins at home,”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34, no.3 (July 2007): 800.和文化遺產(44)陳享爾、蔡建明《旅游客體真實性與主體真實性集合式關系探討——以文化遺產故宮為例》,《人文地理》2012年第4期,第153頁。為背景參照所提出的“客觀本真和存在本真性可能存在某種關系或轉換機制”的研究結論,也豐富了客觀本真和存在本真體驗之間關系研究的深度和廣度。
(二)討論
川藏線騎行旅游者表現出對現代大眾旅游的摒棄和本真性體驗的強烈追尋,背后到底是何種因素起了關鍵性作用?旅游社會學家試圖從現代社會轉型背景回答該問題。麥坎內爾認為,是現代性的疏離,促使旅游者去尋找他處的本真(45)Dean Maccannell, “Staged authenticity: Arrangement of social space in tourist setting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9, no.3 (November 1973): 595-599.;科恩認為,旅游是對現代社會消失本真的一種重現(46)Erik Cohen, “Tourism as play,” Religion 15, no.3 (July 1985): 292.;王寧把旅游視作現代性背景下“好惡交織”的產物和表現(47)王寧《旅游、現代性與“好惡交織”——旅游社會學的理論探索》,《社會學研究》1999年第6期,第100頁。。后續學者大多沿襲這些觀點,將旅游視為現代性危機下人們追求理想家園和自我本真存在的重要形式(48)董培海、李偉《旅游、現代性與懷舊——旅游社會學的理論探索》,《旅游學刊》2013年第4期,第112頁。。然而,倘若只是現代性危機推動了旅游者的本真性體驗追求,那么作為旅游主體旅游者的自主意識何在?旅游者難道只是現代性危機的被動承受方?現有旅游本真性理論尚未對此作出回應。超越旅游學科視角局限的研究,則可能獲得對現有問題更為前瞻、更為深刻的認識。泰勒從微觀個體角度追尋本真性之源,他認為,現代性雖帶來個人主義濫觴、工具主義與理性主義盛行等困境,但同時也實現了以個人自主性為標志的自我理解的現代轉變,現代性賦予個體“自決的自由”,這意味著每個人都能且只能從真實自我出發,尋求并實現本真性理想。(49)查爾斯·泰勒《本真性的倫理》,程煉譯,上海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35-38頁。這給予我們極大的思辨啟發。川藏線騎行者對本真體驗的追尋,既與宏觀社會轉型下的現代性推動有關,更與微觀個體角度的“忠實于自我”的個人自主性追求緊密相關。兩種因素相比,現代性之于川藏線騎行旅游者的本真性體驗追求,更多地表現為外部環境的推力作用,這種力量似乎更多地決定著旅游者是否出游;而摒棄現代化交通工具,選擇騎行方式,克服艱險穿越川藏線這種具身性實踐,則更多地表征著旅游者的內心渴望尋求他處的客觀真實與本真自我,是一種更深層次的以個人自主性為基礎、“忠實于自我”的發自內心的拉力,這股力量似乎更加強烈,它內生地決定了旅游者選擇特殊的旅游目的地和旅游方式。有意思的是,大眾旅游情景下的旅游障礙因素(克服重重艱難)在此變成了誘發川藏線騎行旅游者的動力源。與謝佳、朱璇視作生活政治實踐的追求反思自我和人生選擇的背包客、窮游者相比(50)解佳、朱璇《“窮游”興起的社會學分析——兼論窮游者與背包客的異同》,《旅游學刊》2019年第1期,第124頁。,以個人自主性為起點的強烈追求自我實現的身體實踐性的川藏線騎行旅游者更具韻味。正如訪談者所言:“出發前川藏線是我心中的一座山,如果我能完成,以后生活中還有什么困難不能夠克服?旅行結束后,我們每個人都有所改變,有人備考雅思,有人準備出國或考研,還有準備跑一次馬拉松等。”(CZX-23)在此,受苦多難的騎游川藏線,似乎已成為旅游者的人生“閾限”(51)趙紅梅《論儀式理論在旅游研究中的應用——兼評納爾什·格雷本教授的“旅游儀式論”》,《旅游學刊》2007年第9期, 第71-72頁。,旅游者于此反思過往、寄望未來,騎游川藏線成為溝通往昔和未來、架接此岸與彼岸的橋梁。
本文以川藏線騎行旅游者作為研究對象,采用質性研究方法,探索性地發現了關于客觀本真和存在本真之間結構性關系的結論,并由此展開具有一定思辨性的討論。但是,這些結論和討論均是建立在川藏線騎行旅游這一特殊情景下,對于類似的小眾專項旅游產品,值得后續研究進一步探索、跟進。再者,現有結論是基于30個騎行旅游者的訪談文本深度分析的自然浮現,尚需獲取實證數據開展進一步的科學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