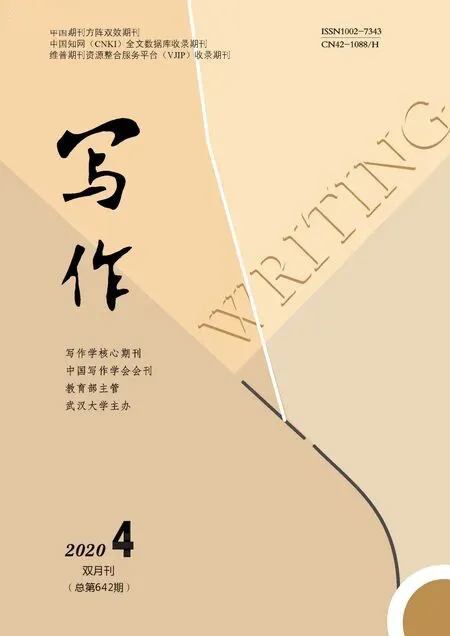從過渡禮儀看汪曾祺《受戒》中的雙重世界
汪云霞 耿 葉
汪曾祺被視為京派文學的最后一位傳承者,他的作品注重民風民俗的描畫,并由風俗而及人,在呈現“世外桃源”般的鄉土風情的同時,深入生活,直面人性①汪曾祺:《談談風俗畫》,《汪曾祺文集》文論卷,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59-66頁。。《受戒》是汪曾祺經歷“文革”復出后的作品,小說詩意的文化色彩始終吸引著學者們的研究興趣,已有學者從小說的詩性文化②王本朝:《瀆神的詩性:〈受戒〉作為1980年代的文化寓言》,《當代文壇》2012年第2期。、文學意蘊③張紅翠:《重審〈受戒〉的多重內涵》,《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6年第12期。以及敘事特色④王曉薇:《平遠小景簡雅拙淡——試論汪曾祺的小說〈受戒〉》,《當代作家評論》2003年第5期。等角度對其進行解讀,成果較為豐富。不過,與1980年代主流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不同,小說圍繞著題名“受戒”儀式展開,描繪了諸多宗教禮儀與民風民俗。而各種禮儀的刻畫,為小說增添了豐富的文化氣息,與文化人類學的“過渡禮儀”觀念頗為契合。
過渡禮儀也稱“通過儀式”,是重要的人類學概念。阿諾爾德·范熱內普在《過渡禮儀》一書中提出:“在任何社會中,個體生活都是從一年齡到另一年齡、從一種職業到另一種職業之過渡。凡對年齡或職業群體有明確分隔的社會,群體間過渡都伴有特別行為。”⑤[法]阿諾爾德·范熱內普:《過渡禮儀》,張舉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5頁。特納在《象征之林》一書中進一步解釋了范熱內普的觀點,過渡禮儀即“伴隨著地點、狀態、社會位置和年齡的每一次變化而舉行的儀式”⑥[英]維克多·特納:《象征之林》,趙玉燕、歐陽敏、徐洪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124頁。。小說《受戒》,如題名所示,主人公的“受戒儀式”即為最重要的過渡禮儀。明海經歷了從世俗世界到神圣世界的閾限過渡,也在受戒儀式中通過了自己的成長考驗,獲得了直面自我的勇氣與權利。閾限過渡處于模糊不定的時空,小說《受戒》在三個層面體現著雙重世界的模糊性。首先,受戒作為一種宗教禮儀,體現著主人公在世俗世界與神圣世界之間的過渡。其次,主人公在閾限期學習著宗教和社會禮儀,在社會化的過程中走向文明,在自然世界與文明世界之間過渡。再次,主人公在經歷了成長考驗,完成了受戒儀式后,愛情也從現實世界走向理想世界。
一、神圣與世俗的雙重變奏
人類學家將個體的成長過渡劃分為三個階段:分離、閾限和融合。阿諾爾德·范熱內普在《過渡禮儀》一書中提出:“世俗世界與神圣世界之間不存在兼容,以致一個個體從一個世界過渡到另一世界時,非經過一中間階段不可。”①[法]阿諾爾德·范熱內普:《過渡禮儀》,張舉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4、26頁。這一中間階段即為閾限時期。它是最重要的階段,由特定的成長儀式組成,實現對閾限主體的考驗。受戒作為一種宗教儀式,象征著主人公由世俗世界向神圣世界轉變。通過成長閾限的考驗,主人公會在身份和社會地位上發生轉變,進而獲得從前不曾擁有的權利。
首先,“分離儀式”是閾限過渡的前提,個體遠離常規的生活環境,通過既定的儀式完成與親緣主體的分離,為自我的獨立成長創造空間。在小說《受戒》中,主人公明海的家鄉代表著世俗世界,而荸薺庵則代表著宗教的神圣世界。在動身前往荸薺庵之前,明海經歷了一場特殊的分離儀式。“明子穿了這件和尚短衫,下身還是在家穿的紫花褲子,赤腳穿了一雙新布鞋,跟他爹、他娘磕了一個頭,就跟舅舅走了。”②汪曾祺:《受戒》,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3頁。和尚短衫是這一儀式中具有象征性意義的符號。明海上身換上了和尚短衫,下身穿的還是在家穿的衣服,通過非僧非俗的狀態,將主人公置于閾限過渡的中間狀態。此時的明海已經與宗教建立起初步的聯系,不再隸屬世俗世界;而他尚未受戒,也不屬于真正的和尚,處于世俗世界與神圣世界之間。這一中間狀態也標志著明海成長考驗的開始。服飾在器物層面上見證了主人公的轉變,為閾限主體的精神轉變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
在經歷與父母親緣的閾限分離后,小說中又出現了一個重要的意象——“渡船”。按照范熱內普的觀念,“過河”被視為一項重要的過渡儀式③[法]阿諾爾德·范熱內普:《過渡禮儀》,張舉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4、26頁。,啟程的“渡船”就具有分離儀式的象征含義。從換裝、扣頭再到渡船離開,明海逐漸遠離原本的生活空間,物理空間的拉長也暗示著主人公心理距離的延展。在渡河的過程中,他與以家鄉為代表的世俗世界漸遠,與寺廟為代表的神圣世界漸近。“渡河”結束昭示著分離儀式的完成,明海來到了閾限過渡的荸薺庵,也正式走入世俗世界與神圣世界之間。
其次,閾限是“過渡禮儀”最重要的階段。閾限過渡的界域由一種模糊不定的時空構成,象征著平等、不確定性和無限可能性。小說中的荸薺庵雖然屬于宗教場所,但這里的和尚不大受清規戒律的束縛,主人公的活動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性。在這個僧俗融合的空間里,世俗世界與神圣世界沒有涇渭分明地對立,兩者之間的界限被模糊化處理。
明海在荸薺庵學習了基本的宗教禮儀,初步具備合格的宗教身份,為最終的受戒儀式做準備。明海來到荸薺庵學習的第一個儀式是“唱經”。唱經儀式有著一整套完善的動作和唱詞,參與者只需按照范式嚴格執行。它雖程式化,卻被視為俗家子弟加入和尚群體的例行儀式。這種廣泛存在于和尚日常生活中的唱經儀式,在這里卻有著特殊的象征意義。教給明海唱經的是他舅舅,也是帶他進入荸薺庵的“當家的”。明海在師父的引導下習得了唱經,也標志著他成功跨過“和尚行業”的第一道門檻,成為荸薺庵和尚群體的一員。這種身份的轉變,使明海在接下來的活動中具有了合法的主體資格。緊接著,小說介紹了放焰口儀式。放焰口是一種常見的法事,也是僧俗之間發生直接聯系的儀式。“荸薺庵只有四個和尚……通常只是放半臺焰口。一個正座,一個敲鼓,另外一邊一個。”①汪曾祺:《受戒》,南京:譯林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7、20、20、22 頁。小說以放焰口儀式為跳板,引出荸薺庵三個和尚的情況,一個有老婆,一個“拐媳婦”,充分展現了他們“世俗性”的一面。荸薺庵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佛教世界,和尚們抽煙打牌、殺豬吃肉、耍“飛鐃”、唱小調,無奇不有,毫無清規戒律。這個充滿無限自由的空間,為明海的活動提供了更大的可行性界域。
亦僧亦俗的地域,契合閾限過渡的中間狀態,是主人公接受成長考驗的最佳場所。在這里,明海一邊學習宗教禮儀,一邊體驗世俗生活的美好。他在世俗世界與神圣世界之間度過了四年的閾限時期,不斷修習基本的宗教禮儀,也在不斷地成長。荸薺庵的經歷賦予主人公合格的主體身份,也具備了融入宗教世界的權利。
再次,融合是“閾限過渡”的最后一個階段,主人公通過了“過渡禮儀”的考驗,獲得融入新世界的權利。受戒是閾限過渡的高潮點,也是明海與神圣世界融合的標志。受戒完成標志著主人公通過了從世俗世界到神圣世界的考驗,“領到了一張和尚的合格文憑”②汪曾祺:《受戒》,南京:譯林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7、20、20、22 頁。。和尚想取得合格的主體身份,需要到善因寺受戒,否則就只是“野和尚”。與荸薺庵相比,莊嚴氣派的善因寺代表著權威,也更接近傳統意義上的佛教寺廟,那是理想的神圣世界。“廟門的門檻比小英子的肐膝都高。”③汪曾祺:《受戒》,南京:譯林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7、20、20、22 頁。小說沒有正面描寫明海跨過門檻的情形,而是以小英子的見聞感受來展現善因寺的神圣氣象。跨過善因寺的門檻,是受戒儀式的起點。在人類學理論中,門檻作為一種象征性符號,跨過去就意味著進入了一個新的界域④[法]阿諾爾德·范熱內普:《過渡禮儀》,張舉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24頁。。明海跨過這高大的門檻,開始成長考驗的最后一場儀式,也正式開啟融入新世界的歷程。小英子陪伴著明海閾限過渡的每一場儀式,自然不會缺席最重要的受戒儀式。她以旁觀者的眼光看待這場受戒禮儀。“燒戒疤是不許人看的”⑤汪曾祺:《受戒》,南京:譯林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7、20、20、22 頁。,小說遵循了這一隱蔽性的風俗,沒有正面描寫明海受戒的場面,而是從小英子的視角,以她從明海那里聽得的傳聞,介紹了受戒儀式,牽引出“剃頭—燒戒疤—散戒”的整個過程。汪曾祺作為一位注重宗教民俗寫作的作家,整個受戒儀式沒有直接展露在讀者眼前,保持了受戒儀式的神秘感和莊重性,也體現出作家對宗教習俗的尊重。
受戒儀式的完成,標志著主人公的閾限考驗正式結束,也標志著主人公在身份上完成了從世俗世界到神圣世界的轉變。不過小說并沒有過多地直接描述善因寺這個神圣世界,這意味著主人公即便是脫俗入教、進入了新世界,依然面臨著某種不確定。而這種不確定同時意味著一種自由,意味著一切可能性。這種寫作策略除了體現汪曾祺對于宗教和習俗的尊重,也使文本自身具有一定的開放性,讓人對主人公的未來充滿想象。
二、文明與自然的交相輝映
受戒之路也是一場別樣的成長之旅,明海在荸薺庵的經歷構成他不斷社會化的過程。受戒之時明海17歲,剛好是身體和心理成熟的年紀。人類學鼻祖愛德華·泰勒在《原始文化》一書中給文化的定義為:“文化,或文明,就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說,是包括全部的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習慣的復合體。”⑥[英]愛德華·泰勒:《原始文化》,連樹聲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頁。“掌握和接受”體現出文化是習得的特性。無論是荸薺庵的學習,還是庵趙莊的往來經歷,都使明海不斷成長。受戒完成時主人公也就長大成人,獲得了獨立的人格,自我意識也開始覺醒。在家鄉時,明海處于自然世界,本性純真不受拘束。受戒使他進入了文明世界,成長為具有獨立意識的成年人。庵趙莊的學習生活經歷就成為明海由自然世界走入文明世界的閾限過渡,這一時期明海在寺廟修習宗教禮儀,也在與小英子一家的交往中習得社會禮儀,為他步入文明世界奠定了基礎。
首先,修習宗教禮儀實現成長是一個不斷走向文明的社會化過程。在一定意義上,宗教是文化的載體。明海的家鄉遠離荸薺庵,象征著蠻荒的自然世界。明海從小學習讀書寫字,但那只是發蒙,是為當和尚做準備的。只有到了荸薺庵,系統地學習宗教禮儀,他才算真正接受了文明的洗禮。學習帶來了成長,推動主人公自我意識的覺醒,接受教育的過程也是不斷向文明靠攏的過程。按照人類學的觀點,人們在閾限過渡時期,主人公即將加入的群體會派出熟悉其規則和事物的人員對新成員進行引導,這一角色被稱為“精神訓導者”①[英]維克多·特納:《象征之林》,趙玉燕、歐陽敏、徐洪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131頁。。精神訓導者帶領新成員了解群體規范,也為閾限主人公提供了一定的通過保障。從小說的敘事來看,舅舅“仁山”在明海的閾限考驗中充當著“訓導者”和“精神導師”的角色。明海7歲那年,“當和尚”的舅舅就和他父母共同商定了明海未來的職業——當和尚,也在六年后如期歸來帶走了明海。舅舅幫助明海進入“和尚行業”,教會明海念經,引導他學習基本的佛教禮儀,使他在宗教世界的活動具有了合格的主體身份。經過四年的宗教修習,伴隨著身心的茁壯成長,明海也就從鄉野少年成長為有文化的成年人,受戒完成標志著明海由自然世界走入文明世界,通過教化實現了成長。
其次,婚俗學習使主人公在參與的過程逐漸向社會文明靠攏。“庵”是佛教場所,“趙”是俗家姓氏,“庵趙莊”因庵得名。這一命名意味著庵趙莊靠近文明世界的中心,處于神圣世界的邊緣,是自然與文明交匯的地方。這使明海在閾限過渡時期得以體驗亦僧亦俗兩種生活狀態。當然,庵趙莊畢竟是村而不是庵,這為明海的成長和社會化提供了世俗生活空間,為他學習社會禮儀提供了契機。婚俗是社會禮儀的重要組成部分,明海在參與婚嫁籌備的過程中學習社會禮儀,也通過自身的成長推動婚俗文明的進程。小說用較多的筆墨描繪大英子籌備嫁妝、繡花的場景。“大裁大剪”“挑花繡花”,是趕制嫁妝的重要步驟。有了好的畫樣才能繡出好的花樣,大英子母女繡法高超,礙于樣式老舊,無法做出精致的繡鞋。明海會畫畫,他經常翻看《芥子園》,照著描。在小英子的保舉下,明海參與到大英子籌備嫁妝的儀式中。“石榴花、梔子花、鳳仙花……”小英子把花掐來,明海就能畫得惟妙惟肖。好的畫樣也催生出新的繡法——“亂孱”。大英子的繡鞋傳遍四方,方圓三十里的姑娘慕名而來,央求明海畫樣。在婚俗的儀式化展演中,明海進行著由學習到成長的社會化過程,同時,明海又是作為一個有文化的人出現在庵趙莊的,他的參與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當地婚俗文明的進步。
繪畫作為一種文化藝術,是文明的表現形式。明海在庵趙莊參與婚嫁儀式,獲得學習婚俗的契機,學習推動他的創作意識覺醒,使他從自然世界走向文明世界。參與婚嫁籌備前,明海的繪畫屬于自然世界的無意識描摹,庵趙莊的經歷使他具備獨立自主的創作意識。明海在實踐中學習繪畫技巧,提高創作水平。他的繪畫催生出新的繡法,促進了婚俗文化的發展。他在庵趙莊學習文化藝術,與當地人民合力構建社會文明。在婚俗的學習過程中,明海與小英子一起見證婚姻,兩人的愛情也由自然世界的純真懵懂走向文明世界的責任與擔當。
再次,由愛情到婚姻也是一個從自然到文明、不斷成長的社會化過程。明海與小英子一起學習婚俗,在自由自在的田間勞作。“薅草”“打汪”“唱山歌”,宛如天作之合。一開始,兩人處于無意識的自然狀態,一起玩耍只是孩童的友伴心理,兩小無猜,屬于人的本能。在參與婚俗籌備的過程中,兩人的心智也在不斷成熟。在他們親密無間的配合中出現了汪曾祺后期經常使用的 “性暗示”意象——腳。“她老是故意用自己的光腳去踩明子的腳。”“明海看著她的腳印,傻了……這一串美麗的腳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亂了。”①汪曾祺:《受戒》,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9、26、2頁。“腳”作為身體的一部分是自然狀態的表現,而小英子“故意用自己的光腳去踩明子的腳”,這里的“故意”就象征著意識的主動性。小英子那美麗的腳印擾亂了小和尚的心,也體現出青春少年性愛意識的朦朧覺醒。接受了社會禮儀的洗禮,兩人的身體和心理都得到了成長。隱晦的性暗示推動了明海和小英子懵懂愛情的進程。
明海始終是“做和尚”,而不是“出家”。他在自然世界與文明世界之間游走,不斷學習宗教和社會禮儀,由學習實現成長。受戒之后,明海的閾限過渡也完全結束。他順利通過成長的考驗,從世俗世界步入神圣世界,也從自然世界步入文明世界。“過渡禮儀”被人類學家認為是一種地位變化的社會機制②[法]阿諾爾德·范熱內普:《過渡禮儀》,張舉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xii頁。。受戒之后,明海具有了全新的身份和社會地位,也擁有了直面自我、選擇人生的權利。在這時,小英子適時地拋出兩人心中發酵許久的問題:
“我給你當老婆,你要不要?”
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
“你說話呀!”
明子說:“嗯。”
“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
明子大聲地說:“要!”③汪曾祺:《受戒》,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9、26、2頁。
受戒之路成為別樣的定情之旅,明海在受戒后做出愿意娶小英子的決定,既體現出主人公自我意識的覺醒,也暗示兩人的愛情由本能的自然狀態走向文明的自主選擇。如果愛情是人性的展現,那么肯定愛情也就是肯定人性。無論是宗教還是文化,都是成全人性,而不是否定人性。小說的標題叫《受戒》,汪曾祺卻始終沒有將宗教追求放在首位。明海雖然是為了受戒而來,要做和尚,但他卻在受戒后選擇了成全愛情。小說的這種矛盾性恰恰體現出汪曾祺的價值訴求。無論是明海,還是荸薺庵的和尚,他們的人性追求都遠高于宗教追求。即便是善因寺的方丈,據說都是有小老婆的。小說在開頭就明確表示了和尚是一種謀生手段,“做和尚”不是“出家”“可以吃現成飯,可以攢錢”④汪曾祺:《受戒》,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9、26、2頁。,與“劁豬的”“織席子的”無異。小說雖沒有明顯的反宗教情緒,卻在人性追求的謳歌中消解了宗教的神圣性。在神性與人性之間,汪曾祺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后者,將宗教的神圣性還原到人性的基礎之上。無論是在荸薺庵里的修習,庵趙莊里的行走,還是愛情的覺醒,明海彰顯的都是人性的光輝。庵趙莊這一僧俗融合的世界淡化了宗教追求與人性追求的矛盾,竭力營造著人情美、人性美的氛圍。
三、在理想與現實之間
汪曾祺在《關于〈受戒〉》一文中說:“我寫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⑤汪曾祺:《關于〈受戒〉》,《汪曾祺文集》文論卷,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頁。現實層面的荸薺庵,是一個亦僧亦俗的存在。即便是善因寺,看起來金碧輝煌,底子里卻也并不是完全的超凡脫俗,老方丈也并非不食人間煙火。所以,小說雖然借用了宗教概念和場景,展現了從世俗世界到神圣世界的過渡,但宗教的神圣性最終消解到人性之中。相比之下,庵趙莊才是理想世界的縮影。那里景色優美,民風淳樸,晨鐘暮鼓與打場號子相得益彰,自然和文明交相輝映。理想世界的愛情也是理想的。在庵趙莊和諧美好的氛圍里,主人公的愛情也是純真而爛漫的,成為彰顯人性、成全自我的必由之路。小說對純真愛情進行了“虛化”表現,在虛實之間淡化宗教追求與人性追求的矛盾,維系人情美、人性美的牧歌。
一方面,明海與小英子的愛情被虛化處理,在理想世界開出了圣潔的花。汪曾祺在小說后寫道:“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二日,寫四十三年前的一個夢。”①汪曾祺:《受戒》,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26頁。無論是作家創作的1980年代,還是文本指向的1930年代,庵趙莊這樣的理想世界在現實中都很難存在。小說極力淡化現實世界的痕跡,將庵趙莊塑造成世外桃源般美好的理想世界。
明海與小英子的愛情滋長過程中,很少有其他人參與。小說竭力為主人公營造著自由美好的二人世界,不受現實世界的束縛。兩人從戀愛到定情,從懵懂到覺醒,雙方父母都沒有參與。明海的父母遠在故鄉,小英子的父母也并未干涉,連荸薺庵的師父也不曾出現。愛情種子擁有最理想的生長空間,自然會開出最美好的情花。兩人的愛情成為純粹自我的行為,非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是理想世界的產物。庵趙莊是理想世界的象征,小英子的父母和荸薺庵的師父自然不會干涉兩人的愛情。但庵趙莊以外的世界,如明海的家鄉與善因寺,則是現實世界的象征。純真愛情走入現實世界會怎樣,小說似乎在極力回避這個問題,對明海的家鄉與父母所言甚少。汪曾祺致力于刻畫人性美的世界,將純真愛情置于理想世界,回避了現實世界的矛盾與沖突。
明海是家里的老幺,家道清寒,無田產可分,從小就被決定要當和尚,受戒之路是家人為明海選擇的道路。受戒后的明海,不但拿到了“和尚的合格文憑”,還被定為“沙彌尾”的候選人,將來可以當方丈,和尚之路前途光明。宗教追求是符合家人期望的人生道路。而在小說中,明海與小英子卻在受戒完成后確立了愛情,互許終身。明海在宗教追求與人性追求之間選擇了后者,也在一定程度上忤逆了家人的期許。閾限過渡時期,主人公的行為完全自由,處于理想世界與現實世界之間模糊的狀態。脫離閾限過渡的純粹空間,主人公需要復歸社會,重回現實世界。理想固然可以照亮現實,但終歸不能替代現實。兩人回去后將面對什么,該如何面對,我們不可得知。庵趙莊是一個不同尋常的世界,但愛情結局的走向,我們卻不能不考慮現實的因素——以善因寺為代表的宗教權威和以明海家鄉為代表的現實世界。汪曾祺希望表達美,給人以美的憧憬和希望。他不去觸碰現實的陰霾,不愿讓純真的愛情遭遇現實的障礙,努力塑造著烏托邦的美好。
另一方面,主人公的愛情結局在虛實之間。明海與小英子在定情儀式后劃船駛入了蘆花蕩,小說在浪漫美好的氛圍中戛然而止。蘆花蕩是烏托邦的象征,也代表著閾限空間的無限可能性。它是庵趙莊通往外界的渠道,如同陶淵明筆下那片神秘的桃林,隔絕出和諧美好的理想空間。蘆花蕩是連接理想世界與現實世界的通道,明海與小英子曾多次駛過這里,也在定情后駛入這片充滿未知的蘆花蕩。小說沒有對之后的事情做交代,進一步回避了現實的沖突,將愛情的走向懸置起來。
理想愛情遭遇現實會如何,愛情是否可以超越時代和社會的約束,這歷來是作家熱衷探討的話題。汪曾祺曾提到對他影響較深的作家,“中國現代作家是魯迅、沈從文和廢名”②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文論卷,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53頁。。魯迅的《傷逝》表達了理想愛情在現實中幻滅的主題。涓生和子君敢于打破家人與世俗的桎梏,毅然選擇理想的愛情,卻在現實的雞毛蒜皮中分崩離析。娜拉出走之后會怎樣?現實與理想的張力讓愛情始終面臨著意想不到的困境。愛之初的美好,也只能被生活的瑣屑所耗盡。魯迅冷峻地揭示了愛情的虛無,傳遞的是無法調和的悲劇感。沈從文的《邊城》也描寫了一個美麗而悲傷的愛情故事。翠翠與儺送真心相愛,卻不斷遭受著現實的變故,主人公只能在感傷中無望地等待。這里也包含著作家對人生無常、世事難料的悲劇性體驗。《受戒》與《邊城》存在諸多相似之處,主人公的天真爛漫,人們對美好愛情的渴望與追求等,但兩個小說的內在張力不同,結局也迥然有別。汪曾祺曾說過:“《邊城》是一個溫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隱伏著作者的很深的悲劇感。”①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文論卷,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128、229頁。在“悲劇感”這一點上,《傷逝》與《邊城》是相似的。魯迅和沈從文的作品中,主人公的愛情都在現實世界里碰壁受傷,呈現出難以彌合的悲劇感,引發人們無盡的思考。而在《受戒》中,“作品的內在情緒是歡樂的”②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文論卷,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128、229頁。。汪曾祺將樂觀情緒注入純真愛情,以活潑輕快的筆調處理各種矛盾和沖突。盡管主人公的人生道路和愛情追求都處于神圣與世俗、文明與自然、理想與現實的張力之中,但人性的自由似乎全然無視這種張力,始終保持著積極前進的姿態。
結 語
人類學家指出:“在儀式的閾限階段,社會的等級關系和矛盾得以化解。”③[英]維克多·特納:《象征之林》,趙玉燕、歐陽敏、徐洪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xiii、128頁。閾限空間得以打破社會等級和界限的制約,為人性發展提供超乎尋常的理想環境。事實上,無論是荸薺庵,還是庵趙莊,作為主人公閾限過渡的場所和追求無限可能性的地方,均具有雙重世界的象征意義。“(閾限)可以看作一個純粹可能性的領域。”④[英]維克多·特納:《象征之林》,趙玉燕、歐陽敏、徐洪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xiii、128頁。這里不同的價值觀念并存,世俗與神圣、自然與文明、現實與理想之間并非涇渭分明的對立,而是呈現出交融共生的狀態。這個充滿無限可能性的界域,人的本性不受拘束,性情發展擁有最廣闊的自由空間。
汪曾祺在談《受戒》時說:“我相信我的作品是健康的,是引人向上的,是可以增加人們對于生活的信心的,這至少是我的希望。”⑤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文論卷,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128、229頁。為了給人們希望和信心,汪曾祺塑造了庵趙莊這一僧俗融合、雅俗共賞、“模棱兩可、似是而非”的世界。庵趙莊作為閾限過渡的界域,正是作家所渴望的混溶狀態。在此,矛盾被弱化和消解,和諧共融觀念得以凸顯,愛情也得到最大限度的舒展,人性得以擺脫各種有形無形的束縛,最終實現突圍和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