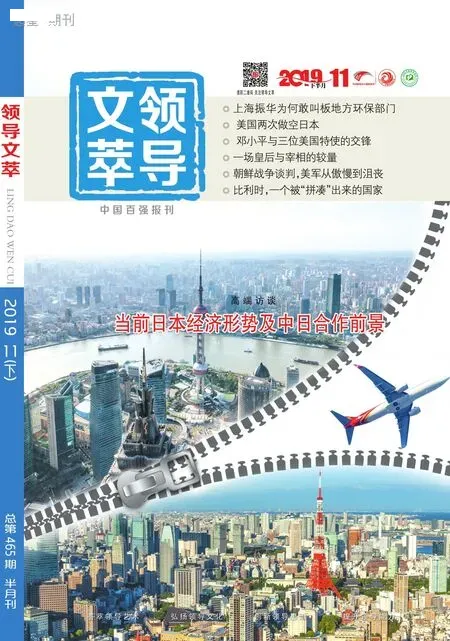如果北洋水師是左宗棠管理,甲午戰爭打日本能贏嗎?
張嵚
說起那場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清政府再次戰敗認慫的甲午戰爭,掌舵北洋水師且主持整個戰事的“中堂大人”李鴻章,至今還扛著不少口誅筆伐。而另一位“錯過”甲午戰爭的“晚清鷹派”左宗棠,卻是惹來不少懷念與期待。
作為一位親手創辦福建船政局等“洋務運動品牌”,且以抬棺出征的方式怒懟沙俄,漂亮收復西北百萬平方公里國土的老英雄,左宗棠堪稱是晚清“挨打成習慣”的憋屈史上,一位少有的給力人物。因此面對甲午戰爭的慘敗,以及《馬關條約》的狠狠一刀,好些人也生出熱烈憧憬:假如左宗棠老爺子的身子骨再硬朗一些,能撐到甲午戰爭時,且可以掌舵“亞洲第一”的北洋水師且主持戰事,那么這場“中日大戰”,結局會不會改寫?
但很殘酷的事實是,哪怕這一切假設都成真,1894年出現在甲午戰爭戰場的不是“李中堂”,而是“老鷹派”左宗棠,甲午戰爭的結果,乃至《馬關條約》的內容,也不會有多少太大的改變。當然,這絕不是因為左宗棠能力不夠。
首先一個原因是,無論是李鴻章還是左宗棠,放在甲午戰爭前夜,都無法解決當時北洋水師的困難。
在當時晚清政府眼里,海軍不過是“看家護院”的工具,所謂“海權意識”“海防安全”,滿朝文武都沒幾個懂。能有幾艘先進戰艦裝點一下門面,守住“我大清”的海上門戶,那就心滿意足。更何況大清花錢的地方多,花在海軍身上,貌似就是往海里扔。所以1891年時,大清朝就頒布了《外購軍火禁令》,別管“買船”還是“造船”,清王朝從此統統不買單,頂著“亞洲第一”名號的北洋水師,這才落到“多年未添一船一炮”的窘境。
如此境遇,就算執掌北洋水師的是左宗棠,也絕不會比李鴻章好多少。
而且,在大清朝的權貴們看來,北洋水師何止能看家護院,更是油水滿滿的肥肉。只要手“摸”得著的,都要想方設法摟一把。比如北洋水師燒的燃煤,就被開平礦務局總辦張翼擅自換成了劣質煤。那被克扣的優質煤?自然被張翼倒賣了中飽私囊,諸多王公大臣都從中敲金分肥。燒著“爛煤”的北洋水師,就好像吃著劣質食物的士兵一樣,戰斗力可以想。
雖說甲午戰敗后,北洋水師被潑了諸如“腐敗”“戰斗力低下”等各種臟水。但英國《布雷賽海軍年鑒》卻告訴我們:“黃海大戰”等甲午戰爭重要海戰上,北洋水師的命中率超過百分之二,是日本艦隊的兩倍多。日本在甲午戰后繪制的《戰艦受損圖》,更給北洋水師正了名:日本在黃海大戰里的12艘戰艦,中彈主要在“艦尾”“鍋爐”“水線下”等要害位置,公認近代世界海戰戰場上的“教科書級射擊”。
如此強大的命中率,也足以證明一個事實:盡管面臨千難萬難,但在訓練水平戰斗素質等層面,李鴻章掌舵的北洋水師,已經做到了最好。換成左宗棠?最好也只能做成這樣。至于戰況戰果,已是可以想。
而第二個原因是:就算左宗棠掌舵下的北洋水師,能夠創造奇跡打贏日本艦隊,也無法改變甲午戰爭的戰果。因為真正決定甲午戰爭局勢走向的,不是海戰,而是陸戰!
在甲午陸戰戰場上,以李鴻章淮軍嫡系為主的清軍,幾乎是一潰千里。那如果換成左宗棠“掌舵”呢?事實上,晚清王朝之前裝備最好、戰斗意志最堅決的陸軍,就是當年左宗棠麾下那支橫掃西北,懟得沙俄“改合同”的“西征軍”。但甲午戰前,西征軍的精銳都駐扎在西北要地,輕易動不得。內地的湘軍呢?早已經過了幾次裁撤,以至于士兵們“未經戰陣,槍不知用”,裝備也是“屢修屢壞”。上前線?顯然不靠譜。
相比之下,甲午戰前清王朝能用得上的,最靠譜的陸軍,依然還是李鴻章的嫡系淮軍,就算是左宗棠掌舵,也得先倚重這支軍隊。而且和許多“歷史票友”想象不同的是,比起“多年未添一炮一船”的北洋水師來,當時以淮軍為代表的清軍陸軍精銳,可謂武裝到牙齒——清王朝當時國產的后膛火炮,以及單兵步槍和仿制馬克沁步槍,樣樣領先日本。特別是作為“大殺器”的后膛炮,工藝更甩開日本9年以上。
理論上說,甲午戰爭對于清軍陸軍來說,該是個“簡單事”:碰上日軍就擺開槍炮猛轟就行。可為何又被打得丟盔卸甲,分分鐘就丟掉朝鮮半島呢?
當時日軍的戰地記錄,就還原了清軍的“優異表現”:清軍在作戰時最常干的事兒,就是“俄亂發巨炮”,哪怕只看到點敵人影子,就一頓亂開炮壯膽。步兵開火時也是“浪費彈藥”。看上去動靜震天,其實打不著幾個日軍。等著嚇一跳的日軍湊近了,把刺刀往眼前一亮,清軍就立刻“把子彈上了膛的步槍丟下一哄而散”,連“拼一把”的膽子都沒有。
這樣連“瞄準”“拼刺刀”都外行的兵,就算換成左宗棠,就算左老英雄依然熱血滿腔。戰果,依然也是可以想……
總的來說,甲午戰爭的悲劇,何止是一個李鴻章,乃至一支北洋水師的悲劇?又何止是換掉一個人,就能改變得了的?
比“左宗棠李鴻章誰行誰上”更有意義的,是那段恥辱歷史背后,多少讓人嘆息,卻歷歷在目的慘痛教訓。
(摘自微信公眾號“朝文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