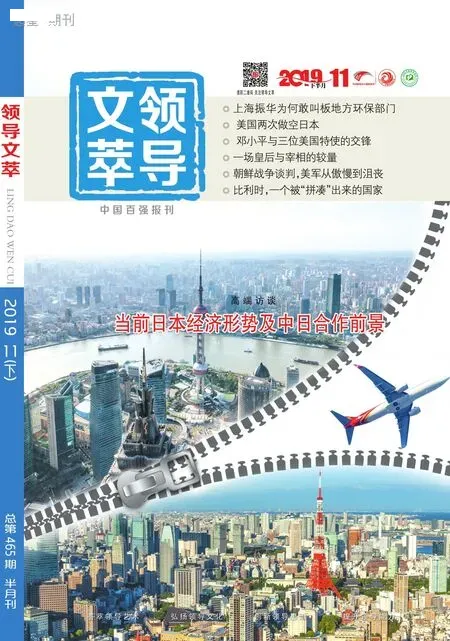信陵君的命運
趙宗彪
公元前260年,歷時三年的秦趙長平之戰結束,趙國失利,參戰的四十萬戰士被秦軍全部坑殺,只放回二百四十個孩童。能夠單獨與秦國挑戰的趙國,從此一蹶不振。秦國為了徹底消滅這個宿敵,盡管自己也已疲憊不堪,還是乘機圍困了趙都邯鄲。趙國危在旦夕。
以當時的七國而論,如果趙國被滅,秦國獨大的局面將更加明顯,誰也無法單獨與秦抗衡。秦國長期實行遠交近攻的國策,正在蠶食、擊破各個國家。為各國計,只有團結合作,共同抗秦,才是救亡圖存的唯一途徑。
作為鄰居,魏國已來了多批趙國的求救信使,希望魏國能出兵相助。秦國也派來使者警告魏王:誰出兵,下一個就攻打誰。魏安釐王雖然派出了晉鄙元帥率領十萬救兵到了鄴地,卻按兵不動,只作壁上觀。
魏王的異母弟無忌是信陵君,是戰國時期最著名的四公子之一。他養士三千,人才濟濟。他的國王哥哥,心中既高興又害怕。高興的是,有弟弟的號召力,魏國在各國間很有威信。害怕的是,萬一哪天弟弟想當國君了,自己的地位很危險。
信陵君的姐姐,是趙王之弟、著名公子平原君趙勝的夫人,她也以私人名義多次寫信給魏王和信陵君,希望弟弟倆早點來幫老姐一把。趙勝也來信對無忌說:您即使不在乎我,難道不考慮您姐姐的命運嗎?信陵君和賓客們百般勸說魏王下令迅速攻秦救趙,但是,魏王畏秦,就是不肯。無奈之下,信陵君用了侯嬴之計,讓魏王寵姬如姬竊得兵符,以力士朱亥之錘殺了元帥晉鄙,取得魏軍領導權。最終他們打敗了秦軍,保全了趙國。“竊符救趙”的典故,就因此而來。
從各國力量平衡和魏國的根本利益上說,信陵君做了一件大好事,但是,畢竟他是矯詔抗命,也有叛國之嫌,魏王哥哥的臉上也擱不住。所以,聯軍勝利后,無忌讓魏軍回到國內,自己就留在了趙國。
在恢復了幾年之后,為了報復當年魏國的不顧警告救趙,秦國首先出兵攻魏。
魏王看到大敵當前,想起了弟弟信陵君,派了使者去趙國請他回國。別離十年后,兄弟再相見,相抱而泣。哥哥授予弟弟上將軍印,讓他統一指揮全國軍隊。同時,魏國也向各國派出使者求救,以信陵君的號召力,果然趙、燕、韓、楚各國都派兵援助,五國部隊統一協作,在河外大破秦軍,打敗了秦將蒙驁,并一路西進,將秦軍打回到函谷關,再也不敢出來。
魏國保住了,但是,信陵君的處境反而更危險了。一是魏王一直擔心弟弟發動政變,而現在弟弟的威望更高,這個風險當然更大。二是秦國為了自己的利益,出資萬金,讓人在魏國到處說信陵君的壞話,說他陰謀篡權。內外夾攻下,魏王也不得不信,于是奪了弟弟的兵權。無忌既不想篡位,又不想再次流亡國外,但無以自證清白,只好從此稱病不上班。過了幾年,信陵君就死了。他的哥哥也在當年死去。
得到信陵君的死訊,秦國馬上派出當年的敗將蒙驁出征魏國,攻取了二十城。十八年后,秦滅魏,俘魏王,屠大梁。
信陵君的命運,可說是專權體制下能臣的縮影。盡管他是國王的親弟弟,但是,所有的國王都警惕任何可能對他權力構成威脅的人。一個王國或團體,最重要的資源是人才,信陵君無疑是魏國的一號人才,但是,作為國君的哥哥依然提防大于依靠,于國家于本人,都是一個悲劇。
信陵君是司馬遷最推崇的人物之一,也是戰國四公子中給予最高評價的人。行文中,司馬遷稱信陵君一口一個“公子”,從不直呼其名,景仰之情溢于言表。事實上,信陵君因為胸懷寬廣、禮賢下士,才擁有了廣泛的人才資源。那些卓越功勛,是他和三千門客集體創造的。在關鍵時刻,他的門客們都給了最好的建議,也愿意為他作出犧牲。但是,信陵君集團越能干,魏王越要提防。
如此一來,就形成了人才的逆淘汰機制:為了權力的穩定,只有讓統轄區的人越來越愚蠢,君王才會越安全。正如史學家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寫的那樣:“凡取人之術,茍不得圣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倘若一國之中,能用的和能信任的,只有愚蠢者,那么最后必定假話盛行,天天都過愚人節,而信陵君這樣的人,肯定沒有好下場。信陵君一死,魏國的命運可想而知。
(摘自《今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