蟋蟀之歌
沈喬生
幾年前,有個山東的蟋蟀販子往我家送了一批蟋蟀,一定要賣給我。看他懇切又哀求的樣子,我買了不少。
金陵名流俞律老先生也是喜歡蟋蟀的,我提了盆盂,從南京的西邊,穿過大半個城區(qū)到東南邊,按了門鈴,俞老顫巍巍迎出來,說,帶來了?喜悅之情溢于言表。此時俞老哪像87歲高齡,倒像是一個饒有野趣的少年。
這次斗蟲真可以說是蟋蟀的戰(zhàn)爭,山東的蟲從來好斗,這和我小時候玩的上海郊區(qū)的蟋蟀不一樣,那些蟲斗上幾個回合,翻一次白肚子都算是精彩的了。可是山東的蟲不這樣,還有河北一帶的蟲,斗起來都是往死里咬,咬得大腿掉了,咬得腦漿流出來了,只要還能動,依然張開一副紫牙,勇往直前。看得我們血脈僨張,直呼精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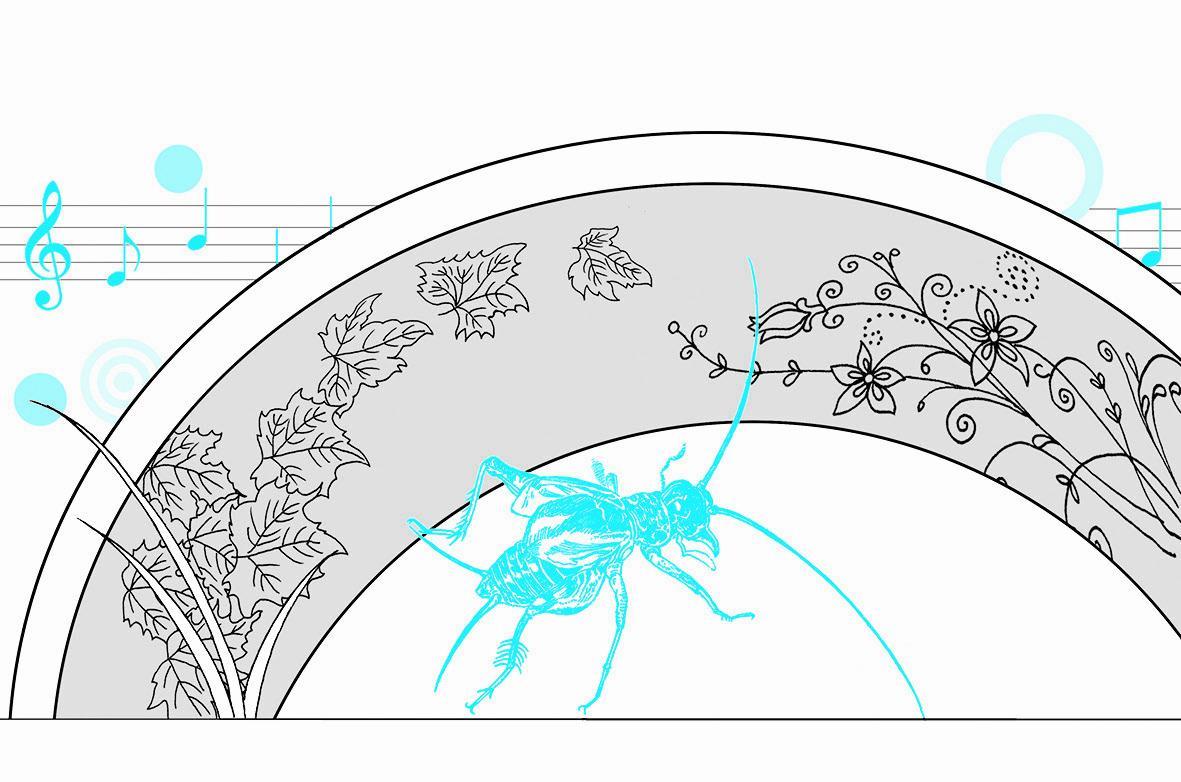
這次蟋蟀大戰(zhàn),可以說是旗鼓相當,俞老贏了幾盆,我也贏了差不多的盆數。這時候已經是晚秋了,如何讓勝利者好好地活下去,是一個課題。
很快天冷了,我就用棉襖把一個個泥盆包了起來,放進抽屜里。還是不行,沒幾天,就有蟲子先后死去。進入11月,只剩下兩只未曾有過敗績的常勝將軍,其他蟲都一一歸西了。
我想出一個法子,把熱水沖進瓶子里,然后用瓶子貼緊泥盆,再用布片把兩者緊緊綁在一起,這樣在漫長的冬夜,蟋蟀可能不怕冷了。可是早晨起來一摸,瓶里的水早冷了,我的蟲子在漫漫長夜中,是和冷水綁在一起的呀!這怎么行?
后來我又把盆放進屋里,晚上開暖氣。我把取暖器開得很大,屋里暖洋洋的,像是春天提前來了。蟋蟀也感覺到了,振起翅膀,歡快地唱起歌來。很快問題來了,我太太晚上不能睡在開暖氣的房間里,因為空氣太干,她睡不著。而蟲子又不能沒有暖氣。矛盾十分尖銳。可是,如果把它們放在另一個房間,單獨為它們開油汀,似乎又太奢侈了。于是,我只能采取折中的做法,一會兒在半夜偷偷打開油汀,一會兒把它們放進隔壁房間,把油汀也移過去。這樣期期艾艾,一只蟋蟀終于也離去了,只剩下最后一只了。
我清楚地記得,它就是我眾多蟲子中最驍勇善戰(zhàn)的一個!它是勇士中的勇士,是大將軍。然而,它軀殼的顏色也在慢慢地變化,像浮起了一層黃色的蠟,很不真實。一天,它的一條大腿脫落了,兩天,另一條大腿也掉了。我以為它的死期將近,沒想到它卻突然活躍起來,充滿了生命的質感。它用剩下的四條細腿在盆里不停地爬,如果用草逗引它,它就憤然張開一對紫色的鋼牙,和往日一樣威風凜凜。
已經12月中旬了,每天打開蓋子之前,我總有一種隱約的恐懼,擔心它會四腳朝天,成為一具尸體。可是它每次都好好的,讓我的恐懼悄然消失。后來,我開始不擔心了,它活著似乎成了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我的一個蟲友知道了,簡直不敢相信,他養(yǎng)了十多年蟲子,還沒有這么長壽的。他讓我拍了照傳給他。我拿起草,逗開它一對紫牙,讓它唱歌,還通過手機傳給那一端的朋友聽。朋友叫起來,說,聽到了,聽到了!叫得很響,很有力!
他對我說,要是拿人打比方,這蟲子已經是百歲老人了。我十分感慨,它已經沒有敵人了,它的敵人都在嚴冬一一死去了,它也沒有伴侶了,只有它還在孤獨地、勇敢地活著。美國的名將麥克阿瑟說:“老兵永遠不死,只會慢慢凋零。”這可以借用到我的蟲子身上吧。
此時,蟋蟀已經不是蟋蟀了,它成了生命的感召。只要想到,在凜冽的寒冬里,我有一只無畏地活著的蟲子,心里就暖暖的,很有力量。
然而,生命總有終結的時候,進入新年的第一天,元旦,下午3點,我的蟋蟀之王、長壽之星安然過世。但在我的心中,它沒有死,現在我還能聽見它歌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