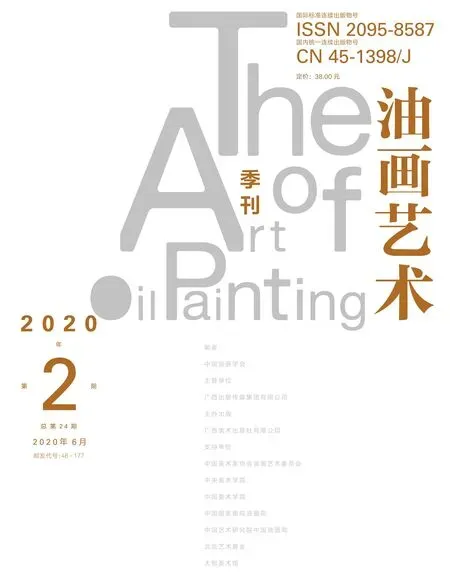從沅陵到安江村(上)
——校長滕固與抗戰初期的國立藝專
石建邦
滕固(1901—1941),字若渠,上海寶山月浦人。在民國文化史上,滕固雖然英年早逝,但無疑是一位多面手,既是小說家,又是中國美術史的開拓者,撰寫的《唐宋繪畫史》至今仍被奉為經典之作;他又積極從政,是國民政府行政院參事,負責文化藝術方面的事務。綜其一生,他在文學創作、文藝批評、美術史、藝術考古、文物古跡保護乃至學術譯介等方面均有卓著的貢獻。
1938年6月至1940年秋冬,滕固在日本侵華戰爭初期的危難關頭,毅然出任國立藝專校長,期間負責北平藝專和杭州藝專的合并事宜,并率領全校師生從湖南沅陵一路輾轉內遷,經貴陽到達昆明,后又從昆明市內轉移至呈貢縣(今呈貢區)安江村,最后遷至重慶璧山,一路備嘗艱辛。
長期以來,由于各種復雜因素,人們對這段國立藝專歷史的了解比較模糊,本文試圖以滕固為線索,對他在擔任國立藝專校長期間的事跡做一梳理和還原,以彌補這一歷史缺憾。疏漏之處,敬祈方家指正。
一
1938年6月,國民政府教育部正式任命滕固為國立藝專校長。之所以選定他接任,背后還有點故事。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日本正式對中國發動侵華戰爭,臨國難而播遷,北方很多大學相繼一路南下內遷。北平藝專在戰爭爆發不久,就在校長趙太侔的帶領下,即行南下。一路從北平到漢口再到江西廬山牯嶺。在牯嶺,學校還上了一段時間的課。后戰事緊迫,于這年11月到達沅陵老鴉溪復課1,還有一部分師生像龐薰琹等人,是于1938年元旦后到達湖南沅陵的2。
至于杭州國立藝專,大約是在11月中旬開始轉移內遷的。據學生丁天缺回憶,“11月13日一早,學校貼出布告,稱奉浙江省教育廳命令,即日撤退到諸暨湖墅。要求凡愿隨校內遷的同學,于當日下午二時前,將行李送到總務處,由學校統一辦理運輸,下午四時到南星橋碼頭集中乘船過江”3。
當時校長林風眠匆忙帶領二百多個師生員工離開西湖,向內地轉輾流亡。師生一路經浙江諸暨到金華再到江西鷹潭,在貴溪短暫上課后再啟程赴湖南長沙,在長沙逗留一個月,最后到達沅陵。據當時杭州藝專教務長林文錚從長沙寫給他岳父蔡元培的信,學校“于去年(1937)十二月遷至江西貴溪縣城,上課二星期,即舉行學期考試,今年一月五日試畢。十日遷湖南,十五日抵長沙,假雅禮為宿舍”4。丁天缺說他們“在長沙逗留近一個月”,才由水路穿過洞庭湖,先到常德,逗留十多天,再換乘汽車,直達沅陵。這么算起來,杭校師生到達的時間大約在1938年2月下旬。5
當年1月25日,在國民政府行政院召開的第347次會議上,教育部提出合并北平藝專和杭州藝專兩校,改為國立藝術專科學校的議案,得到正式通過。6當時教育部部長陳立夫剛剛上任,他任職教育部部長七年,實事求是地說,為戰時教育事業做了不少好事。他主持擬定《戰時各級教育實施方案綱要》及實施要點,組織教育部人員將愿意從軍抗日的流亡師生送至軍校或軍訓班,將年幼及愿繼續上學者安置入學并供給生活費。“他推動各大學在后方單獨或聯合復校,使大學生可以各回原校;在后方城鎮建立一批國立中學及教師服務團,設立貸金制用于衣食住讀,以保證十余萬師生能繼續學業,俾使教育事業不因戰爭而中輟。”7
當時的校址暫定設在湖南沅陵,兩校合并后教育部指令專門設立了一個校務委員會,校委會由林風眠、趙太侔和常書鴻三人組成,并指定林風眠為主任委員。這一安排看上去似乎很公平,但實際上必然埋下后患,因為北平藝專占了兩個席位,對林風眠這個主任委員而言很多時候根本無法行使職權,必然造成“三個和尚沒水吃”的局面。所以從兩校合并開始就矛盾不斷,使學校無法走上正軌。
二
沅陵是湖南湘西的門戶,湘西是政治、經濟、文化重鎮,依山傍水,風景秀美。在抗戰時期,一時也有很多文化機構暫遷此地,或者經過此地再輾轉貴陽和昆明。
兩校合并后,雙方矛盾重重。
原因很復雜,首先是北平藝專因為先到,人員不多,共有學生四十多人,教師六人,職員七人,舊居圖書也極少。他們從廬山遷到沅陵后,就在城對岸老鴉溪邊上租下一家私人宅院,略加修整就做了學舍。而杭州藝專后到,師生一共近兩百號人,還帶來很多圖書教具,一時找不到合適的落腳處,不得不暫住北平藝專的學舍內,很多生活瑣事引起雙方矛盾。
其次,杭州藝專一路顛簸過來,由于人員眾多,還運來很多教具圖書和設備,因此到達沅陵時學校經費所剩無幾。所以當第一次校務會議,常書鴻提出兩校各拿一部分經費為應急之用,林風眠沒有辦法拿出來。后來談到將來遷往昆明的計劃,林風眠他們的杭州藝專方面更沒有辦法籌措經費。8
最后,更不容易回避的問題是,兩校教學程度和教學方式也存在很大的差異。北平藝專系大專設置,入學招的是高中畢業生,很多是沒有任何繪畫基礎的,需要從頭學起;杭州藝專從預科讀起,初中畢業即可報考,兩校合并之后是依學年而非繪畫程度分班。這樣導致杭校四年級的學生僅僅相當于大一,雖然有三年嚴格的專業訓練,卻只能與剛進校門的北平藝專一年級學生同班上課。如此懸殊的水平,不僅老師在教學過程中感到顧此失彼,同學之間相處,在學業交流上也有不少困難。而且,兩校校風,彼此提倡的藝術理念也同樣大相徑庭,甚至南轅北轍。9
諸如此類的矛盾,還有很多,正如劉開渠說的“這時的藝專是個復雜的混合體”10。
校務委員會中,林風眠雖然是主任委員,但趙太侔和常書鴻有兩席位置,導致很多事情他無法拍板做主,相互間掣制得非常厲害。趙太侔(1889—1968)是戲劇家,早年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1925年回國后,應聘為北京藝術專門學校教授,兼戲劇系主任。北伐時期,他在國民政府任外交部秘書,后參與籌備山東大學(籌備過程中,蔡元培主張將山東大學設在青島,國民政府教育部指令將山東大學改為青島大學),并任山東省立第一中學校長、省立實驗劇院院長等職。他先后兩次擔任山東大學校長,辦學經驗豐富,能量巨大。所以平心而論,當時無論從年齡、資歷甚或人脈關系等方面來看,林風眠都不是趙太侔的對手,國立藝專很多老師當時就明確提出要讓趙當校長。
其間,南北兩校各推四位教員開會,北平藝專方面有龐薰琹、李有行、王曼碩、王臨乙四位教授,杭州藝專有李樸園、王子云、雷圭元、劉開渠。八位教授參與校務決策,提了些建議,并推舉李有行為教務長。11
這八位教授均頗有名望,北平藝專的龐薰琹(1906—1985)留法學習油畫,回國后發起組織“決瀾社”,后來在工藝美術方面有重要成就,是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的籌備人。李有行(1905—1982)留學法國里昂,學的是染織設計,回國后在上海美亞印染廠擔任設計工作,他在北平藝專圖案系的教學很受歡迎,因為既熟悉業務又懂得如何教學,由淺入深,結合得很好。王曼碩(1905—1985)畢業于日本東京美術學校,油畫家。1938年赴延安,任魯迅藝術學院美術系主任,1954年后任中央美院副院長。王臨乙(1908 — 1997)是雕塑家,曾師從徐悲鴻,并兩次留法學習,新中國成立后任中央美院雕塑系主任。杭州藝專的李樸園(1901—1956)博學多才,既是戲劇家又是美術史家、美術理論家,還組織“藝專劇社”,非常活躍。王子云(1897 — 1990)和劉開渠(1904 —1993)兩人都是雕塑家,都是安徽蕭縣人,又都留學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后來各有非凡成就。雷圭元(1906— 1989)是現代工藝美術家和教育家,早年留學法國,學習染織和漆畫,回國后在杭州藝專任教,負責圖案系教學多年,新中國成立后他與龐薰琹一起參與中央工藝美院的創建。
不久,八位教授兩次聯名寫信給主任委員林風眠,內容大有質詢問難之意,林風眠受不了,于3月14日一早出走。杭校學生聽到這個消息后發動學潮,敦促趙太侔、常書鴻將林風眠請回來。
藝專師生將林風眠請回來不久,由于仍然無法解決兩校之間、師生之間、教授之間乃至學校和教育部之間錯綜復雜的矛盾,最后林風眠還是黯然離去。后來,趙太侔也迫于壓力辭職。
作家沈從文是湘西鳳凰人,1938年1月中旬,沈從文當時帶了幾個人正好路過沅陵,小住在他大哥沈云麓家里,前后長達三個月。沈從文當時也從側面耳聞目睹了一些有關藝專學潮的情形:
過不了幾天,學校出了事,鬧起風潮來了。一鬧風潮,糾察隊,打架隊,以及什么古怪組織都一起出現了,風潮且牽涉到每一個教員。文錚原是杭州美專的教務長,自然也牽扯在內。以后教育部派了陳之邁先生來調停此事時,借用我家房子開會,有些學生竟裝作寫生,分批來到我家大門前作畫,以便探聽誰進誰出。我覺得這些人行為可鄙,十分討厭……這些讀書人來到后方,卻打來鬧去,實在看不慣。且明白糾糾紛紛,是非混淆,外邊人也毫無辦法。很有幾個“藝術家”疑心多,計策多,沾上去說不定還有人以為我也在內,要奪他們臭皮蛋!12
在這一事件調停中,林風眠曾有信給陳之邁,要求了解龐薰琹、王曼碩等人向他反映了什么情況。13
藝專學生個性強烈,尤其杭校鬧學潮當時是出了名的。此次藝專風潮,前后長達兩個多月。杭校學生彥涵(劉寶森),被推選為學生自治會主席,不但領導罷課,還接管學校的伙房、財務等部門。當時師生中有不少人要求進步,積極投身革命。風潮過后,彥涵就和王文秋、陳角榆等幾個同學在老師盧鴻基,同學羅工柳、楊筠等人影響下,放棄學業,離開沅陵,正式投身革命,奔赴延安。14
三
正是在這樣一種矛盾僵局下,教育部部長陳立夫、次長張道藩等人經過一番權衡,決定指派滕固當校長。
在當時來說,之所以選擇滕固確實有不少考量。首先,滕固既不是北平藝專的人,也不是杭州藝專的人,與兩校沒有瓜葛。其次,他是留德博士,在中國藝術史和文物古跡研究方面頗有成就,而且過去也在上海美專等校上課,在行政院任職后還兼任中山大學、金陵大學教授;他還擔任故宮博物院理事、中央古跡調查委員會常務委員等職務,在學術界頗有名望。最后,也許最重要的是,滕固從政多年,在行政院負責文化藝術方面的工作,有豐富的行政經驗,懂得官場運作規矩,和政府各部門之間比較容易溝通協調。
而對滕固來說,他當時之所以接受這一任命,一來雄心勃勃,希望在美術教育方面發揮自己的專長,為中國美術事業多做貢獻;二來,他為人正直樸素,很不喜歡行政院的官場作風。用好友朱偰的話說:“若渠個性,豪放不羈,固不宜久處幕僚;且群小當道,邪正不分,當局雖震于其名,屈為延攬,然若渠崇尚氣節,早萌去志。”15所以他當時欣然接受這一任命,希望借此機會一展抱負。
用空白血清制備低、中、高濃度的質控樣品,每個濃度質控樣品取6份測定作為日內精密度,連續檢測3天獲得的結果作為日間精密度。向空白血清中加入低、中、高濃度的標準品,每個濃度各取6份,通過計算檢測值與加入的標準品的比值,取平均值得到回收率。結果表明,各藥物的日內、日間精密度(RSD%)均小于15%;平均回收率在90%~110%。見表4。
四
6月13日,滕固正式得到教育部任命,被聘為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校長,不久即赴湘西沅陵履新。當時教育部等機關大部分還在武漢,16日那天,滕固從重慶飛到漢口。
在漢口待了一個多星期,滕固于6月24日啟程赴長沙,四天后即動身前往沅陵,29日那天抵達沅陵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到任。
滕固到校后即雷厲風行,大行整頓。7月1日,是學校新學年的開始,滕固到校視事,正式開展工作。那天他“攜總務長楊某及會計員二人來,手諭當天未到校之教職員,不論是否請假,均停職”16。
滕固對師生作訓話,提出自己的辦學宗旨:“以平實深厚之素養為基礎,以崇高偉大之體范為途轍,以期達于新時代之創造”,“切戒浮華、新奇、偏頗、畸形”。另外,根據當前戰火紛飛的戰亂形勢,藝專應擔負并注重抗日宣傳人才和中小學藝術教育師資之培訓。17一番演講,頗得學生方面好感。
在具體整頓上,滕固針對教職員工管理制度大刀闊斧,實行改革,擬定了校務方針及辦學經費使用辦法,非常具體,概括而言有以下幾條18:
一、凡本校教職員中已離校或素不在學校所在地之人員,不論聘任委任,自即日起一律停職。
二、本校各處館分配工作,指定人員所有職員暫照頒布的表格中分配工作,未指定工作人員即予疏散。
三、查明這數月來發去薪金的實數。確定經費支配之原則:辦公估15%,事業估20%,薪給65%。
四、薪酬分級出差辦法。
一級有兩類:甲類400元,乙類210—300元;
二級:100—200元;
三級:60—90元;
四級:35—55元。
這樣一來,杭州藝專的十多位教師都被滕固裁掉了,連蔡元培的女兒蔡威廉、女婿林文錚也未能幸免,其他還有黃紀興、李樹化、張光等人,均被停職。黃紀興是蔡元培的內弟,教授法語,因為當時正在休假,晚到了幾天,也被去職。北平藝專的教師也走掉不少。
據劉開渠夫人程麗娜回憶,滕固到任后,本來也要開除她的,當時有一條理由是“夫妻不能同時留用!”結果滕固那天看了程麗娜主演的戲劇《偉大的女性》,是藝專戲劇教授李樸園為她量身定做的,竟大受感動。李樸園乘機與之商量留下她,滕固馬上就同意了,讓她擔任戲劇指導。19由此也可看出滕固為人性情的一面。
為了加強師資,充實教學力量,滕固又另聘他的留德同學徐梵澄和夏昌世。徐梵澄(1909—2000)是學哲學的,教西洋美術史的課。他上課很認真,而且博聞強記,對國學非常精通,慢慢贏得了學生的尊敬,像丁天缺后來就很服帖他。夏昌世(1903—1996)是學建筑的,他是后來到的,滕固為他破例辦了一個建筑班。20留法學者秦宣夫原來是北平藝專專任教員,1936年因校長換人而去職,這時他在南下途中通過朋友介紹也得到滕固邀約,來到沅陵任教,負責素描、美術史和法文等課程。21
訓話的第二天,滕固就給行政院的好友陳克文、端木愷寫信,敘述接收國立藝專情形:“此間校內混亂不堪,一切真如兒戲,現正整理行政,樹立種種辦法,俾納正軌,麻煩誠麻煩,但亦覺有味。”“此間生活苦極,又患腹瀉,只好磨練磨練吧!”22言辭之間,躊躇滿志。7月22日,他給陳克文的信里又說,“校務機構已調整,減薪及疏散人員,皆無反響,亦可謂初告成功也。此后但望國家環境好,學校亦必蒸蒸日上也”23。7月30日的信中,他又說校務進展順利,深信“事在人為必成,去取中理必信”24。可謂信心滿滿。
蔡元培先生在香港得知女兒女婿雙雙遭到解聘的消息,非常關心,曾打電報給滕固(7月4日),甚至請褚民誼致函滕固,請他們兩人多有關照,希望能保留教職。一直到7月24日,滕固才寫信請葉恭綽帶給蔡先生,“言林文錚及威廉教部另有借重,故未續聘”25。不知道是托辭還是橫生變故,后來就沒有了下文,弄得他們夫婦倆帶著五個小孩滯留沅陵,失業等待,不久來到昆明謀事。
當然,滕固在沅陵處理繁雜的校務,面對錯綜復雜的人事關系種種,尤其是在兵荒馬亂的情勢下,有時也不免情緒低落。好友朱偰曾回憶,“抗戰軍興,輾轉西遷,若渠由湘入黔,小駐沅江,嘗有詩云:‘十年低首斂聲華,悔將干將待莫邪。今日荒江驚歲晚,扶膺惟有淚如麻。’蓋其內心生活之苦悶,不禁流露于文字間也”26。這首詩大概寫于1938年歲末,他孤身一人在此偏遠小鎮,難免有寂寞無助的感慨。
在正常的上課教學之余,滕固還帶領國立藝專全體師生投入到抗戰宣傳工作中去,辦星期補習班,舉辦抗戰宣傳訓練課等活動。
“八一三”周年紀念日,國立藝專特別組織舉辦了一次抗敵宣傳藝展,部分作品還被登載到重慶《中央日報》等報刊上。滕固為展覽專門撰寫介紹文字,鼓勵學生的愛國熱情:
這些作品在短期間急就的,制作的同學們都不是木刻的專習者,在技巧方面自然不敢說有怎樣的成就,然而在一刀一筆之間,深深嵌進了我民族抗戰的偉大的一年間之高貴的血跡和淚痕,是不可否認的,這些作品已顯示出一種生辣銳利的面對現實的新風格。
把木刻稱作“刀筆”,不太牽強吧,這些刀筆的背后,蘊藏著不可抵抗的民族的偉力,因此我們不能僅視它為本校若干同學的制作品,簡直可視作為百千萬青年的熱血所噴澆出的火漿,使敵人在這不可向邇的火漿前發抖。27
五
經過滕固的一番努力,國立藝專粗粗安定下來,漸漸走上正軌。1938年雙十節那天,校長滕固特別頒布國立藝專校訓——“博約弘毅”。
在校訓告示中,滕固專門撰文解釋“博約弘毅”四字,取自《論語》,孔子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滕固說:“大哲之所教示,前賢之所引申,義至明顯,我人立身行己,貴乎博約,開物成務,期以弘毅,愿諸生身體而力行之。”
在抗戰烽火的特殊時刻,滕固飽含感情,在《校訓》中對藝專師生寄有更深切的期望:
本校創立于抗戰發軔之秋,民族存亡,系于一發,國家休戚,匹夫有責。我人于曾子弘毅之旨,尤須深切體認,服膺勿失。夫在抗戰酣激,將士沐血,同胞死難,老弱溝壑之時,吾人猶得享受國家之教養,國家之厚我者至矣盡矣。我人宜急起直追,力自振奮,恪遵總理立志做大事及人生服務之明訓,苦心志,勞筋骨,餓體膚,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以身許國,知有國而不知有身,挽救危亡,復興民族。茍人人能負重任,人人能致遠路,則不特抗戰必勝,建國必成,而世界人類亦將同蒙福利。完成一己之志業在此,所以圖報國家者亦在此,諸生勉乎哉。28
滕固在雙十節頒布這一校訓,一來表示自己正式“接管”國立藝專成功,各方面走上正軌;二來鼓舞學生士氣,明確學習方向。另外,當然還有向國民政府教育部擺功示好的意思在。
不過平心而論,在抗戰期間國民政府能盡力保障學生安心讀書,確實頗不容易,想了各種辦法。藝專學生鄭為曾在生前和筆者聊起,他們那時讀書是不要錢的,即使像他到別的大學去吃飯都不要錢。他在重慶讀書期間,經常到中央大學去聽傅抱石等人的課,中間在中央大學食堂吃飯,并不收取分文費用。這是抗戰期間對莘莘學子的特別優待。
六
但好景不長,在沅陵還沒有安定幾個月,日寇戰火隨之蔓延過來。
1938年10月25日,武漢失守。11月10日,日軍攻占岳陽,緊逼長沙。13日凌晨,發生“長沙大火”,燒了五天五夜,官方公布死亡三萬多人,一座兩千多年的古城被夷為廢墟,損失無法估量,黎民流離失所,紛紛逃難。國立藝專雖在沅陵,同樣也受波及,士兵難民紛紛涌來,各種物資告竭。11月27日,滕固在給陳克文的信中說:
長沙大火真真悲慘而滑稽,沅陵大受影響,蓋難民士兵叢集,糧食米鹽告缺,幾乎鬧亂子。又日夜警報,民眾紛雜異常,入晚槍聲不絕,蓋擊逃兵與鎮壓小匪也。弟除校務外,尚擔任湘西抗敵宣傳團副團長(此系中央駐沅及地方各機關會組,陳榘珍為團長),即毅然參加安定工作,不睡者三夜,如臨前敵,……現算告一段落,一切略如常態矣。回想一過,不覺可痛可笑。弟現在才感到在院中的一切快適安靜,無憂無慮,然大丈夫過過此等生活,亦殊值得,弟至今亦不悔之。29
信中提及的陳榘珍(1882—1952)系湖南鳳凰人,早年畢業于湖南武備學堂,并曾加入同盟會。他號稱“湘西王”,在當地很有影響,當時也幫助藝專師生做過不少事情,還幫劉開渠造了一個雕塑工作室。30
國立藝專隨之奉教育部命令開始遷滇計劃,12月中下旬,師生開始分批向貴陽遷移。滕固為此作詩鼓勵學生,振奮士氣:
抗戰經秋又半年,軍容民氣壯于前。學生亦是提戈士,南北賓士路萬千。31
轉移過程一路坎坷艱辛。當時轉移的方式多樣,師生有的自行尋找交通工具,如搭汽車、黃魚車等分散前往,有的則隨藝專包車集體行動。據學生阮璞回憶,他們當時是包車南遷的,車隊司機都是從南洋歸國駕車支援抗戰的愛國華僑,人稱“南僑機工”,年輕膽大。結果有一天,他們有三輛車從芷江出發,一輛車在湘黔交界叫冷水鋪的附近遭遇土匪搶劫,把很多人的衣服都剝掉了。司機耳門中了一彈,幸無大礙。后來幸好有軍隊趕到,把土匪打跑。學生們在河中看到幾具土匪的尸體,以及被撕毀的學生課本、紙張,散落一地,河邊有被土匪燒毀的房子,還有幾個土匪的首級被掛在木牌上示眾。32
有女生回憶,那天他們是倒數第二批撤離沅陵的,時間應在12月13日,由教戲劇的李樸園老師和“周教官”等人跟車隨行,結果路上碰到土匪,被洗劫一空。除了搬不動的教具外,行李外套、書本鈔票等全部被拿走了。大家的心情非常沮喪,車到貴陽,準備下車。駕駛員指著一摞臉盆說:“把東西帶走。”有同學說:“什么都沒有了,還要臉盆嗎?”沒有一個人肯去拿。等到了住處要洗臉時,大家才感到自己的無知可笑。33
遷校時,以研究生李霖燦為首的七名學生,還組織了一個步行宣傳團。滕固對此大加贊許,并加倍發給路費。乘汽車者十六元,步行團每人發給三十二元,并請沅陵行署發一公文護照,以利沿途方便。
據參與者李浴回憶,步行宣傳團出發的時候,“全校師生,有為之擔憂者,有為之壯行者。因為當時湘黔公路很不太平,明暗之匪徒時有出沒,搶劫殺人之事時有發生。幾名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學生,徒步宣傳抗日,自然會引起師生們的震驚,但滕校長卻非常支持。邱璽先生特為步行團繪制了團徽。于是一行七人,身背宣傳品、畫具與行囊上路,沿途開展覽會,畫壁畫,進行宣傳。確也遇到一些驚險的場面,最終均安然度過,平安到達昆明新校址。我是七名行者中的一員,收獲之大親有體會。事隔五十年,記憶猶新”34。
七
1939年元旦前后,國立藝專師生陸續抵達貴陽,并作短暫停留,休整復課。先遣隊事先聯絡了天主教堂和育嬰堂作為藝專的臨時校舍。校長滕固勞累過度,痔瘡發作,住院割治。期間校務及搬遷善后事宜委托常書鴻等人負責。
2月4日,貴陽遭遇日軍大轟炸,藝專部分老師借住的旅館被炸毀,幸無人員傷亡。常書鴻的行李書籍等物化為灰燼,只在瓦礫中找到自己在巴黎學習時的兩塊獎牌。幸好他本人那天去醫院看望校長滕固,僥幸躲過一劫。35
對那次貴陽大轟炸,藝專師生們都刻骨銘心,吳冠中晚年回憶起當時的恐怖情景:
那一天我爬到黔靈山上作畫,眼看著一群日本飛機低飛投彈,彈如一陣黑色的冰雹滿城起火,一片火海。我丟開畫具,凝視被死神魔掌覆蓋了的整個山城,也難辨大街小巷和我們所住的天主堂的位置。等到近傍晚解除警報,我穿過煙霧彌漫的街道回去,看到到處是尸體,還有大腿掛在歪斜的木柱子上,皮肉焦黃,露著骨頭。我鼓著最大的勇氣從尸叢中沖出去,想盡快回到天主堂宿舍。但愈往前煙愈濃,火愈旺,烤得我有些受不了,前后已無行人,只剩我一人了才發覺市區道路已根本通不過,有的地方余彈著火后還在爆炸,我急急忙忙退回原路,從城外繞道回到了天主堂。天主堂偏處城邊未遭炸,師生無一罹難,只住在市區旅店的常書鴻老師的行李被炸毀一空,慶幸人身無恙。36
在貴陽養病,學校即將轉移昆明復課期間,滕固曾寫報告給教育部,總結自己執掌藝專七個多月來的心情,自謂“對于人事之調整,秩序之安定,課業工作之恢復,最低設備之補充”等做出了許多努力和改善,但離自己的目標還有不少距離。在負責全校教師學生遷滇過程中,滕固更是兢兢業業,“對于學生之沿途工作及訓導,邀各教員全數參加,使師生于困難之中,認識現實社會,約束向上,以表現國家學府之尊嚴”37。
1939年2月底,藝專師生先后分批到達昆明,從此翻開新的一頁。
注釋
1.常書鴻:《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甘肅文化出版社,1999,第32頁。
2.龐薰琹夫人袁韻宜所著《龐薰琹傳》(北京工藝美術出版社,1995年)第93頁記載,1937年12月31日除夕,龐薰琹和師生是在沅江的船上度過的。
3.丁天缺:《夢里孤山——丁天缺藝術人生》,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8,第27頁。
4.王世儒編《蔡元培日記》,1938年2月15日條,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5.丁天缺:《顧鏡遺夢》,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05,第22頁。
6.沈寧編著《滕固年譜長編》,上海書畫出版社,2019,第432—433頁。
7.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朱信泉、婁獻閣主編《民國人物傳》第十二卷,2005,第53—54頁。
8.鄭重:《林風眠傳》,東方出版中心,2008,第137—138頁。
9.朱晴:《朱德群——從漢家子到法蘭西院士》,河南文藝出版社,2007。
10.鄭重:《林風眠傳》,東方出版中心,2008,第136頁。
11.龐薰琹:《就是這樣走過來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第157—158頁。
12.沈從文:《記蔡威廉女士》,載《沈從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
13.林風眠:《林風眠長短錄》,中國青年出版社,2014,第191頁。
14.孫志遠:《感謝苦難——彥涵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第104—114頁。
15.朱偰:《天風海濤樓札記》,中華書局,2009,第165頁。
16.王世儒編《蔡元培日記》,1938年7月9日條,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17.沈寧編著《滕固年譜長編》,上海書畫出版社,2019,第444頁。
18 .同上。
19.程麗娜:《人生是可以雕塑的——回憶劉開渠》,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
20.談健、談曉玲:《建筑家夏昌世》,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12,第67頁。但書中說他擔任過國立藝專教務長,不準確。
21.秦宣夫:《秦宣夫自述》,載《秦宣夫文集》,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第399頁。
22.沈寧編著《滕固年譜長編》,上海書畫出版社,2019,第446頁。
23.同上書,第447頁。
24.同上書,第448頁。
25.王世儒編《蔡元培日記》,1938年7月4日、5日和8月2日條,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26.朱偰:《天風海濤樓札記》,中華書局,2009,第165頁。
27.沈寧編著《滕固年譜長編》,上海書畫出版社,2019,第449頁。
28.根據《校訓》原件照片整理。
29.沈寧編著《滕固年譜長編》,上海書畫出版社,2019,第451頁。
30.紀宇:《雕塑大師劉開渠》,山東美術出版社,1985,第115頁。
31.李浴:《滕固和他的一首抗戰詩》,載沈寧編著《滕固年譜長編》,上海書畫出版社,2019,第452頁。
32.阮璞:《往事如煙》,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05,第166頁。
33.唐冠芳、張玫白:《憶遷黔途中二三事》,載吳冠中、李浴等著《烽火藝程——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校友回憶錄》,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1998。
34.同注31。
35.常書鴻:《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甘肅文化出版社,1999,第33頁。
36.吳冠中:《出了象牙之塔》,載《烽火藝程——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校友回憶錄》,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1998。
37.沈寧編著《滕固年譜長編》,上海書畫出版社,2019,第4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