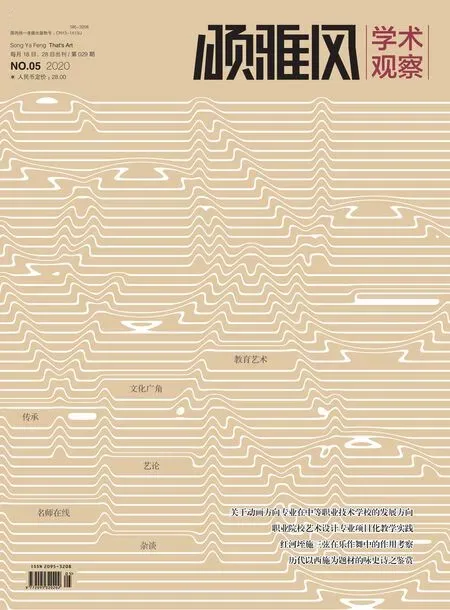論冀中笙管樂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關系
◎郭婧
冀中笙管樂進入學界視野并得以極大關注,起源于屈家營“音樂會”這第一顆打破冀中平原一池平靜的鵝卵石,繼而由張振濤執筆在《中國音樂年鑒》1994、1995、1996年三卷連續發表約十萬字的《冀中、京、津地區民間“音樂會”普查實錄》五十家“音樂會”的普查報告,引發學界的軒然大波,而事實證明,其影響遠遠超乎想象。幾乎北京地區所有音樂學專業的專家學者悉數參與其中、走向田野,以此作為研究對象的學術成果不勝枚舉。四人考察小組中的三位學者張振濤、薛藝兵、鐘思第分別完成了博士論文《笙管音位的樂律學研究》《冀中鄉村禮俗中的鼓吹樂社——音樂會》《神圣的娛樂——中國民間祭祀儀式及其音樂的人類學研究》《中國民間樂社》。
學者們以點帶面,以時間為軸,越來越多個案調查、志式撰寫如雨后春筍欣然呈現。這些記錄,一方面將冀中笙管樂種從歷史的民族音樂學角度“溯流探源”沿著“傳統是一條河流”奔涌向前;另一方面秉承“把目光投向當下”,以周密計劃考察與民族志式的客觀記述,在先進科技手段的輔助下精準刻錄冀中地區“音樂會”活態存見的現場畫面。
冀中笙管樂其主奏樂器管子,另有笙、笛、云鑼、鼓、板、鐃、鈸、鐺子幾件樂器合奏,演奏風格古樸祥寧。音樂會多伴隨宗教及祭祀儀式所用,與傳統禮儀、民間信仰緊密相依,且從不參加婚禮、生子等民間俗事活動,長期以來由于義務服務民間,擁有較高威望。對于村莊而言,傳統的鄉村儀式與國家制度的對立致使依附于儀式共生的音樂文化一度也被認為是陳風陋俗,隨著時代變遷和人們觀念的轉變,傳統的宗祠祭祀、春節祈祥、中元祭鬼、祈雨驅雹儀式或寄予新的禮俗樣式,或刪繁就簡。然而,葬禮是任何一個家庭組織所必要經歷的生活程序,承載家庭失親的哀念寄托,接受鄉鄰里舍的吊唁悲悼。在這與百姓的生活習俗息息相關、再也無法刪減的葬禮中定會請來音樂會演奏,也正因如此,音樂會沒有消亡。
冀中地區音樂會數量龐大、較為集中,這個地區為何有這么多的音樂會,有什么功能,又是如何生成的,皆成為學界普遍關心的問題。這其中涉及其律、調、譜、器的本體研究林林總總,對其歷史、傳承、樂社結構的采錄考察亦未盡其詳。
在樂器研究方面,音樂會所使用的樂器十七管滿簧全字笙保持著唐宋時期的笙制,黃鐘標準保持著漢代鼓吹樂黃鐘=E的律高標準;南樂會使用大管子主奏,北樂會使用小管子主奏;九孔管子與唐宋形制一致仍見使用;打擊樂器百年以上歷史。在宮調研究方面,大管子與小管子音高相差四度,一套樂器可以奏全四宮,兩套不同調高的樂器實際配應著兩套四宮,相當于把原先的四宮系統擴展一倍,即拓展了古代音樂宮調實踐范圍。在曲譜研究方面,冀中音樂會歷史悠久的重要依據即各樂社一般均藏有古老的手抄譜本,據考察約有80種,除保留大量傳統曲目,在封面、扉頁、序言等處一般記有傳抄時間以及相關背景信息,如合莊譜本傳自乾隆五十二年;記錄的曲目多與唐宋詞牌和元明戲曲曲牌、小令曲名一致,其中大曲子演奏時長可達一小時以上,一般具備“頭—身—尾”固定邏輯,即頭(序曲)—身(幾個固定曲牌連綴,第一個曲牌名稱為套曲名稱,如《普庵咒》《錦堂月》)—尾(固定結尾方式《金字經》《五聲佛》《四季》《撼動山》)。在樂社研究方面有一批代代相傳的農民樂師多達數百人陣容龐大,其傳承方式有師徒傳承、家族傳承、樂社間的傳承。
“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層、更持久的力量。中華文化獨一無二的理念、智慧、氣度、神韻,增添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內心深處的自信和自豪。”應該說,現在進入該課題的學者何其幸運,在這前序的三十年中已產生諸多如燈塔般的研究成果可供參鑒。前輩學者的孜孜以求開疆拓土已一步一個腳印、如工筆畫般細細填描勾勒了一幅活色生香的“冀中笙管樂版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