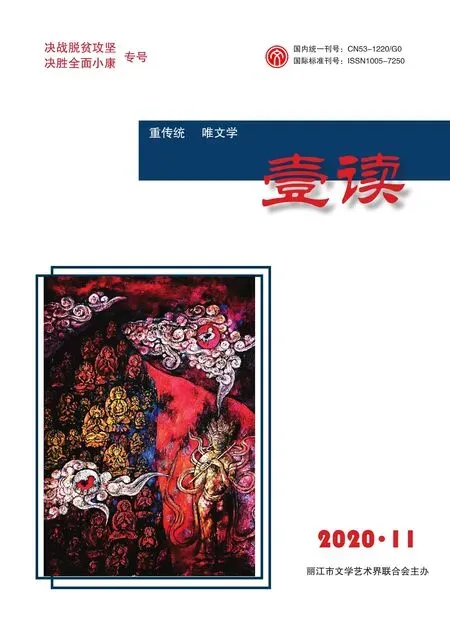木呷的身份
◆黃立康
黨員木呷
“今年是我國脫貧攻堅的決勝之年,在云南省麗江,駐村扶貧第一書記吉克木呷常年奔波在大山深處。吉克木呷在駐村一年期滿后,仍主動要求繼續留下,他說,他要站好最后一班崗。”這段話來自中央電視臺13 頻道2020年5月6日午間的“新聞30 分”欄目,新聞的標題是“吉克木呷:站好精準脫貧的最后一班崗”。同天下午的“新聞直播間”以“以青春的名義”為主題,播放了吉克木呷的駐村故事。而早兩天在5月4日的中央電視臺1 頻道的“新聞聯播”,就已經播出了吉克木呷扶貧的事跡。
你可能想問:吉克木呷是誰?這個問題答案千種,對于我來說,吉克木呷是我的同事,但在所有麗江市文聯的同事里,他是和我們相處的最少的那個,他一直在麗江市寧蒗縣春東村委會駐村扶貧。春東村深藏在金沙江畔的大山深處,是寧蒗縣最偏遠、交通最差的一個深度貧困村,全村522 戶人家中有164 戶貧困戶,貧困發生率高達38%,這樣的脫貧攻堅戰,在我看來,如同在鉆石上雕刻。當我們坐在明亮的辦公室面對著電腦校對《壹讀》雜志時,木呷的辦公室在草木包裹、風雨侵襲的原始蒼茫大山間;當我們手指輕按、調整一個逗號、讓一個句子變得順滑通暢時,木呷的雙腳走在雨后泥濘的山間鄉道,一步一滑,步步驚心;當我們為因投稿作者錯別字滿篇的文章“別有幽愁暗恨生”時,木呷頂著風云烈日眺望“東邊日出西邊雨”的扶貧之路。我無法體會木呷行走山野的疲憊,汗水浸濕了衣服,緊貼著后背,粘稠和癢痛,像是將太陽射下的陽光背在背上。我也無法體會,扶貧路上的饑寒熬煮,他站在斜坡上,手支著大腿眺望,山的那邊還是山,一個個星點小村是藏在樹葉下的菌子,那一刻他是否想起遠方的故鄉和親人。當然,我也無法明白,與知識少、私心重的建檔立卡戶講解國家政策的艱難,不患寡而患不均,人人心里一桿秤,都只是稱自己的生活。我無法虛構同事木呷在扶貧駐村生活里的真實。水冷或者燙,只能自己嘗。但我知道,這其間一定會有心酸、疲憊、孤獨和困頓。世界并不是一個傾聽者,有時候,就連超人,也都需要一個電話亭。凡夫俗子的歲月靜好,不過是有人替你負重前行。
但平凡的世界,總有平凡的人生讓我們感動。路遙的《平凡的世界》里有一句話讓我一直記得:“什么是人生?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奮斗!只有選定了目標并在奮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沒有虛擲,這樣的生活才是充實的,精神也會永遠年輕!”當我的同事木呷出現在中央電視臺的新聞里,我為他欣喜,一顆努力發光發熱的星星穿過光年射來的光,終于被人看見了。被看見讓人欣喜,這是對奮斗人生的肯定,但更值得人自豪、肅然起敬的是這顆星孜孜不倦、默默無聞地朝著目標奮斗。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星光照見的一瞬,是他堅持不舍的一生寫照。
我像其他同事、朋友、親人一樣,贊嘆他的精神,祝賀他取得的成績,卻也在心里深藏著迷惑:木呷在想什么,怎樣想,是什么樣的內核決定著他的言行,是什么樣的力量推動著他一路前行?《當你像鳥飛往你的群山》里我記下一句話:“決定你是誰的最大因素來自你的內心。”木呷的內心藏著怎樣的核能,或者說,他有著一顆怎樣的初心,讓他成為了一個讓人親近又敬佩的人?
我們成為我們所期待的人。我相信,木呷一直在努力著,他秉持著一種信念,堅守著一顆初心,這顆初心蘊含著無限的力量,推著他向著期待中的自己努力。什么樣的形象會是木呷期待中的自己呢?我想,在內心最深處、最深沉的渴望里,木呷希望自己成為一名優秀的共產黨員。是的,這就是他的初心,成為一名優秀的共產黨員。在他入黨宣誓、高舉右拳、聲如洪鐘時,他已經立下了這個目標,他跋山涉水、脫貧攻堅的路,就是通往自己的路、通往“黨員木呷”的路。
2020年5月14日,市文聯全體人員在黨組書記魯若迪基、副主席陳洪金帶隊下,去往春東村開展一月一次的扶貧自查工作。木呷又一次踏上了那條他熟悉的山路,翠玉、牦牛廠、羊腸箐、東坡甸、勝利村……數不清他是第幾次、幾十次走在這條路上了。一路上杜鵑花開得燦爛,漫山遍野的幸福花讓風聲也變成杜鵑的啼鳴。在羊腸箐一棵開滿白花的樹前,我們停了下來。木呷說,一個月前,攝制組和他在這里拍攝新聞,四月間,卻大雪漫天。木呷靜靜地看著那一樹白花,時光飛逝似曾相識的恍惚,讓他沉默不語。從一地白雪到滿樹春花,木呷走過的不只是冬春,不只是蒼茫大地十萬大山。那棵樹是他初心的見證者,也是他心路的參照物,他一路走著,走過山河的冬夏、草木的春秋,走過建檔立卡戶脫貧的生活點滴,走過寧蒗大地的巨變和自己的蛻變。現在,我走在他熟悉的路上,遇見了黨員木呷,也將遇見奮斗人生中的每一個他。
詩人木呷
占卜
羊丟了
外公找來一截樹枝
用刀一邊刻
一邊念念有詞
刻出的樹皮
很像許多只耳朵
那只羊從樹下走過
應該能聽見
我最初認識的木呷是位詩人,《占卜》是他寫下的詩。2016年,我一度處在灼心而漫長的等待中,憂慮地猜測著前途命運,像只驚弓之鳥,總是防備著某些看不見的意外。那時我將從學校調動到文聯雜志社工作,事業單位人員的身份和教師出身的緣故,讓我在命運的轉口、好運垂臨時顯得謹小慎微、患得患失。等待讓人煎熬,但日子如同奔跑的斑馬,黑白交替,不舍晝夜。一邊等待,我開始一邊接觸雜志編輯的工作,有時候,需要到文聯去辦理一些事務。某一天到文聯,未來的同事們告訴我,從寧蒗選調的新同事因為是公務員身份,調動手續辦理相對較快,已經到單位上班了。因為調到文聯的人都要求能編會寫,所以,在我悄聲詢問他名字的讀音、知道他叫吉克木呷前,我已經知道他是一個詩人、小涼山詩人。
王小妮說:所有的詩人都是預先認識的。在我開始寫散文之前,我有十年的寫詩經歷。在原先的學校,同事們都戲稱我為:“詩人”,我也一度迷失其間,“端”著自己的詩人身份,讓自己的言行都接近于一首移動的詩。只是后來因為寫詩的天賦所限、閱歷淺顯,斷言碎語只能達到浮光掠影的膚淺層次,就像陽光只到達河水表面那樣,于是我放棄了詩歌,或者說是詩歌放棄了我,我開始寫散文,自稱“散人”,一個世俗氣息濃烈、總是緊張兮兮毫不松散的散人。
在內心深處,我與木呷是有一些“我自以為”的詩人間相惜和敬意的。詩人是我們隱秘的身份,潛伏在光陰與天地之間,為山川湖泊抒情,為星辰大海守秘。
以文會友,在沒有和他有深入了解的交流前,我開始從他的詩歌的字里行間尋找高山流水的蛛絲馬跡。2016年,市文聯與《邊疆文學》接洽,在《邊疆文學》推出“麗江青年作品小輯”,那是我第一次上省級刊物,也是在那一期上,我讀到了木呷的詩。之后斷斷續續讀到木呷的詩,在《民族文學》《西藏文學》里,驚喜之余,我開始悄悄用他詩歌的詞義和詩情粘貼木呷的詩人身份。
我很喜歡木呷的詩,他的詩,像他這個人,他的詩樸素,語言自然簡潔,意義曉暢而內斂,開闊的視野下常常把目光和真情傾注在柔軟的細節上,而在他詩歌的結尾,又常常藏著小小的撬動,能讓你隨著蚌心里的沙粒,一起疼痛,又一起驚喜。木呷心有萬物,所以,萬物充滿了他的靈魂,在詩中浮現,平凡普通卻閃著光芒。
初見的木呷,他靦腆、內斂,說話的聲音很輕,說話時帶著微笑。就是這樣一個人,他的詩卻是他心靈的密碼,一個個落到白紙上的黑字,像黑夜里回家,不自覺唱起的明亮、悠揚的鄉謠。木呷的心事藏得很深。
今天在派出所
看到一位彝族老媽媽
正在辦二代身份證
采集指紋時
機器卻怎么也讀不出
她的指紋
看著她長滿老繭的手
粗糙如樹皮
我的心里一酸
想起了遠在老家的母親
我猜啊
能讀出她們指紋的
也只有家里那一畝三分地了
許多影子在木呷詩歌里晃動,只言片語間,白紙上黑色的抒情,慰藉他客居的鄉情。公雞、羊;洋芋、苦蕎;吸煙的房子、彝人的火塘;畢摩,族譜,一個紙上的故鄉被臨摹而出,山川萬物在擬人和隱喻間,漸漸升騰到他精神的高原。在他精神的高原,有故鄉、有云貴,更有中國。今年初在與新冠疫情的戰斗中,木呷帶著隊員挨家挨戶進行排查,當一天緊張的工作結束,他依然走在戰“疫”的路上,那時的他是“詩人木呷”。心懷著詩人的悲憫和責任,他寫下了《戴著白色口罩的月亮守住了村莊》:
1
一到晚上
月亮總是戴著白色的口罩
出現在我們上頭
2
夜色在山巒間
不斷傳染
輕輕地思念一遍
就無法隔離了
3
月光有毒
天上的星星太多太近
即使兩三顆落下來
也被我們排查成
萬家燈火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一個詩人,可以細微到收存毫毛,也可以廣闊到容納十方宇宙,雖然我們無法達到“為天地立心”的境界,但詩言志,如果說故鄉與遠方是一個詩人的柔情和靈魂,那么責任與擔當便是他的骨氣和血性,是不可少、不可缺的。在詩人木呷的詩里,我讀到了他的柔情,猜出他的心事,也讀到了血和骨,讀到了一顆紅彤彤的詩心。我曾寫過一首名叫《謄抄一位詩人》的拙劣的詩,現在,請允許我矯情地做出應和,應和木呷那些樸素深情的歌,我要謄抄木呷的詩,也要謄抄這位叫“吉克木呷”的詩人——
清水凈手,我將謄抄一位詩人
于懸崖尋風蘸血寫就的詩。黑字
如淵,一張白紙升起他夢見的故鄉
他將生命平鋪。連同突起的怒低陷的憂
都戴上詩歌的謎面,跳躍在
意象與隱喻間,結局或開始處
我在暗處,橫折彎鉤隱去身形
跟蹤他的停頓轉折,控制腳步輕重緩急
飛奔山重坐看水盡,看他星火引發海嘯
在熟悉漢字澆鑄出的驚喜和感動間
他追尋的是心緒還是天意
我和我的敬意誰先到他夢里天堂之門
他的天堂萌芽于原始蒼茫,一日將盡
我屏住呼吸,在黃昏登上他精神的高原
與他的孤獨并立,等待夢中盛宴降臨
同事木呷
2017年初,我的調令終于批下來了,當我正式到文聯上班時,木呷已經下鄉駐村扶貧快半年了。所以,我和木呷的同事關系,是形而上的,是一種朋友圈的同事關系。我是他的“點贊之交”。我經常在朋友圈看到木呷走村串戶留下的照片,照片略去了長路和冷汗、高山和烈日,只留下和建檔立卡戶溝通的場景,寥寥數語做備注,如同警句,鏗鏘有力。
“催建房,拆舊房,硬化路。”“廁所革命宣傳。”“市文聯幫扶干部走訪扶貧戶。”“人居環境提升工作。”“決勝脫貧攻堅掛牌督戰推進會。”“東坡甸學校動工。”“愛心超市籌備。”
我所看到的,不過是扶貧生活的萬分之一,也無法穿過圖片和文字觸摸到扶貧工作的艱難困苦和任重道遠。不痛不癢的“點贊”只能遙寄我微不足道的敬意,木呷所做的事情,是在為高天厚地和時代春秋“點贊”,每一個腳印、每一句話、每一次幫扶,都在“心”里,都是將“心”點紅。
與木呷的近距離相處,大多是在我們去春東村走訪扶貧戶的時候。木呷中等身材。在我印象中,他的衣著固定、保守——黑色帽子、深色夾克西褲、黑皮鞋。我幾乎沒有見過他穿色彩鮮亮、款式新潮的衣服,想來扶貧路上風塵泥淖,深色衣褲耐臟耐揉,又不失穩重踏實。鴨舌帽下,是木呷端正清秀的五官。他笑起來的時候,牙齒潔白,眼鏡后的眼睛會瞇成一線。
在和我們一起走訪扶貧戶的路上,他會將你所負責的掛聯戶的近況以及未來發展的動向告訴你,事無巨細。他無數次走在這條路上,進村入戶,開展工作。春夏秋冬,陰晴雨雪,這些彎曲陡峭的路,像是他的年輪,一圈圈繞著他的心。原始蒼茫,山遙水長,這條路是他回家的路,但又不是他回家的路。此心安處是吾鄉,或許木呷已經將扶貧的這方天地當成了故鄉,所以他的神情總是沉靜、恬淡而知足,國事也就是家事,扶貧其實是扶自己的親人。
不多的閑談間,我得知木呷是四川涼山州喜德縣人,2002年中專畢業后,就到寧蒗縣工作。他從基層的電視新聞編輯、記者以及彝文翻譯編輯工作做起,任過寧蒗縣廣播電視臺臺長,后又參加公務員考試,在新營盤鄉人民政府辦公室工作,他調動到市文聯前,任寧蒗縣文化體育廣電新聞出版局副局長。18年來,他的工作有升職、有調動,但他一直在寧蒗的土地工作,播撒光熱。
寧蒗的山川,屬于小涼山,而木呷的家鄉,在大涼山。我問木呷,是否時常回去。他說,以前一年回去一兩次,現在扶貧工作忙,已經很久沒有回故鄉了。我繼續問,你家鄉那邊也在扶貧吧?他笑著說,是啊,扶貧后家鄉變化很大。我很喜歡“涼山”這個詞,雖然“涼”,但卻是一種可感、可觸、可親的溫度,讓山也有了煙火氣和人間味。涼山有大有小,像兩兄弟,中間圍著清澈可人的瀘沽湖,那是他們的妹妹,掌上明珠、心上佳人。我想,是不是這里所有的山,都將溫度寄給了天上的云和湖中的水,才讓云朵舒卷自在,才讓水波起伏悠然,也才讓那些云下水旁的人,有一腔激蕩的熱血?
木呷溫文爾雅的書卷氣下,有一股奔流的熱血,他的愛深沉、飽滿,所以,他腳下的涼山,不管大還是小,對于他來說,都是熱土。大小涼山,是他連成一片的故鄉。
四月走訪扶貧戶的工作結束了,同事們就要回麗江城。木呷等著給我們送行。我看著遠山,尋找著詩人魯若迪基家的斯布炯神山。木呷的深色背影就在我前面,市文聯副主席陳洪金和木呷說著話,叮囑他繼續做好工作,同時也要照顧好自己。這時候,魯若迪基的弟妹也走出來送行,她看著我們正收東西,就親熱地和木呷開起了玩笑:木呷,你同事們要走了,你一個人留在這,待會不要哭啊。我感覺木呷的背影顫了一下、縮了一下,某種情緒像刺猬遇險,將柔軟的肚腹收往內里深處。這是我的捕風捉影,我無法透過背影看到他內心的激蕩,而木呷、我的同事,只是輕笑了兩聲,云淡風輕,不露心事。
彝人木呷
九十年代,我讀小學時,有段時間很流行“山鷹組合”“彝人制造”的歌。有同學會請你把歌詞抄到歌本上。那時候寫的字,當然很丑,但膽子大,能面不改自戀之色地將歌詞抄完,表情得意,情緒微醺。后來聽到“太陽部落”“吉克雋逸”的歌,那些帶著音律的意象,在我腦海中搭建了彝人的故鄉。那是很美的地方,在山頂,白天開滿了索瑪花,夜晚開滿了紅火把,羊群在云朵間捉迷藏。蕎麥翠綠,零星開著細碎的小白花。木楞房建在向陽的山坡上,房里的火塘燃得正歡,茶罐里的水唱著低音,應和著阿媽的歌謠……
2017年11月,我第一次下鄉到寧蒗縣翠玉鄉春東村那晚,在詩人魯若迪基家的火塘邊見到了他的“1958年的父親”。那晚木呷坐在我旁邊,精致的龍紋酒碗放在地上。酒碗內里是明亮的鮮黃色,端到火光照不到的暗處,像黑夜里的黃月亮,不知道,那醉人的月光是否是天界神明注滿的美酒。
翠玉鄉多是普米族,也有彝族和漢族,魯若迪基在當地很有威望,知道他回來,很多人來看他,人們圍坐在火塘邊,相互敬酒。我發現,來敬酒的普米漢子們都不像我這樣叫木呷的名字,他們端起酒碗,邁步過來,沖著木呷喊:“吉克”。
“吉克”,是木呷家族的名字。
家族之名,門庭的榮耀,血脈的印章。一個人行走在天地間,接過祖先傳下的姓氏,被命名,才有生。家族的姓氏如同徽章,一筆一筆雕刻著過往的歲月、凝固的歷史、靜默的家神和流動的血脈。家族的姓氏是我們的堡壘、坐騎和后盾,是不能被辱沒的。在敬酒的呼喊中,我能聽出語氣中的敬意——家族的姓氏,是你的名字,你的前行,背負著一個家族的尊嚴。但這種敬意并非來自血統。那些普米族漢子,有著自己的生場與血地、鬼怪和神明,他們是另一條河,不會在乎你的河水源頭是否來自雪山之巔。但他們確實是帶著敬意和親切去稱呼彝人木呷的:“吉克,來,喝酒。”
決定我們的不是記憶、血脈、家勢,而是行為。木呷身上帶著他的大涼山、家族和故鄉,將自己深沉的愛澆筑在異鄉。他甚至比一個土生土長的當地人還了解這片天地,他去過許多當地人都沒有到過的村子,倉巖洞、青稞坪、衙門坪、罐罐山、白草坪、老屋基,這些早已異地搬遷的“空殼村”,木呷走到過;貧困戶建房、人居提升、產業驗收、合作社覆蓋、檔案完善,這些關系到當地老百姓生活的細節,木呷努力做著;下雨了、進村的路斷了、建房子的材料拉不了、老百姓莊稼收不了,木呷憂心著。行為決定了你的人格,有句老話說: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果說肉身即是故鄉、我們是各自家族的骨頭,那么,彝人木呷就是吉克家族的一塊硬骨頭。
“小涼山很小/只有我的拇指那么大/在外的時候/我總是把它豎在別人的眼前”。我想,在木呷心里,大涼山很小,彝族很小,吉克家族很小,那個叫“躍進”的小村很小,他那么努力,是為了把它們豎在別人面前。
某天在朋友圈里看到一則新聞:“2019年云南吉克家族獎學金頒獎暨募捐儀式舉行”。點進文章看熱鬧,發現是云南吉克家族為71 名品學兼優的學生發放獎學金,不由地心下贊嘆。“云南吉克家族獎學金”到今年已經是第四次了。后來我跟木呷閑聊到此事,表示欽佩,他才說起,吉克家族獎學金是他和家族的一個企業家共同發起的,由家族共同捐款資助家族中優秀學子的一項民間助學活動,一年舉行一次。木呷深藏功與名。
文章下有許多留言,讀來充滿能量,很是感動:“真的很高興能生在這么重視教育,愛國,守法的畢摩家族,再次看到我們家族為這次云南省吉克家族獎學金儀式舉行默默付出的所有人員,在這里向你說一聲辛苦了!”
“我們四川的吉克向云南學習。”
“彝族同胞的教育理念大大轉變,給你們點贊!有了這樣的儀式不僅增加了孩子們的學習興趣還培養了更多的人才!”
“一個家族的家風真的很重要,作為吉克子女,我希望我們年輕人繼承先輩重視教育的家風,學知識,長見識,開眼界,愛國,愛族,愛家。偉人說過,落后就要挨打,我希望我們家族乃至整個民族改變觀念,與時俱進,跟上日新月異的時代潮流。”
“書則(彝語:厲害),我們大涼山吉克家應該向云南吉克家學習。”
我想,這是一個家族的自愛自尊。如果你想把你的家族豎在別人的眼前,也想讓別人把你的家族豎在你的眼前,那么,首先,你得自己先站起來,穩穩地站在大地上。
書記木呷
電話響了。
寧蒗縣春東村委會第一書記、工作隊長吉克木呷將視線從電腦上移開,扒開辦公桌上堆積的表格,手忙腳亂地找著手機。相同的鈴聲但不是來自木呷的手機。旁邊同事接通了電話。終于木呷也在散亂的A4 紙下找到了手機,他把屏幕按亮,看了一眼,沒有未接來電。做了一早上的材料,建檔立卡戶的檔案完善、“明白卡”的內容核對,讓木呷頭暈眼花。順勢休息一下吧。木呷點開通話記錄,上下劃著,然后關掉,又點開,又關掉。今天手機出奇地安靜。要在平時,電話多得恨不得手機就長在耳朵上。中午還要開會,“拆舊復墾復綠”工作得提前準備,得安排一下遍訪的工作。手上的工作先放一放,先準備中午開會的內容吧,這一次“伙頭”“排方”“龍塘”這幾個村得加強動態管理。
中午開會布置工作的時候,木呷感覺手機在兜里震動,抽出手和眼,拿出電話看了一眼:沒有來電。手機是調成靜音的。木呷劃下手機窗口,把手機調成震動,放在桌上,免得整天疑神疑鬼的。副書記楊紹海補充發言時,手機真的響了,木呷的心顫了一下,拿起手機看屏幕,是市文聯的同事打來的。木呷起身到門外接電話,同事來電話是詢問扶貧戶就讀子女的普通高中補助政策的細節。掛了電話,木呷心里空空的。打起精神,下午還得入戶督促危房改造問題。
這些是日常,一個駐村第一書記的日常,也是一個扶貧工作隊員的日常。一切都圍繞著扶貧工作展開,貧困戶建房、人居提升、危房改造、產業驗收、合作社覆蓋、兩后生勸學、勞動力轉移培訓、檔案完善、明白卡上墻……每一項工作都得狠抓細抓,時間緊,任務重,有時候甚至都沒有時間停下來關照一下自己的內心,但作為第一書記,又不能讓工作隊員們看到自己的沉重,怕影響軍心。有時候,真想把自己變成一臺沒有感情的機器,但那是奇思妙想,扶貧,其實是扶人,要把國家的扶貧政策,化入老百姓的生活中,不能死搬硬套,要有煙火氣和人情味,那不是沒有感情的機器能做的事情,甚至,扶貧隊員開展工作,如果對扶貧戶沒有感情,那這工作也是做不好、收不到效果的。扶貧工作需要愛,需要大愛,一些小情緒,得自己調整好。
向信用社借了車,木呷和隊員們又奔波在熟悉的路上。一路上,手機一反早上的安靜,響個不停。先是一個未知號碼來電,接通了,是一個春東村村民打來的。村民激動地說,干兒子,我在電視上看到你了,沒想到你連晚上做夢都是有關扶貧工作的事,你們扶貧干部辛苦啦,我們會記在心里的。木呷被激動的村民弄得笑出了聲,后又被村民幾句話弄得眼睛濕潤,掛了電話后又有些誠惶誠恐,扶貧是他的本職工作,是他該做好的事情,這樣一宣傳,反倒讓自己生出腳觸不到地的虛妄感。
隨后是工作隊的女同事打來電話,接通電話,是唱歌一樣的永勝口音:“木呷書記……”她詢問的是關于“明白卡”制作事宜。
到牦牛廠村入戶,快走完的時候,市文聯書記打來電話,說要說三件事情。一件事是詢問前往勝利村的路是否通暢,單位開始做這個月的下鄉準備了,但雨季車路通暢是大問題,所以先問清楚,好靈活機動地安排工作。二是春東村“愛心超市”的事情,市文聯在春東村籌建的“愛心超市”是全市范圍內最早建好的,應該盡快投入使用,把工作做在前頭,盡快讓群眾受惠,調動起村民的積極性。
掛了電話,木呷才想起書記原本要說三件事的,但只說了兩件。木呷感覺今天書記說話欲言又止的,大概是要落實一些扶貧工作的具體細節,需要深思熟慮,說話才有些吞吐。木呷沒想太多,心思又回到“路”上來。這兩年,翠玉鄉春東村已經基本上實現了道路硬化,去往勝利村和光明村的路也打好基礎,相信很快就有通暢的水泥路,到時候,運送建房的水泥等材料就會方便。以前扶貧戶買來水泥,山路因下雨無法通行,雨水淋到水泥上,水泥就廢了。建房的扶貧戶很愁,工作隊員也很愁,無端增加了建房成本,好好的水泥變成石頭,扶貧戶的無助,這讓人心疼。以后路通了,村里的優質花椒、核桃往外運送就方便了。扶貧路何時才能成為致富路呢?一路上木呷都在想這個問題。他時不時拿出電話看看,這些天總是有錯覺,覺得有電話打進來。
回到翠玉后,吃過晚飯,已經是晚上七點了。雖然有些累,但木呷還是讓自己加了三小時的班,繼續完善建檔立卡戶“明白卡”的資料。回到住處,十點過,木呷躺在床上不想動彈。一旦手頭無事、安靜下來,木呷又生出有電話打入的錯覺。他拿起電話,點進通話記錄,上下劃動。當一個熟悉的號碼跳進眼簾時,木呷突然想起,已經有好幾天沒給妻子和兒子木果打電話了。木呷按下電話,看到屏幕上方時間顯示是22 點34 分鐘,旋即又掛掉電話。這么晚了,家人怕是休息了。木呷想起在麗江的家,想起遠在四川的故鄉,一時間千頭萬緒,這一整天患得患失的情緒,原來就是來自這兩個沒有撥通的電話。木呷又一次撥通了妻子的電話,停了兩三秒,又馬上掛掉。今天文聯書記打來電話沒說完,是不是就是要和他說這件事情呢?這件事木呷沒和妻子說過,但夫妻這么多年,這些天他又不敢往家里打電話,妻子也不打電話來,怕是已經猜出事情的大概了。
木呷深吸了一口氣,又緩緩呼出。今年是脫貧攻堅的決勝年,十分關鍵。寧蒗縣的扶貧工作是麗江市扶貧工作的重點,而春東村又是寧蒗扶貧的重點之一。寧蒗縣委領導多次來到翠玉,去到春東村指導工作,對現階段春東的扶貧工作給予了高度肯定,希望工作隊能夠擼起袖子,鼓足干勁,順利實現春東村脫貧出列的目標。木呷也對此充滿信心。但是,到今年,已經是他到春東村扶貧、做第一書記的第四年了。原本下鄉駐村一年后,就可以回原單位的,但是,木呷放不下啊。就這樣堅持著,第二年,第三年,他一直在扶貧路上奮斗。不知道兒子木果心里,是否期待著自己的父親能夠出現在自己校門口,拉著自己走在放學回家的路上。這些年,兒子木果從幼兒園讀到了小學,家庭的重擔也一直壓在妻子身上。木呷也希望能夠陪在親人身邊,可是,作為春東村第一書記、工作隊長,扶貧的重擔扛在肩上,是不能說放就放的。假如換一個書記、隊長,新書記需要時間熟悉工作,短時間內不可能像他這樣熟悉,這樣勢必會影響春東村脫貧的進度和質量。一顆釘子決定一場戰爭,這個時候不能有絲毫的松懈,木呷已經決定站好最后一班崗,2020年也堅守在扶貧書記的崗位上。他已經將自己的決定報告了寧蒗縣委領導和市文聯書記,但他沒有告訴家人,他不知道怎么開口……
窗外,雨又開始下了。
親人木呷
在春東村很少有人叫他——“木呷”,年齡大一點的叫他“干兒子”,更多人喜歡叫他“木呷兄弟”。無論是叫“干兒子”還是“兄弟”,其實都意味著老百姓把木呷當做親人、親人木呷。在我的金沙江邊的老家,有一句非常喜人的方言:“人親骨頭香。”我可以預見到,每當木呷走進扶貧戶家里,那些沒有血緣、但情濃于血的親人,會帶著微笑迎接他。扶貧戶臉上的微笑是來自內心的。親人們會被一種親切感擁抱著,這種親切感帶著香氣,如花氣、似草香,天然而純真。這香氣,應該就是來自骨頭里的。相見時的喜悅、激動,相處時的愉快、親近,離別時的感激、不舍,魚水情深,星月相照,骨肉相連。春東村村民楊建花說:因為他(木呷)
對我們太好了,他變成我們的親人了。
親人間總有些牽掛,牽掛就會織出許多故事。關于木呷和他的親人們的故事,我聽過很多,比如“熊采獨瑪的白房子”,比如“李衣生母的獎狀”。
“白房子”。這是熊采獨瑪對自己的新房子的稱呼,當我聽到這個詞時,內心欣喜地贊嘆人們的創造力:語言在生活里才如魚得水,才是最鮮活的。我到過熊采獨瑪在勝利村的家,房子是傳統的普米族木楞房,房頂灰黑,木楞粗糲,屋內昏暗,卻漏著風。房檐下雜亂、參差地晾曬著衣物。院子內老母雞帶著一群剛孵出不久的毛絨小雞仔四處啄食,老母雞傲嬌,小雞仔慌張。豬牛關在正房的下層,我能聞到一股豬牛糞便和濕草被捂悶過的混雜氣味。
木楞房里裝存著漏風滴雨的冷色生活。木呷入戶調查后,識別出符合條件的十七戶貧困戶,熊采獨瑪家就是其中的一戶。納入建檔立卡貧困戶后,熊采獨瑪家享受到一系列精準扶貧政策,搬離了原來居住的勝利村,做起了小生意,蓋起了新房。我到過她在翠玉的新家,是現在常見的鋼筋水泥房,相較于木楞房里的生活,現在,熊采獨瑪像是住在一個夢里,她說,感謝他們,要不是他們,住不上這樣的“白房子”。我不知道她是否會在白房子的夢中做夢,夢到自己的老房子,夢境里出現一段獨白,帶著陽光,說著心聲:
“即使是藍天白云、和風暖陽的好天氣,也無法將老去的木楞房從昏沉的夢中喚醒。木楞房的膚色漸漸回歸泥土,他確實是老了,回憶和昏睡占去了他大部分的時間,我望向他,虛掩的門,眼瞼沉重。像斑駁的灰發,經風歷雨的屋瓦上流過太多的晝夜和秋冬。木楞層疊,皺紋里藏著太多風聲和故事,那些故事和火塘的柴火一起發出光熱,讓童年的睡夢溫暖。我想念在木楞房里度過的時光,但我更喜歡新房子帶給我的憧憬和希望。木楞房對面,貼著白色瓷磚的新房子艷麗、明亮、寬敞,一朵朵向陽的花,開在院子里,開在窗戶、門簾和我的臉上。屋頂的水泥是另一種石頭,融在一起的石頭,我信賴石頭,它沉默、沉重,它幫我壓著我的新房子,我害怕大風把我家的新房子吹到天上去。我太喜歡我家的新房子了。”
木呷在李衣生母家客廳的墻上看到一排獎狀。之所以會注意到這個細節,我想,大概是因為木呷想起自己正在讀書的兒子。或許曾經有一天,木呷的兒子通過電話視頻向木呷展示自己剛得到的獎狀,帶著驕傲和羞澀,急切而激動的和遠在寧蒗扶貧的父親分享自己的喜悅。扶貧和學習一樣,需要努力奮斗才能得到一些成績。但木呷沒想到的是,成績優異的李衣生母居然輟學了,并且是在高考前兩個月。那時是2019年4月,開展戶戶清工作,木呷來到李衣生母家入戶調查,奇怪地發現,為什么成績那么好的學生1月份就輟學外出務工了?
原因其實不言自明:因為貧困。
木呷或許沒有意識到,當時的他處在一個兩難的境地。作為第一書記、扶貧隊長,自然是希望自己負責的貧困戶全部脫貧。有很多貧困戶致貧的原因是:“因學致貧”,李衣生母選擇輟學,為家庭減輕負擔,并且早日去務工,也能給家庭帶來一些經濟收入,能順利脫貧,也能讓弟弟繼續求學。但木呷并沒有這樣考慮,他沒有因為要讓一個家庭脫貧而選擇對一個好學生的命運置之不理。木呷馬上打電話給李衣生母的父親,讓她父親告訴李衣生母,說扶貧工作隊讓她必須回來參加高考。
高考是人生一個埡口,不參加高考,不讀大學,不繼續學習知識,那這個學生,可能一生都在和貧困斗爭。參加高考,她的人生會因此和父輩不同,就會有更多可能性和希望。高考前一個月,李衣生母回到學校,考上了大學,她說,高考是人生的一個轉折點,而遇到木呷、得到幫助是她人生的另個一個轉折點。
或許是因為那張獎狀,或許是因為想到兒子,或許是因為木呷想到了從前的自己,曾經有那么一刻,或許木呷也面臨輟學的處境,所以他知道需要有人站出來支持李衣生母、幫助李衣生母,這只是一個小小的幫扶,但對李衣生母,卻意義重大。我知道木呷還有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在他的學生時代,求學的渴望和家庭的困難是兩只矛,都頂著木呷的脊背。但他堅持了下來,他的親人也堅持讓他和弟妹讀書。后來,木呷畢業來到麗江工作、成家,而家鄉的弟弟妹妹都當了老師。知識能改變命運,讀書,在木呷看來是改變人生的一條路。扶貧,不僅僅給人富裕,還應該給人希望。這是最高級的給予和幫扶。比你更關心你自己的,是你的親人。
父親木呷
讀小學的木果在造句。
老師安排家庭作業——寫生字“嗎”“怎么”,然后造句。木果左手抱頭,咬著鉛筆,絞盡腦汁,但大腦一片空白。他懊惱地直起身子,靠在椅子上,看向窗外,隨后,看向書桌,目光呆直:太難了。房間很安靜,只有書桌上的鬧鐘發出“沙沙”的聲音,木果想看看時間,他覺得時間漫長得快過了一百年。突然,木果看到了他們一家人的合影,一下就知道自己要寫什么了。木果用歪斜、稚嫩的筆跡順暢、快速地寫下句子,這句子幾乎沒有讓他費神,因為他寫的是他這個孩童對世界的大大疑惑和小小心事。他寫下:“爸爸怎么天天去山上?”“爸爸你現在走嗎?”
這是讓人心顫的句子,也是讓人心疼的句子。不知道當木果的媽媽為他檢查作業時,有沒有含著眼淚。天真的發問有時候卻最顯滄桑。“天天”“現在走嗎”,世界對于孩童木果,是碩大、籠統而抽象的,他不明真相,無法填充更多可靠的細節,他僅能理解的真實,是他的爸爸沒有陪在他身邊。
爸爸去哪兒?爸爸去“山上”了。木果可能無法精準地理解“精準扶貧”這個詞里包含的艱辛、漫長和重大,與無法理解父輩們為之奮斗的初心、使命和責任。他無法感受國土上正磅礴展開的激情事件、偉大進程,對于他,能感受到的,是一種小小的稚嫩的委屈。父親不能陪他下國際象棋,不能陪他畫畫,不能給他講故事。父親,像是一個疑問句,木果無法用陳述句、判斷句來“造句”父親,也不能用省略句或是否定句,父親太珍貴了,珍貴得,像是節日。
對于木果,從他出生那一刻,“父親”就因為他而天然地存在著。而對于吉克木呷,他并非生來就是某人的父親。木呷也在“造句”,他造的句,也是關于“父親”、如何成為一名父親。
《請回答1988》中女孩德善因為家里窮,被迫和姐姐一同過生日,向父母哭訴后,她父親對她說:“爸爸媽媽對不住你。爸爸也是第一次當爸爸,很多事情不知道,請女兒你多體諒。”每次讀到這句話,我都感動得想哭。爸爸也是第一次當爸爸,孩子的心酸和委屈,如同一聲輕喊,卻能夠激起父母內心的雪崩。史鐵生在《我與地壇》里寫他和母親,他說:“兒子的不幸在母親那兒總是要加倍的。”孩子的心酸,是父母的心痛,孩子的委屈,是父母的苦楚。當父親木呷讀到兒子的造句時,心中肯定是五味雜陳、有如刀割的。疼痛讓人成長,木呷也在努力成長為一個父親。他要如何給自己,也給兒子造句,一個關于父親的句子呢?
這個句子里,要有父親和兒子、我和你,要有愛和思念,要有陪伴和離別,要有兩個人的心心相印,也要有體諒、包容和期待。更重要的是,“父親”這一道題的答案里,木呷要身體力行地填寫下男兒的責任、堅定的目標和崇高的意義,這是父親的意義,將廣闊的世界、高遠生活的版圖和精神,融入到父親的形象里,像一張地圖,讓兒子按圖索驥。哪怕有時父親留下的只是一道背影、一句尋常話語,但在某個時刻,卻能在兒子心里小小地撬動一下,讓他明白平凡世界的道路,讓他明白奮斗人生的意義。
如果要以“精準扶貧”這個詞來造句,你會寫下什么?我們都知道,“扶貧”造的句子會很長,因為這個時代的人們正在大地上“造夢”、一場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中國夢”。無數的人在努力著,為中國夢添磚加瓦,澆筑心血。這是一個時代的造句,這是無數人的造句,木果造下的句子是中國夢的一小部分,木呷造下的句,也是其中的一個部分。雖然有分別和苦痛,但總有一天,當木果明白自己的父親為之奮斗的扶貧事業意義重大而深遠,我想,他會在自己關于“父親”的造句里,在結尾處,寫下一排入紙三分的感嘆號。
凡人木呷
每一個人都是平凡人,包括木呷,包括你和我,但平凡的人們總給我們最多感動,平凡世界里有真心英雄。
2020年5月6日,中央電視臺13 頻道“新聞直播間”欄目中,介紹吉克木呷扶貧事跡的新聞的最后,木呷的妻子出現在畫面里,她說了這樣一段話:“我身邊也有很多這種扶貧工作隊的朋友,其實他們跟他(木呷)一樣的,也是很長時間回不了家。并不是說他(木呷)有多特殊,在這個群體里面,他就是普普通通的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