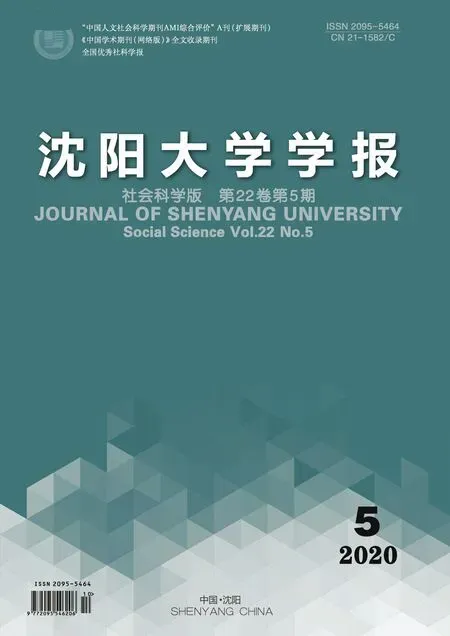遼寧各民族民間文藝互鑒互補發展之路
----基于文化場域理論的探析
齊海英, 周 菁, 魏 佳
(沈陽大學 文法學院, 遼寧 沈陽 110041)
遼寧是一個多民族和諧共存的省份。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各民族廣大民眾創造了豐富多彩的、自身民族特色鮮明的民間文學藝術。這些民間文學藝術資源既為廣大民眾帶來美好的精神享受,同時也成為遼寧地域文化的重要構成因素。但隨著時代和社會的發展,這些躍動于民眾耳目口唇之際的鮮活藝術資源卻漸趨式微。如何使這些寶貴的民間藝術資源地煥發藝術生命力,重新投入到當代遼寧文化建設中來,成為值得思考并著力解決的重要課題。解決問題需要廣開思路,以達成破解問題的多元合力。遼寧各民族民間文藝歷史地共存于同一文化場域,或曰同一宏觀化的民俗文化圈中,形成了同異藝術因素共時在場的關聯和互動關系。對此問題的深入思考和探討對遼寧地域民族文化的發展和建設有一定的助益作用。基于此種考慮,擬以文化場域理論為透視視角,針對遼寧各民族民間文藝跨民族互鑒互補發展問題提出一些可資借鑒的思路和策略。
一、 關于場域及文化場域理論
皮埃爾·布迪厄是法國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社會學大師,場域理論在其社會學思想體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場域理論是關于人類行為的一種概念模式。布迪厄認為,將一個場域定義為位置間客觀關系的網絡或一個形構,這些位置是經過客觀限定的[1]。從此定義可以看出,布迪厄所理解的“場域”并非有具象化的邊際或邊界,而是呈現為某種客觀的網絡結構的建構。在此場域的組構要素中,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人與人的社會關系、人的價值觀、生活方式等,都是構成這一社區網絡結構的因子和因素,這些因子和因素在此社區結構網絡中在場的狀態并非靜止不動,而是呈現著相互牽扯、纏繞,變動不居的運動發展狀態,形成一種內蘊豐富,具有吸附力的人類精神化的生存場域。為易于把握場域概念,布迪厄提出“資本”這一概念,他所說的資本并非經濟領域的概念,而是指一種社會資源。這種資源是由勞動積累起來的,具有排他性和歷史繼承性[2]56。
由此可以看出,他所強調的“場域”構成要素主要是指社區中人與人之間復雜多元,且存在密切聯動或互動的人際關系,這種關系構成精神化的網絡形態,這標志著“場域”的形成和存在。但問題的實質在于,所謂人與人之間復雜的社會化關系都是受特定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的浸漬和影響而形成的,也就是說,人與人之間外化的社會關系問題的實質內核是文化問題。社會既表現為各種關系的系統,也由各種文化所形構,所以說,人是文化的動物。社會上各種文化交織在一起構成各種場域,成為文化的場域,即文化場域。在文化場域中,布迪厄的資本概念依然存在,只不過這里的“資本”變成了“文化”。因為人受到各種文化、思想、習俗影響,其行為和想法都將通過“文化”付諸實現,走向現實。這個想法走向現實的過程就是文化場域對人產生作用的過程[2]57。
以布迪厄的場域理論為肇端,在一些社會學者的思考和探討中,文化場域理論應運而生。文化場域理論與場域理論并非有本質的區別,只不過更凸顯了場域中相互牽扯的文化要素及其作用。
二、 文化場域與民間文藝
文化場域是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人與人的社會關系、人的價值觀、生活方式等因子和因素構成的社會精神化的網絡結構。初看文化場域定義,似乎與民間文藝不存在密切的關聯,但其實民間文藝是內在于特定社會的整體文化場域中的一種兼具審美性和娛樂性的精神文化現象。之所以如此說,是因為民間文藝作為與廣大民眾生存體驗相伴而生的精神文化形態,既直觀、形象地表現著廣大民眾喜怒哀樂之生存化情感,同時也以素樸而具藝術魅力的形式蘊含著廣大民眾的世界觀、價值觀、生存觀及對民間人際道德倫理關系的情感化評判尺度。
特定社區文化場域所具有的極其厚重的文化背景和內蘊也對該社區口耳相傳的民間文藝具有一種思想內蘊及藝術特質等方面的宏觀性的規約影響作用,使某一地域民間文藝總是具有一些共性的藝術品貌或特色。
民間文藝因其生于民間、長于民間而具有極強的親民性,同時也具有極強的民心、民情感召力。這種精神文化形態在社區文化場域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二者之間存在一定相互依托的關系。
三、 文化場域理論觀照下的遼寧各民族民間文藝互鑒互補發展策略
遼寧是多民族共存的省份,民間文藝較之于其他地域呈現出更加豐富多彩的局面。正是因為帶有東北獨特文化背景的宏觀文化場域的影響,遼寧各民族所創造的民間文藝既有各自的發展途徑,又呈現出交流互融之勢。交流共榮是當今文化之世界性的發展趨勢,遼寧各民族民間文藝之間也應在文化溝通和交流的世界性背景、趨勢下搶占發展先機。本文試圖以文化場域理論為觀照背景,探討遼寧各民族民間文藝互鑒互補發展策略。
1. 各民族民間文藝同異藝術因素的在場
(1) 宏觀化文化場域影響下的共性藝術因素。因共存于同一宏觀化的東北文化場域中,所以遼寧地域各民族雖然各有其獨具民族特色的亞文化場域,但受宏觀化大文化場域影響,作為民間文藝資源中的同類藝術存在著族際互動中的類同或共性因素。如遼寧滿族與蒙古族的民間神話故事大多表現關于人類及部族起源方面的民間記憶,具有各自民族鮮明的民族化歷史印記,但這些民間故事之間也存在著一些趨同的因素。同時,因為滿族與蒙古族文化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與漢民族文化不斷交流和交融,從遼寧滿族和蒙古族流傳的神話故事中,可以看到滿蒙漢三種文化互為影響的痕跡。
流傳于遼寧地域的滿族神話故事《人的來歷》[3]1-3,屬于中國多個民族共有的兄妹婚神話類型。兄妹(姐弟)婚神話母題一般只是表現婚姻和人類起源主題的神話,在世界各地流傳和分布極其廣泛,已成為一個重要的神話母題類型,具有豐富的人類早期文化內蘊。遼寧地域流傳的蒙古族人類創生神話《月中高娃》[4]兼有人類起源和部族起源的雙重敘事內蘊。這兩則神話同屬于“天塌地陷型”的人類再生神話,二者體現了一定的共性演述思路。兩則神話之中所出現的用黃泥或淤泥捏制泥人,然后用口氣或配偶泥人使泥偶獲得生命力,并繁衍出后代的故事情節讓人們想到了中國漢民族傳統的女媧造人的神話。《月中高娃》的后半部分出現了高娃和獵人兩位蒙古始祖人物飛升成仙的情節,而其飛升成仙的經歷、方式與漢民族民間故事流傳的《嫦娥奔月》和《牛郎織女》神話有著一定的關聯和相似性,形成了一種融合性的民間神話故事演繹情境。
從滿族《人的來歷》和蒙古族《月中高娃》等人類創生、民族起源類神話來看, 與漢族的一些遠古神話傳說存在著明顯的類同之處, 三者是否相互影響? 誰影響了誰? 是否有另外的中介性影響因素? 這些是有待進一步深入探討的問題, 但事實本身卻表明, 在遼寧地域共存的滿蒙漢民間神話傳說確實存在著相互影響而形成的共性因素。
再比如風行于東北地區的二人轉, 看似與滿族民間文藝并無關聯, 但據一些文化學者的研究發現,其形成卻與滿族遠古自然宗教----薩滿教的跳神祭祀儀式有著密切的關聯。沒有哪一種藝術能像二人轉那樣呈現著薩滿的身影,沒有哪一種藝術能像二人轉那樣強烈地體現著薩滿精神,也沒有哪一種藝術能像二人轉那樣蘊藉著薩滿的靈魂[5]。如仔細品味二人轉與薩滿祭神儀式可以發現,前者不僅對后者有外在的表演手段方面的吸收,更有內在的激情化、生命化的民間藝術精神方面的轉換性傳承與發揮。
(2) 各民族各自亞文化場域影響下的差異性藝術因素。遼寧各個少數民族在大分散的情況下又有相對集中的生存地域,同一民族在漫長歷史時空中的相對聚居形成了獨具民族特色的亞文化場域,而不同民族亞文化場域之間必然存在著一些文化品質方面的差異。作為民族文化重要構成部分的民間文藝也必然在自身亞文化場域影響下形成一些不同于其他民族民間文藝的特色和品格。
滿族始祖神話傳說具有將始祖崇拜與靈禽崇拜合而為一的敘事特色。流傳于遼東山區的《天鵝仙女》[3]4-8是一則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始祖誕生的神話傳說故事,其中靈禽崇拜的意識較為鮮明。誕下滿族部族始祖布庫里雍順的三仙女佛庫倫和她的兩個姐姐恩固倫、正固倫在整個神話故事的演述中始終處于“鵝”“仙”“人”跨界化的轉換與變異中。“天鵝”可以說是連接三位仙女“天宮”和“凡界”的中介形態,姿態高雅、潔白純凈的天鵝使仙女能夠自由地徜徉往返于人界和仙界,滿族始祖誕生的神圣與神秘藉此獲得了一種張揚。而“額娘”稱呼的演繹更是將“天鵝”靈禽與部族始祖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三個兄弟打獵回來,不見了妻子,只聽孩子說:“鵝,鵝,飛走了!”一找衣服也沒有了,知道三個仙女回天上去了,就對孩子說:“那鵝,就是你們的娘,知道嗎?”
傳說滿族人管母親叫額娘(“鵝”與“額”音同),就是從這兒起的。
《天鵝仙女》中,記述滿族確切的始祖布庫里雍順的誕生過程則又與另一種靈禽喜鵲發生了密切的關聯:
正洗著,三仙女見天邊飛來一只喜鵲,飛到天池上空,將嘴里銜著的東西吐在她的衣服上。她本來已經不想在水中多待了,就游上岸,見衣服上放著一枚熟透了的紅果,大得出奇,紅得透亮,她在山上待過三年,還沒有見過這樣的果子,撿起來含在嘴里,準備穿好衣服等大姐二姐上岸好給她們看。誰知紅果一含進嘴里,“哧溜”一下從嗓子眼滑進肚子里去了。
大姐、二姐穿好衣服要回天上去了,三仙女身子發沉,說什么也飛不起來。大姐,二姐知道她是誤吃紅果懷了孕,勸她不要著急,等生完孩子再來接她,說完后飛走了。
《天鵝仙女》中出現的“天鵝”“喜鵲”等飛禽形象是滿族民眾靈禽崇拜意識的形象呈現,更準確地說,是滿族民眾“天鵝”“喜鵲”崇拜意識的肇端和源頭。正因為“天鵝”“喜鵲”與滿族部族始祖的誕生有著極富神秘色彩的關聯,故而這兩種飛禽便成為了日后廣大滿族民眾歷史記憶深處極富民族情感的崇拜符號。這種崇拜符號里也透露出了“君權神授”這種由漢族傳統文化影響的記憶,同時又與滿族早期信奉的薩滿教有著歷史的淵源和關聯。
再看,遼寧地域蒙古族民間始祖神話則往往具有濃郁的佛教色彩。《月中高娃》將部族始祖的誕生置于一個濃郁的佛教背景和情境中加以記敘和演繹:
據說天上每經過一個劫樂布就得毀滅回爐一次。啥叫毀滅回爐?就是當劫樂布到來這一天,是世界末日,海嘯山崩,天塌地陷,是凡活物全都死光。天下除了汪洋大海,再就是淤泥。鴉雀咕咚,要多寂寞有多寂寞。
煞介土巴佛祖一看,這也太沒意思啦,于是就挖了一塊淤泥,蹲在地上鼓鼓搗搗地捏了八個小泥人。捏成之后,對著八個小泥人吹了一口氣,然后說:
“哈!這回天下又有人啦。你們走吧,到四面八方謀生去吧!天下有的是林木田地,足夠你們過日子用的了。”
說完,煞介土巴佛祖就走了。
蒙古族民眾受佛教思想濡染極深。清朝建立之后,出于統治的需要,統治者在遼寧地域的蒙古族聚集區域以官方的形式進一步強化了佛教思想和意識。遼寧地域的蒙古勒津、喀喇沁等地區修建了大量的藏傳佛教寺廟,蒙古族家庭的世代男丁大部分都走進了寺廟,成為誦經念佛的喇嘛。佛教思想和觀念隨著歷史的推進不斷鞏固和深化,以至于完全滲透和融入于廣大蒙古族民眾的日常生存的各個層面,成為一種心靈化、體驗化、情感化的宗教觀念和意識,也成為遼寧地域蒙古族亞文化場域的一個鮮明特色。
各民族的舞蹈藝術也因各自環境、生計條件及亞文化場域的差異而體現出不同的藝術風貌。如共同生存于宏觀東北文化場域中的滿族、蒙古族與朝鮮族。
滿族主要有腰鈴舞、銅鏡舞、單鼓舞、寸子舞、莽勢舞、秧歌舞等舞蹈形式,其突出藝術特征表現為對大自然的模仿及豪放彪悍的民族個性。蒙古族舞蹈以盅碗舞和筷子舞最為著名,其突出藝術表現特征是肩部、手臂動作豐富,步伐常模仿“馬步”;朝鮮族舞蹈主要形式有農樂舞、扇舞、假面舞等。其舞蹈特色體現為瀟灑、典雅、含蓄、飄逸的舞風,以細膩而又具有跳躍感的12/8拍為主要節拍類型,看似簡單的動作,卻蘊含著高難度的呼吸技巧。
2. 各民族民間文藝互鑒互補發展策略
宏觀文化場域及各民族亞文化場域影響下生成的遼寧地域各民族民間文藝共性,以及差異性的存在恰恰是造就民間文藝豐富多彩形態的原因之一,這也為思考和探尋遼寧各民族民間文藝的互鑒發展途徑和策略提供了可能。
(1) 理論探析----各民族民間文藝互鑒互補的前提性策略。廣大民眾對于本民族民間文藝的風貌及特征一般來說至少保有一定程度的感性印象,而對本民族與其他民族民間文藝的同異關系則一般缺少清晰的體認和理解。故此從各民族民間文藝互鑒互補實踐活動開展角度而言,由專業民間文藝研究者所進行的理論研討活動對普及有關各民族民間文藝常識,并進而引導廣大民眾理性認知各民族民間文藝的特征特色及同異關系問題有很大的助益作用,理論探討和研究因此而成為各民族民間文藝互鑒互補實踐活動得以有效開展的前提性條件。
這種理論研討要防止“書齋”式的空洞探討,而應更多地結合各民族民間文藝的現實存在狀況來進行。理論研究也需要“接地氣”,要為解決民間文藝發展的實際需要而服務。
(2) 人才儲備----各民族民間文藝互鑒互補的主體性策略。原生態的民間文藝大多是代代口耳相傳的集體性創作,并沒有固定、準確的創作者。但在當下民間文藝傳承和弘揚情境下,民間文藝的創新發展卻大多需要有專業的創編者和表演者的參與,尤其是各民族民間文藝間的互鑒互補活動更需要有一些通曉各民族文化及民間文藝的專業創編者、表演者,作為中介性主體條件參與其中。所以,出于各民族民間文藝互鑒互補、共同繁榮的考慮,應著力培養具有貫通遼寧地域各民族文化及民間文藝之學識和素養的藝術創作和表演人才,為遼寧地域各民族民間文藝交流溝通和相互借鑒中的建設和發展儲備過硬的專業人才,提供良好的主體條件。
(3) 精品打造----各民族民間文藝互鑒互補的導引性策略。精品是同類作品中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作品,具有標準和標桿的導引和感召功能。各民族民間文藝從自身的保護與傳承而言,都需要打造精品來提升本民族民間文藝的感召力和影響力。而在這里所探討的“精品”則主要是指在保有自身民族文化特色基礎上,又能以積極的態度去吸納其他民族亞文化場域優秀文化及藝術因子和養分而打造的藝術精品,期望以此類精品為各民族民間文藝的互鑒互補發展活動提供從方向到具體踐行操作的全面導引。
誕生于吉林松原地區的滿族新城戲是以滿族民間八角鼓說唱藝術為基礎形成的一個民族劇種。近年來,松原地區民族文藝工作者努力重振滿族新城戲,以“精品”驅動新城戲發展為策略,打造了諸如《鐵血女真》《洪皓》《皇天后土》《紅羅女》《繡花女》《戰風沙》《箭帕緣》等在國內產生重大影響的系列新城戲精品。這些新城戲精品在音樂、唱腔、樂器、舞蹈、背景、服飾等方面極力突出滿族民族特色,藉此使新城戲獲得穩固的地位。但同時在戲劇的思想情感意蘊方面融入了中華民族的儒家文化特征,體現了對其他民族文化因素的積極吸納借鑒的態度。在滿族新城戲的舞臺上,塑造了一個個鮮活的人物,紅羅女、烏巴圖、阿骨打、烏古倫、洪皓等,探尋滿族新城戲藝術中的憂患意識,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構建全球和平與發展事業而言,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6]。
(4) 平臺構建----各民族民間文藝互鑒互補的踐行性策略。遼寧地域各民族民間文藝共處于具東北文化特色的宏觀文化場域中,這決定了其互鑒互補的可能性,同時,它們又存在于各自不同的民族亞文化場域中,這又決定了它們之間的互鑒互補需要一定的支撐性、輔助性條件。條件之一便是各民族民間文藝獲得共時展示、相互觀摩平臺的建構。此平臺可以采用多元化的建構策略,如文化管理、演藝等部門組織的各民族民間文藝調演、匯演等舞臺展示形式。中央民族歌舞團曾于北京組織舉辦“云貴川----中國少數民族精品音樂會”,為西南地區各民族民間音樂藝術的相互交流和溝通提供了一個充分展示的平臺。其所體現的音樂形態的差別是民族間文化異質性多樣性的表征,是不同民族身份認同的重要因素,是形成中國音樂王國色彩斑斕的核心因素,同時也是中國各民族大團結、大繁榮、共筑強大祖國的中國夢的必要條件。[7]遼寧的文化管理、演藝等部門也應盡可能多的為各民族民間文藝創造類似的交流機會。
平臺的創建也可以采用引導各族民眾自發地組織形成廣場化的民間文藝交流展示場所的方式,此方式具有更強的互動交流功能。云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北部,滇、藏、川三省區交界處,境內有藏、傈僳、納西、漢、白、回、彝、苗、普米等二十余個少數民族。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該自治州文化館就產生了通過各族民眾公共活動廣場來推廣各民族歌舞的想法并踐行。發展到今天,不僅吸引了當地各民族廣大民眾的熱情參與,而且還吸引了大量來當地觀光的游客。迪慶藏族自治州多民族歌舞廣場把存在于各自不同亞文化場域中的各民族民間文藝聚攏于共時性的公共場所,不僅促成了各民族民間文藝的交流、互認、互鑒、互補的效果,同時也為當地帶來了旅游經濟效益。此舉對遼寧地域各民族民間文藝的互鑒互補、共同發展活動的開展有一定的借鑒價值和意義。
此外,還可以依托網絡媒體技術來創建交流范圍更為廣泛、傳播速度更為迅捷的遼寧多民族民間文藝交流平臺獲得更全面、更充分的展示。網絡的多元互動技術優勢也更便于各民族民間文藝跨越不同亞文化場域的深度溝通和交流,在隨機、即時、靈動的網絡情境中達成各民族民間文藝的互鑒互補的共同發展的良好效果。
四、 結 語
民族文化跨越不同文化場域的交流、互鑒、互補已成為當下文化建設活動的基本發展趨勢。同處于東北文化場域中的遼寧各民族民間文藝要積極尋求立足于本民族亞文化場域,而又積極向其他亞文化場域中民間文藝汲取藝術養分的思路和策略。理論的思考和探討是必要的,它能給予實踐以一定的引路作用,但更重要的是理論引導下的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