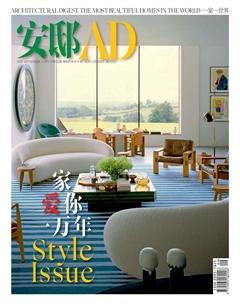愛物吉屋
隋思聰
身兼創意人、時裝買手店主等多重身份的Eric Young,帶著眾多家當搬進了上海老洋房,用時一年有余,把家“養”到了滿意狀態。
深耕時尚業多年的Eric Young把家安在了舊法租界的一棟三層洋房中,這兒離他創辦的買手店LEMONDEDESHC(LMDS)不遠。天氣好的時候,他常步行前住,悠哉地溜達十來分鐘便能到達。洋房所在的弄堂形成于20世紀30年代末,面向淮海中路的人口毫不起眼,卻清晰地分隔了兩個世界:弄堂外是人群熙攘的現代都市,里面則是寧靜安逸的世外桃源。“我們這兒就像一個村莊,跟當代小區的感覺太不一樣了。”Eric說道,“以往我住的都是高層公寓樓,但心里一直有老洋房情結,這回總算如愿以償了。”和伴侶帶著一貓一狗人住后,他將緊湊的小樓布置得井然有序:一層用作客廳與餐廳;二層設有書房、客臥及衣帽間;三層則是包含臥室、浴室、起居室和露臺的主人套間,為私人所享。對待花園,Eric也絲毫不含糊,他翻新了竹籬笆,又在小院里種滿了歐洲月季和繡球花,獨自偷閑或舉辦派對都快意十足。
不少滬上老宅都經歷過“七十二家房客”,但這棟洋房的產權變動相對簡單。樓房初建時的布局得以保存,藝術裝飾風格的各種原配件也都品相極佳,這些都讓熱愛中古元素的Eric心動不已。房子先天條件優厚,Eric本可以輕輕松松“拎包人住”,但他用了足足一年才拆完所有的搬家紙箱,將家具和器物一一構思擺弄至自己滿意的狀態。養成新居戰線侵長,這跟主人家當眾多不無關系。“買東西是一件嚴肅的事情,貫穿整個人生。”Eric如是說道,“別人或許喜歡用照片、文字記錄生活,但對我而言,器物定格的記憶更為鮮活。我每每看到旅行中尋獲的時裝、家具或擺件,當時的場景瞬間就會變得立體起來。”譬如,書房里的一對老上海扶手椅鐫刻著Eric早年尋訪“調劑商店”、跟店主“老周”討價還價相互摸底的情景;而客廳中一只泰國產的藤編托盤是他在曼谷文華東方樓下的小店覓得的,儲蓄著東南亞的鮮活熱力。眾多物什在房間中埋下豐富的線索,向來客述說著Eric經歷的事、走過的路、遇見的人……隨著Eric逐個介紹這些器物,他自1996年抵達上海后的生活軌跡也漸漸明朗。
在這個家中,對Eric具有啟蒙意義的單品是倉俁史朗(Shiro Kuramaa)為Cappellini設計的旋轉儲物柜。二者早在2000年便已結緣。那時Eric剛剛大學畢業,逛街時被櫥窗里這款明紅色的亞克力抽屜柜深深吸引,但20年前這個儲物柜的價格對初人職場的年輕人來說是一個天文數字,他也只好作罷。“那個柜子要價兩萬,當時對我來說是一筆巨款,根本不可能人手。”他回憶道。這件設計猶如Erio心頭的一顆“朱砂痣”,惦記了約有10年才終將其收入囊中。在之后的又一個10年中,它跟隨Eric搬了幾次家,如今被安置在這座洋房三層的主人套間。從相識到相伴的20年里,這個Cappellini的柜子經歷了Eric家居風格喜好的變換,終究沉淀了下來,與生活共融。“時間是繞不開的東西,審美不可能速成。”Eric總結道,“現在柜子里放著貓的零食、臥室用的香氛等,用起來很方便。”
除審美以外,將家具器物融入日常對Eric而言至關重要,雖然他已擁有不少“厲害收藏”,但以前買的“便宜貨”也沒有遭到淘汰或丟棄。“我蠻戀舊的,入手時考慮充分,以后就會一直喜歡。”對Eric而言,喜愛之物不以價格區分。不管是從新疆喀什的巴扎里淘來的手工地毯,還是愛馬仕復刻的Jean-Michel Frank扶手椅,他都一視同仁——用得愛惜,也用得瀟灑。“我想用家具和器物營造舒服愉快的生活狀態,至于審美,在日常中自然養成即可,這樣的家才能真實反映出主人的模樣。”Eric說道,“人不能為了時髦去打造一座跟生活毫無關系的房子,否則再好看的空間也不過是沒有靈魂的,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