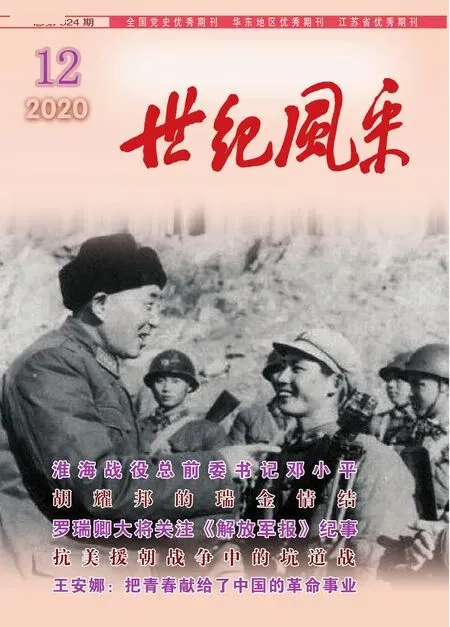歷史不會忘記鄉鎮工業的貢獻
顧介康
鄉鎮工業其前身是“社隊工業”。它萌生于上個世紀50年代末;受挫于60年代;重新起步于70年代;迅猛發展于80年代;90年代后,走上了“兩個根本轉變”即經濟體制和增長方式轉變的新階段。從江蘇特別是蘇州、無錫、常州地區的實踐來看:一是鄉鎮工業是在計劃經濟體制的“夾縫”中萌生的。鄉鎮工業屬“雞”,自己找食吃,它所需要的能源、原材料、技術人才、產品市場都不是國家計劃內的。二是鄉鎮工業是在各種責難聲中成長的。當時不少人指責農民搞鄉鎮工業是“不務正業”,“會嚴重影響農業的發展”;鄉鎮工業“以小擠大”,與城市國有工業爭能源、爭材料、爭市場,“挖社會主義墻角”;鄉鎮工業是“不正之風的根源”,請客送禮那一套是鄉鎮工業搞出來的,如此等等。但鄉鎮工業沒有被“罵倒”,相反在罵聲中茁壯成長。三是鄉鎮工業是在不斷深化改革中保持活力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鄉鎮工業始終與改革相向而行的,從實施“幾定一獎”、經營承包責任制、資產經營責任制,到產權制度改革、調整所有制結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正是在不斷改革中使鄉鎮工業保持和釋放出強大的生命力。80年代前期無錫縣堰橋鄉“一包三改”的經驗(改干部任免制為選聘制、改固定用工制為合同制、改固定工資制為浮動工資制、對企業實施承包經營),可謂是“聞名天下”。四是鄉鎮工業是在不斷擴大開放中壯大的。“三來一補”也好,與外商合資合作也好,引進外商資本也好,都首先是從鄉鎮工業開始的,使鄉鎮工業成為發展外向型經濟的一支生力軍。
在鄉鎮工業剛萌生的上個世紀50年代末,毛澤東就高瞻遠矚地指出:“我們偉大、光明燦爛的希望,就在這里。”在鄉鎮工業進入持續快速發展的80年代中期,鄧小平熱情稱贊她的“異軍突起”,是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在世紀之交的1998年,江澤民專程到江蘇視察鄉鎮工業,在講話中明確指出,發展鄉鎮工業是“一項重大戰略,一個長期的根本方針”。從歷史的眼光來觀察鄉鎮工業的發展歷程,可以清楚地看出鄉鎮工業的異軍突起,改變了農村的經濟結構和生產方式,突破了傳統的城鄉關系,推進了農村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的協調發展,為探索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了先導性實踐,開辟了農民致富的新途徑,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她不僅對農村,而且對整個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都具有深刻的意義。

無錫一家鄉鎮企業車間
一、鄉鎮工業異軍突起,開創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推進工業化的嶄新道路
實現工業化,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不可跨越的歷史階段。西方發達國家完成這一過渡,即工業化前期階段,明顯地表現出三個特點:一是靠剝奪農民(同時也靠掠奪殖民地)為工業提供原始積累;二是大量破產的農民涌入城市,為工業化發展提供廉價勞動力;三是工業企業集中在城市,工業化的過程也是城市迅速擴大、膨脹的過程。中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基礎薄弱,城市實力不強,人口眾多,而農民又占了絕大多數。在實現工業化,推進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的歷程中不可能重走西方發達國家的老路。因為,一不能剝奪農民,二不能讓那么多農民都涌進城市。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工業化道路,這是新中國成立以后一直探索的重大課題。而鄉鎮工業的異軍突起,靠社區農民集體農業為發展工業積累原始資本;由農業上轉移出來的“離土不離鄉”的農民直接進入農民自己辦的工廠做工。這就在加快城市工業化的同時,開創了農村工業化的嶄新道路。城鄉工業相互依托、相互結合、相互促進,加快了工業化的進程。據江蘇的統計資料顯示:在單一計劃經濟時期,江蘇工業總產值突破100億元,整整用了20年時間;自鄉鎮工業發展起來以后,江蘇工業總產值突破200億元,僅用了8年時間。1978年至1997年,江蘇工業總產值從337.65億元(當年價,下同)增至12542.40億元,增加了12204.75億元;同期江蘇的鄉鎮工業由62.34億元增至7856.85億元,增加了7794.42億元,占全省工業總產值增加部分的63.9%。從江蘇國內生產總值中一、二產業所占的比重來看,1952年分別為52.7%和17.6%;經過20年的發展,到1972年基本持平,分別為38.3%和39.2%;到1994年,第一產業比重明顯下降,為16.6%,第二產業比重明顯上升,達53.9%。在這后22年中,正是鄉鎮工業大發展時期,年均增長率高達25%以上,鄉鎮工業在全省工業經濟中的比重由不到20%上升為66.7%。由此可見,江蘇工業經濟在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大幅度提升,主要是由于鄉鎮工業的迅速發展。這表明鄉鎮工業的異軍突起,在中國形成了城市工業和鄉鎮工業兩條腿走路的新格局,首先在農村經濟中實現了由農業經濟為主向工業經濟為主的轉變,從而推進了整個國家工業化的進程,這是中國不同于西方發達國家實現工業化的一個顯著特點。
二、鄉鎮工業的異軍突起,開創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的嶄新道路
農業始終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沒有農業的現代化,就沒有整個國民經濟的現代化。加快農業現代化的步伐,對于我們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土地資源有限的大國而言,更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國際國內的經驗表明,實現農業現代化,即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僅僅靠農業自身的發展和積累是不可能實現的,只有當工業化進入到一定階段以后,才能為農業提供先進的技術裝備,實現農業的機械化,大幅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業規模效益;也才能為實現“科技興農”戰略、建設現代化農田基本設施提供足夠的投入,大幅度提高土地產出率和農業商品率。中國的工業化靠的是鄉鎮工業和城市工業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決定了對農業現代化的支持,應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靠城市工業的發展支持農業,這主要是靠政府運用各種經濟杠桿實施正確的調控、導向來實現的。但城市工業還處在快速發展中,實力不強,很難給農業以更多的支持。另一方面,則靠農村鄉鎮工業的積累反哺農業。從江蘇的實踐來看,后一條起著十分關鍵的作用。鄉鎮工業是從農業母體中分離出來的,最初發展鄉鎮工業的指導思想就是“圍繞農業辦工業,辦好工業促農業”,后來大大突破了原來的設想。但是鄉鎮工業與農業的緊密聯系并沒有改變,鄉鎮工業的廠長、經理和廣大職工對鄉鎮工業反哺農業具有一種天然的感情,這是城市工業無法相比的。在鄉鎮工業反哺農業的過程中,經歷了“以工補農”和“以工建農”兩個階段。“以工補農”,主要是用鄉鎮工業的一部分積累補償務農勞動力因農產品價格因素造成的損失,其目的是調動和保持農業勞動力的生產積極性。“以工建農”,則是用鄉鎮工業的積累來加強現代農業的基礎設施建設,購置先進的農業機械,支持農業科技成果的推廣和應用,其目的是加快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據統計,1978年至1997年的20年間,江蘇全省集體工業企業支農、建農資金達71.37億元,按全省耕地(1990年數)平均,每畝達104.39元,在鄉鎮工業發達的蘇、錫、常地區大大超過這個平均數。1997年,僅鄉鎮集體工業企業在成本費用中列支的支農、建農支出就達2.54億元。當時,在蘇南地區建設“噸糧田”,每畝平均所需經費在3000元左右,主要來自鄉鎮集體工業的積累。以當時鄉鎮工業最發達的“華夏第一縣”無錫縣為例,在1990年代前期,每年鄉鎮工業“以工建農”的資金達1億元左右,相當于縣財政對農業投入的9倍。該縣有個梅村鄉,用鄉鎮工業的積累建設“灌溉暗渠(地下渠道)”,當時有20多個國家的總統、總理前往參觀。在上世紀90年代前期,這個縣就基本上實現了農業機械化,占全縣總勞動力2.5%的農業服務專業隊伍,承擔了全縣稻麥兩熟80%左右的工作量,以社區集體所有的村辦農場經營了全縣60%以上的商品糧農田,農業規模效益大大提高。這些農場成了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積累、自我發展的現代農業企業。沒有鄉鎮工業的“以工建農”,農業現代化的步伐不可能如此之快。江蘇的實踐表明,發展鄉鎮工業并沒有以犧牲農業為代價,相反,由鄉鎮工業為支撐,以農村工業化帶動、促進了農業現代化,實現了工業和農業的協調發展。
三、鄉鎮工業的異軍突起,開創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城鎮化的嶄新道路
在一個特定區域的經濟社會發展中,中心城市起著主導的作用,以其發達的科技、教育所形成的智力優勢、現代工業形成的先進生產力優勢和強大的金融、商貿優勢,向周圍農村輻射自己的能量,來帶動整個區域城鄉經濟社會的共同發展,這是一個普遍規律。而鄉鎮工業的異軍突起,改變了這一常規,使城鄉關系發生了新的變化,突破了“農村農業,城市工業”“農產品進城,工業品下鄉”這樣一種城鄉關系的傳統格局,形成了物資、資金、人才、技術、信息、商品在城鄉之間雙向交流的新格局。而星羅棋布的農村小城鎮成了連接城市與農村的橋梁和紐帶,成了傳遞城市輻射農村的“中轉站”,成了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蓄水池”。從農業上轉移出來的勞動力,小部分進入大中城市,大部分在本地小城鎮上居住下來,從事二、三產業。他們的物質、文化生活與大中城市的居民沒有多少區別。上個世紀80年代初,我國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提出了“小城鎮,大問題”這一重要命題。90年代初,江澤民同志提出了“小城鎮,大戰略”這一重要思想。“大問題”“大戰略”,都深刻揭示了農村小城鎮在推進城市化、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和特殊作用。這是中國城市化區別于西方發達國家城市化的一個顯著特色。從江蘇的實踐來看,小城鎮的發展與鄉鎮工業的異軍突起都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歷史文化名鎮的修復改造、水路交通碼頭的繁榮、絕大多數小城鎮的建設興起,都是靠鄉鎮工業的發展和積累來支撐的。由此可見,鄉鎮工業的異軍突起,對推進農村城鎮化、加快整個城市化的步伐,也是功不可沒的。
四、鄉鎮工業的異軍突起,開創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先導性實踐
鄉鎮工業之所以能在計劃經濟的“夾縫”中艱難而頑強地茁壯成長,其內在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從她誕生之日起所遵循的就是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誠然,鄉鎮工業的開創者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不可能具有明確的市場經濟的概念,只是懷著“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的信念,為了企業的生存,在計劃經濟體制的“夾縫”中艱難地開拓市場調節的活動空間,在國家計劃外的市場上進行購銷活動。起初是“三就地”,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銷售,制造為農業生產、為農民生活服務的生產資料和生活必需品。接著是發展城鄉協作,借用城市的技術、人才,開拓城鄉市場,彌補國家計劃的不足。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的中后期,城市工廠停工停產,鄉鎮工業乘機而起,興辦和發展了一批為城市工業“拾遺補缺”的輕工產品和農機產品。在上世紀70年代末的國民經濟調整中,鄉鎮工業發揮“船小好調頭”的優勢,根據市場需要,迅速變換品種,生產符合市場需要、適銷對路的產品。進入80年代后,在改革開放、新舊體制轉換條件下,鄉鎮工業發揮對市場應變能力強的優勢,進一步以市場為取向,實施全方位、多渠道、多層次對外開放,實現由國內市場拓展到國際市場的重大戰略轉換。同時,鄉鎮工業的每一步改革,也都是以市場為取向的。鄉鎮工業萌生、發展、壯大的過程,不斷經受著市場經濟“優勝劣汰”“生生死死”的考驗。她還催生了城市和國有經濟的改革,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創立,提供了先導性的成功的實踐依據。可以說,由中國農民創造的鄉鎮工業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始的開拓者和先行者。
五、鄉鎮工業的“異軍突起”,開創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致富農民、改造農民小生產者的嶄新途徑
幾千年來,農民以種田為生,經受地主階級的剝削,收入低下,長期處于貧困狀態。新中國成立后,農民在政治上、經濟上翻了身,當家做主人,生活狀況有了一定改善。但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工農業產品價格存在嚴重的“剪刀差”,那么多農民在有限的土地上耕作,農業勞動生產率、商品率不高,加上天災人禍的影響,農民的經濟收入不高,大多數農民的貧困狀態并沒有根本改變。鄉鎮工業的異軍突起,吸納了大批從農業上轉移出來的勞動力,為農民增加收入開辟了一個新的渠道,徹底改變了農民僅靠農業收入維持生計的狀況。據1997年統計資料,江蘇全省鄉鎮集體工業企業僅支付工資、福利費、勞動待業保險費達303.4億元,按全省農業人口平均達576元,占全省農民人均純收入的22.1%,在鄉鎮工業發達的蘇、錫、常地區,務工收入成了農民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同時,分布在廣闊農村的鄉鎮工業企業,吸納了大批的農民小生產者進入現代化的工業生產流程。他們既保留了農民的傳統美德,又逐漸接收工人階級的先進思想意識,接受現代科學文化知識。鄉鎮工業如一座座大熔爐、一所所大學校,把與泥土打交道的傳統農民小生產者鍛煉改造為操縱現代大機器的工人、馳騁國內外市場的商人、精于企業管理的企業家。特別是在鄉鎮工業發達的蘇、錫、常地區出現了一個可喜的發展趨勢。這就是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社會主義的基本道德觀念、共產黨人的奉獻精神,同現代商品經濟觀念、市場競爭意識逐漸融合起來,培育和造就新一代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共產黨人新的革命品格和思想風貌。尤其是那些出身于農民的成功創業的鄉鎮企業家,他們經歷了為個人致富、實現自身人生價值、帶領群眾致富、回報社會幾次思想境界的飛躍。他們不僅是發展農村經濟的組織者、指揮者,也是農村文化建設的組織者、指揮者。以鄉鎮工業為依托,農村的科技、教育、文化設施逐步完善,引發了新中國成立后又一個農村文化建設的高潮。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曾聞名一時的沙洲縣(今張家港市)兆豐鄉“以工養文”的文藝工廠,其職工在廠是工人,在舞臺上是演員,以工廠的盈利支撐編劇、排練、演出的費用,曾進北京中南海演出,得到了當時中央領導同志的贊揚。再者,由鄉鎮工業支撐的農村小城鎮的發展,使進鎮的農民經受了現代城市文明的熏陶,使他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思想觀念、行為習慣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由傳統農民向現代市民轉變。毛澤東同志曾指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鄉鎮工業的異軍突起,開創了改造農民小生產者的有效途徑,推進了農村物質文明建設與精神文明建設的協調發展,其思想意義比經濟意義更為深刻,也更為久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