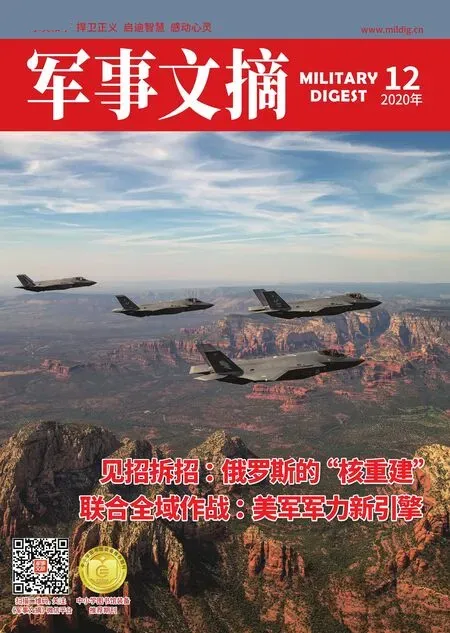透視支撐“印太戰略”的“協同作戰能力”系統
吳敏文

2020年8月19日,美國海軍主戰艦載機F/A-18E/F“超級大黃蜂”的設計生產商波音公司,在馬里蘭州帕特森河海軍航空站進行滑躍式起飛試飛。由于印度是“印太戰略”美、日、印、澳四國中,第二個擁有航母而且是艦載機滑躍式起飛航母的國家。波音公司此舉,隨即被視為美軍正為美、印海軍艦載機在對方航母上起降做準備。
美國明確針對中國的“印太戰略”是一個聯盟戰略,各主要參與國在政治、經濟和軍事領域的宏觀協調與合作顯而易見。然而,在軍事領域,由于現代戰爭是多軍兵種一體化聯合作戰,不僅在一國內要三軍聯合,而且盟國軍隊之間也要聯合。那么,多國軍隊的軍事行動,靠什么實現一體化聯合?“粘合”多國、多軍兵種作戰力量與平臺的深層鏈接是什么?
“印太戰略”需要“協同作戰能力”系統的支撐
美國地緣政治學家和政治家布熱津斯基說:“美國在全球至高無上的地位,是由一個覆蓋全球的同盟和聯盟所組成的精細體系支撐的。”“印太戰略”就是一個為了維持美國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的“至高無上的地位”而組建的,主要由美、日、印、澳等國組成的聯盟體系戰略。美國現政府上任以來,“印太戰略”的推進力度空前加大。
2017年11月,在美國總統特朗普展開他上任后的第一次東亞之行中,在日本和越南等國的講話,分別提及“自由而開放的‘印太地區’”和“美國在這一地區保持領導地位的必要性”。2018年5月30日,為了適應“印太戰略”的需要,美國將總部設在夏威夷珍珠港的太平洋司令部更名為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
2019年6月1日,美國國防部發布關于“印太戰略”的首份權威文件《印太戰略報告》,系統分析了印太戰略格局及其趨勢與挑戰,從做好準備、加強伙伴關系、建立區域化網絡等方面詳細論述了保持美國地區影響力的途徑;強調美國必須“以強大的軍事實力尋求和平,與盟友和合作伙伴共同承擔責任以防范共同威脅”,以及“我們的同盟及合作伙伴是實現和平與交互作戰的力量倍增器”。
2020年6月11日,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高票通過了總額7405億美元的“2021財年國防授權法案”。這一法案特別單列“太平洋威懾倡議”基金,2021財年撥付16億美元,此后在2022財年—2026財年再投資184.6億美元。總投資超過200億美元的款項,主要用于提升駐太平洋地區美軍的導彈防御能力、增強印太地區美軍的前沿部署態勢和加強印太同盟和伙伴關系,提升與伙伴國軍隊的互聯、互通、互操作性和信息共享、信息支援能力。
與此同時,2020年4月10日,日本防衛研究所發布年度更新的《東亞戰略概觀2020》,大肆渲染“日本必須在‘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構想下維護和加強開放的海事秩序”。7月14日,日本發布2020年版《防衛白皮書》,對周邊局勢評估結果極為負面,為強化日本防衛力量以及加強美日同盟渲染不安氣氛,制造緊張氛圍。對此,俄羅斯方面認為,在美國的放任和縱容下,日本和平憲法已經無法約束日本增強實際國防能力,“對華盛頓來說,日本是對抗中國與俄羅斯的前沿陣地。”
2020年7月1日,澳大利亞國防部發布《2020年國防戰略更新》,將印度-太平洋地區作為未來國防規劃重點方向,提出從印度洋東北部到東南亞,再到巴布亞新幾內亞和西南太平洋的周邊地區,是澳大利亞最直接的戰略利益區,也是澳大利亞與盟國開展軍事合作的地區。
綜觀美、日、印、澳以上規劃與部署,可見“印太戰略”不僅在宏觀上已從合作意愿走向協調一致,而且從戰術、技術層次開始密切的合作。其突出表現是強調盟友之間的合作和協作,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各國不約而同提到“協同作戰”和“協同作戰能力”,并將其界定為“力量倍增器”。
對美軍而言,“協同作戰能力”不是一個語義的、宏觀的、籠統的描述,而是一個實際存在的系統和裝備。美軍不僅已經將這個系統裝備本國陸、海、空三軍作戰平臺,而且開始在日本、澳大利亞等盟國軍隊的作戰平臺上陸續部署和安裝使用。

美軍F-18 E戰斗機
“協同作戰能力”系統的功能
“協同作戰能力”的英語是“Cooperative Engagement Capability”,簡稱“CEC”;也有將其譯成“協同交戰能力”的,但譯成“協同作戰能力”的居多。
“協同作戰能力”系統的出現,源于現代海戰的需求。現代海戰中,航母戰斗群的防空體系面臨全新挑戰。艦隊所面臨的威脅不再局限于飛機投擲的炸彈和魚雷,還有敵空中、水面、陸地發射的各種精確制導彈藥,包括智能化彈藥和超高超聲速導彈等,這些威脅使航母戰斗群的防空體系必須在復雜形勢下快速反應。而航母戰斗群中的單個預警探測傳感器,各自的探測偵察能力存在性能、方式、地域、范圍、速度、精度等局限。例如,以單獨方式使用E-2鷹眼和宙斯盾驅逐艦上的雷達,探測和跟蹤從飛機到巡航導彈、彈道導彈等各種目標時,散射效應和環境因素的相互作用會降低探測和跟蹤質量。對于具有超高速和低可觀察特征的重要威脅,不能及時發現并對其進行連續跟蹤,進行規避或是摧毀,后果無疑是災難性的。
“協同作戰能力”系統在美軍各軍兵種的推廣應用,能夠將分布在陸、海、空、天多維作戰空間的各種預警探測、情報偵察系統、指揮控制系統和武器系統有機結合,使戰場態勢高度共享、部隊協調同步、作戰行動快速實時,從而實現整個作戰體系的整體作戰效能的質的飛躍。概而言之,“協同作戰能力”系統具有以下功能。

2019年11月美國防部印太戰略公開版

2020年4月日本防衛研究所《東亞戰略概觀2020》

2020年7月澳大利亞國防部發布《國防戰略更新》
首先,為一體化聯合作戰體系提供傳感器網的“無縫”鏈接。傳感器網是一體化作戰體系的神經末梢,是所有戰場態勢感知的信息源頭。為指揮員提供高度透明、連續不斷的戰場態勢信息,傳感器網至為關鍵。“協同作戰能力”系統可將分布在陸、海、空、天的各類專用偵察設備和各種武器平臺上的嵌入式偵察設備等聯成網絡,使任務部隊克服任何單個傳感器的局限,實現信息高效共享的有效工具。
其次,為一體化聯合作戰體系提供戰術信息共享。美軍為戰術信息共享發展了多款戰術數據鏈,例如海軍使用的Link-11和三軍通用的Link-16等。但Link-11僅限于海軍作戰平臺,Link-16雖然三軍通用,但傳輸的信息極為有限。而且,它們傳輸的是來自本平臺傳感器并經過處理后的結果數據。“協同作戰能力”系統不僅可裝備各軍兵種作戰平臺,而且它傳輸的是傳感器直接獲取的數據。這就使得“協同作戰能力”系統在信息共享的效率上和速度上都具有獨特的優越性。“協同作戰能力”系統的每套裝備由封裝在一個加固機箱里的30臺摩托羅拉68040處理機組成,并包括一整套復雜的算法和程序,為大量的數據融合提供強大的信息存儲和處理能力。通過共享傳感器數據并在每套系統中設置處理機陣列,實現傳感器數據在各個平臺的同步處理。從而,在毫秒級時延內,完成數據融合和數據分發,以實現戰場網絡眾多平臺之間的高度協同。
最后,為一體化聯合作戰提供協同打擊能力。“協同作戰能力”系統使戰斗群中各作戰單元以極短的延時共享其他作戰單元獲取的傳感器目標數據并進行同步處理,使整個作戰體系中的各個平臺能夠實時地協調動作,選擇處于最佳陣位的武器和彈藥對目標進行打擊。戰斗群中的某一作戰單元即使自身的雷達并沒有掌握目標諸元數據,也可以根據來自網絡的其他傳感器探測數據進行融合處理,對目標實施攻擊,實現真正的“超視距攻擊”。
“協同作戰能力”系統大大擴展了作戰平臺和作戰體系的探測范圍,提高了目標發現和跟蹤快捷性、準確性,改善了識別能力,為指揮員提供了更高質量的戰場態勢信息,縮短了從發現到摧毀之間的時延,從而擴展作戰空間,實現超視距打擊,同時也提高了區域、局部和作戰單元的自我防御能力。
“協同作戰能力”系統在“印太戰略”中的作用
通過在美陸、海、空三軍平臺裝備“協同作戰能力”系統,實現美軍內作戰平臺共享傳感器數據和戰術態勢信息;通過裝備盟國軍隊作戰平臺,實現在美軍與盟軍之間作戰平臺級的傳感器數據和戰術態勢信息共享,實現作戰平臺與單兵層級的信息共享和一體聯動;從而達成美軍所追求的,使“協同作戰能力”系統成為美軍和盟軍聯合作戰的“力量倍增器”。
“協同作戰能力”系統主要由美國海軍于1987年開始研制;1995年通過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測試,即用“協同作戰能力”系統將艾森豪威爾號核動力航母、2艘宙斯盾巡洋艦、1艘兩棲攻擊艦以及P-3偵察機聯成網絡,對包括目標綜合航跡的生成與目標敵我識別、遠程數據在本地火控系統中的應用、強電子干擾環境下的目標信息獲取,以及近實時的數據通信等各項系統功能進行了成功的驗證。據此,美國國會和國防部決定將“協同作戰能力”系統應用范圍由海軍擴展到陸軍和空軍。

美軍Link-16與Link-11數據鏈使用示意圖
美海軍繼在給宙斯盾巡洋艦安齊奧號與圣喬治號裝備“協同作戰能力”系統并形成作戰能力后,相繼在艾森豪威爾號航母,黃蜂號兩棲突擊艦,休城號、維克斯堡號導彈巡洋艦上安裝了該系統。從2000年開始,美軍陸續裝備主要的水面艦艇、其他美軍航母和E-2C艦載預警機。迄今,美國海軍的現役航母及兩棲攻擊艦等主要戰艦,空軍主要作戰飛機及陸軍的重要平臺與設施,已分期分批安裝了該系統。
為適應“印太戰略”的需要,美軍加速在澳大利亞和日本等盟國軍隊的主戰平臺安裝和部署“協同作戰能力”系統。澳大利亞基于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在軍事上一直緊密追隨美國,也是“印太戰略”的主動參與者和積極推動者,澳軍成為最先部署和安裝“協同作戰能力”系統的軍隊,也就不足為怪。
2017年12月,美軍開始在澳大利亞海軍的霍巴特級驅逐艦上安裝“協同作戰能力”系統。2018年11月,安裝了“協同作戰能力”系統的霍巴特級驅逐艦的首艦霍巴特號和二號艦布里斯班號,在南澳大利亞海岸進行了一系列測試。在當年的夏威夷演習期間,澳大利亞海軍的霍巴特號與美國海軍伯克級驅逐艦約翰芬恩號通過“協同作戰能力”系統建立了安全的數據鏈接,兩艦共享了來自傳感器網的目標跟蹤和火控數據,驗證了美、澳海軍通過“協同作戰能力”系統聯合作戰的可行性。
迄今,澳大利亞軍隊安裝了“協同作戰能力”系統的平臺包括海軍的第三艘霍巴特級宙斯盾驅逐艦、獵手級護衛艦,以及空軍的E-7A預警機和陸軍防空反導系統等。
日本海上自衛隊是第二個獲得“協同作戰能力”系統的美盟國武裝力量。2018年,日本海軍自衛隊的DDG27型驅逐艦摩耶號下水,搭載“協同作戰能力”系統成為該艦最大的亮點,它使得此艦能與美軍共享陸、海、空、天傳感器網情報,戰時與美海軍第七艦隊聯合作戰。此外,日本空中自衛隊購自美國的F-35A隱身戰斗機出廠即裝備“協同作戰能力”系統,目前正加緊在E-2D預警機、海上自衛隊的宙斯盾驅逐艦等加裝這一系統。
由于印度與俄羅斯之間的長期盟友關系,以及在裝備種類和水平上的差異,目前尚未有印軍平臺加裝“協同作戰能力”系統的計劃或事實。但是,印度在“印太戰略”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隨著美國遏制中國力度的加大,拉攏和與印度發展軍事合作的意圖日益明顯;但是,印度是一個人口和政治、經濟、軍事大國,具有自主的外交選擇和利益關注,尚未做出鐵心加入“印太戰略”的決定,是否裝備“協同作戰能力”系統進入美軍網絡,既有政治問題也有技術障礙,究竟如何發展,尚待后續觀察。
總的來說,“協同作戰能力”系統作為支撐以美國為主導的“印太戰略”的深層紐帶,不僅可以將美國陸、海、空、天作戰平臺,而且可以將盟國軍隊作戰平臺,納入統一的OODA(觀察、定向、決策、行動)循環和“從發現到摧毀”的網絡之中,實現作戰單元和平臺一級的一體化聯合作戰。說“協同作戰能力”系統決定美軍與盟軍聯合作戰的程度與深度,絕非過甚其言。至于其與“印太戰略”的關系,從該系統于2000年開始大量裝備美軍,到2017年開始裝備盟國軍隊,與美國大力推進的“印太戰略”在時間點上如此高度契合,絕非偶然。
為了實現這樣的目標,美國正在加大投入,除專項“太平洋威懾倡議”基金之外,在美國“2021財年國防授權法案”中所列的“聯合兵力殺傷”專項,投入達58.5億美元,用于“在西太地區島嶼分散部署一支具有精確打擊網絡、生存能力強的聯合作戰部隊,在第一島鏈部署陸基反艦和防空導彈系統;在第二島鏈部署一體化防空反導系統”。對于“聯合兵力殺傷”,“協同作戰能力”系統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