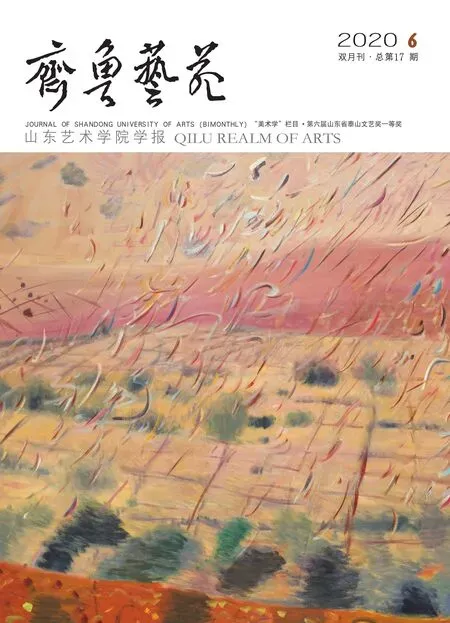中國紀錄片創作的詩意建構
潘夢歌,吳保和
(上海戲劇學院電影電視學院,上海 201112)
中國紀錄片受中國文學與中國詩歌詩化表達的影響,而令其創作呈現出詩意化的特征。為了更近一步探究中國紀錄片的詩意化表達,本文將結合具體作品分析其影像表達以及作品背后蘊藏的人文關懷與哲學思考,并在此基礎上從美學角度出發,探討中國當代紀錄片詩意建構的審美變遷。
一、寫意性:中國紀錄片詩意的特性
中國紀錄片詩化的表達離不開中國文學與中國詩歌的滋養,也正是二者與紀錄片的融合,才能夠將詩化的獨特魅力,通過紀錄片這一藝術形式得以顯現。
中國文學起源于詩歌,詩化表達是其重要特征。“詩與文體迥不類,文尚典實,詩貴清空;詩主風神,文先理道”(1)見胡應麟《詩蔽·外編》卷一。。詩與文的區別,古人已做了很多理論闡釋:在具體的創作上,中國古代則有著“以文為詩”和“以詩為文”兩種打通詩文界限的創作現象。[1](P7)無論是詩歌還是包含其內的中國文學,其詩化的表達都旨在將詩意在意境中生成,而這種表達也體現在中國文化的其他領域,包括紀錄片在內的中國電影中。
(一)詩化傳統對紀錄片的影響
黑格爾說過:“詩比任何其他藝術的創作方式都要更涉及藝術的普遍原則,因此,對藝術的科學研究似乎應該從詩開始”[2](P14)。研究紀錄片似乎也可以從詩化傳統對于紀錄片的影響開始。
20世紀70年代末以《話說長江》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其鏡頭與解說詞大都是詩意的。正如《話說長江》中,畫面多次定格在奔流不息的長江,并以充滿感情色彩的解說詞賦予畫面生命,讓中國的母親河——長江的形象更加立體地呈現在觀眾面前。正是解說詞與畫面的配合,傳達出全片濃郁的詩意。90年代以來,在西方紀錄片大師的影響下,中國紀錄片人在吸取中國詩歌內在精髓的同時,不斷拓寬自己的視野,使得該階段的紀錄片創作頗具詩意。王海兵的《藏北人家》、孫曾田的《最后的山神》、段錦川的《廣場》、雎安奇的《北京風很大》等為代表的紀錄作品,其詩意的表達都是將詩歌的表意系統滲透在紀錄片的表達當中,將人們司空見慣的日常生活中的體驗用攝影機記錄下來,從獨特的視角觀察這個地方、這個現象。這個時期創作的紀錄作品不斷吸收西方先進的紀錄片理論思想,并將這些理論與創作動機進行內化形成富有民族化語境的“詩意”。21世紀以來,以紀錄片《大國崛起》《新絲綢之路》《河西走廊》等為代表的人文地理紀錄片,大都運用文學化傳統,將“詩性”與中國的人文地理相結合,以形式美賦予自然和情感。在追求“精致”畫面效果的同時,運用文學化的表意系統,通過紀錄片的形式,將背后的人文關懷、鄉土情懷、哲學思考以及對現實的反思挖掘出來,而顯現出真實的“詩性”之美。2010年以來,紀錄片的詩意傳遞更多是是透過影像語言實現。創作者不再滿足于人文地理類作品的創作,而逐漸向現實生活靠攏,創作與大眾日常狀態相關的內容,挖掘其中的詩意。紀錄片《人生一串》曾多次出現押韻的解說詞,朗朗上口而延長了食物在觀眾腦海中停留的時間,同時將充滿煙火氣息的市井生活描繪得淋漓盡致。同樣在紀錄片《風味人間》中,解說詞的押韻之感消除了觀眾與美食文化的隔閡,深化了其可銘記性。詩歌的韻律離不開押韻,紀錄片的詩意化表達在詩歌韻律的基礎上加以轉化,形成獨具特色的紀錄片韻律之感,豐富了其影像表達樣態。正是詩化傳統對于中國紀錄片的影響,才使其魅力得以長久存留。
詩化傳統對紀錄片的影響不局限于此,其詩歌和文學常以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方式透過文字含蓄地表達情感,而紀錄片則將這種含蓄的表達方式,外化為導演的主觀化表達。紀錄片《西南聯大》以唐代詩人杜甫所寫的《旅夜書懷》中的“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作為開篇,引出導演對于西南聯大的懷念。導演正是借用詩歌化的表現手法,配合紀錄片獨有的影像語言,將詩人杜甫內心的感傷,通過管弦樂器的演奏、灰白動畫的閃現,而引起觀眾情感上的共鳴。在紀錄片《人生第一次》第3集《長大》中,導演選擇用詩歌去詮釋孩子們的內心世界。正如影片中解說詞所描述的那樣——“對于升學毫無幫助的詩歌,在這些孤獨孩子的內心又留下了什么?”這些現代詩歌的寫作,卻是這群孩子內心的真實寫照。紀錄片旨在通過對詩歌的解構,凸顯導演的主觀創作意圖,以實現其個人情感的表達。
詩化的表達是語義朦朧的,紀錄片則在紀實的基礎上,通過意象的疊加,形成獨特的詩意化表達。吉加·維爾托夫導演的《持攝影機的人》,內容看似是攝影機如何拍攝的過程,實則是通過各種意象的疊加、素材的提煉、剪輯的排列組合,將城市與市民的蘇醒聯系在一起,把攝影機當作是人的眼睛,透過攝影機見證一切事物的鮮活存在。西方導演對于意象的使用是直接鮮明的,而中國導演對于意象的處理卻是內斂含蓄的。如陸慶屹導演紀錄片《四個春天》中多次提及燕子飛來了,導演賦予“燕子”多重語義。在該片中燕子承載著喜悅、春天、回憶、笑容等多種意義,正是意象的疊加,使得“燕子”在影片當中不僅僅作為春天到來的象征,而且也是表意特征滲透到了影像語言當中的修辭,與片名《四個春天》相互呼應,使得其呈現更加耐人尋味。
(二)寫實、寫意與營造意境
在紀錄片的創作中,寫實與寫意是難以相互取代的,某些內容需要寫實方法來反映,而有些場景適合用寫意的形式來表現。除此之外,中國紀錄片創作的詩意建構,還需借助寫意性來營造意境。
1. 寫實與寫意的關系
在紀錄片的創作過程中,寫實與寫意并不矛盾。寫實延續著紀實拍攝的原則,寫意填補著紀實拍攝的意境空白,所以紀錄片的創作需要寫實與寫意的功能互補,以形成有機的整體。在菲爾·查普曼導演的紀錄片《美麗中國》中,紀實部分主要展現中國的野生動物植物和人文景觀,而寫意部分通過營造意境挖掘畫面潛在的意韻之美。紀錄片作品中運用寫意鏡頭,能夠豐富畫面的信息量,營構視覺的吸引力。這種虛實結合的手法,構建出情景交融的審美體驗,進而描摹出象外之境,抒發出韻外之旨。
2. 營造意境
中國紀錄片的美表現在形式上,是注重中國傳統美學“意境”觀念的運用,通常在紀錄片的攝影機運動和美術場景的設計中,可以看到中國式“美”的設計。比如在紀錄片畫面中經常出現中國畫的“留白”“線描”等寫意手法,采用簡筆手法,其場面調度和敘事帶有“氣韻生動”的中國美學特質。[3](P175-176)
在紀錄片創作過程中,對于意境的營造,通常會用對比、反復、隱喻、象征等意象表現手法。在紀錄片《如果國寶會說話》當中,一件件國寶通過導演的擬人化處理出現在公眾視野,而也正是這樣的表現手法,使得紀錄片的風格,更加貼合現代人的審美,從而贏得大眾的喜愛。紀錄片《四個春天》中,有一個隱喻表現手法下所呈現的畫面,母親占據畫左在縫紉機前勞作,父親則占據畫右在電腦前剪輯。整個畫面一分為二,將父母的生活,劃分為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此時隱喻的表現手法,豐富了畫面內容的表達,體現出深層的詩意。
中國紀錄片的寫意性與個體的審美趣味緊密關聯,多表現為通過情景交融的方式,將創作者的主觀審美感知與自然景象交融滲透,再充分運用寫意式的拍攝風格,在寧靜與平淡中營造出悠然淡泊、意味無窮的詩意境界[4](P176)。如張以慶導演的紀錄片《幼兒園》,故事的主體分別是幼兒園大中小班的孩子。通過鏡頭之于日常生活的捕捉,作品以孩子的言行舉止,折射出對成人世界的觀照,這種觀照就是導演個性化的主觀表達——對成人世界的委婉批評。該紀錄片中多次出現空鏡頭,其不再只是單純描述景色,而是被賦予故事與情感。當家長們在放學后陸陸續續接走班里的孩子,紀實的拍攝方法將人群來來往往的動態記錄下來,直到班里就只剩下一個孩子。鏡頭沒有過多定格在孩子焦急等待父母的身影,而是將畫面切換到空鏡頭,此刻空鏡頭交代了天色漸暗的環境,同時反襯出人物內心深處的孤獨之感。
二、詩意化的影像表達
紀錄片的“真實性”應如何界定一直存在爭議。為了達到真實的效果,紀錄片的創作經常采用不同的拍攝方法。不過,紀錄片詩意化的影像表達,是建立在相對客觀真實的基礎上,導演通過對現實素材的陌生化處理、主觀鏡頭的運用、聲音的表情達意等多種藝術表現手段實現“詩化模式”的美學追求。紀錄片的詩意來自于攝影機對現實生活的捕捉,通過鏡頭發掘最具表現力的影像語言來加以渲染。
(一)“陌生化”處理
紀錄片可以將熟悉的現實素材進行陌生化處理,通過剪輯的方式對素材進行提煉與加工,重新排列組合形成新的邏輯順序,使得其在整體上呈現出詩意。在張以慶導演的紀錄片《英與白》中,導演將我們熟悉的飼養員生活進行了陌生化處理,通過后期剪輯的排列組合形成了影片的蒙太奇節奏,通過低機位的拍攝方法捕捉“英”與“白”的生活狀態,呈現在觀眾面前的是女主人公“白”與熊貓“英”之間復雜的情感。紀錄片的陌生化處理打破了觀眾對于事物的刻板認知,讓他們從狹隘的日常關系束縛中解放出來,不再受客觀規律的制約,從而感受作品的詩意。紀錄片《人生第一次》第3集《長大》,透過施應鎖和穆慶云兩位主人公的視角,將現實生活中我們熟知的“詩歌”進行陌生化處理,通過剪輯形成畫面的節奏。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并不是戶外的“詩歌”教學,而是把我們容易忽視掉的詩歌內在的寓意,通過孩子們的寫詩、讀詩,有感于詩歌通過畫面富有邏輯性的組合傳遞給觀眾。關乎詩歌的情感表達,也就伴隨著孩子們的書寫與朗讀油然而生,而紀錄片呈現給觀眾的是聲畫和諧的詩意。
(二)主觀鏡頭的運用
紀錄片的創作離不開主觀鏡頭的運用,將導演的主觀性表達隱藏在影像語言當中,既可以利用直觀視聽形象給予觀眾更多體驗式的感性認識,又以詩意化的鏡頭語言,賦予畫面更具多義性語義。
語言的局限性在于不能夠精確地將事物刻畫出來,而畫面能夠彌補語言的缺陷,將直觀的視聽形象呈現在觀眾面前。同樣在紀錄片創作中,人物內心世界的塑造,需要借助主觀鏡頭來外化。當導演無法從生活中提取素材表達時,便會在影片中利用主觀鏡頭完成超越現實的意象表達,通過對物像的選取到達內心世界的自然流露。在王沖霄導演的紀錄片《茶,一片樹葉的故事》中,“茶”不僅僅是中國文化的符碼加以存在,而且所承載的人情故事也涵蓋在作品當中。從茶的歷史出發,創作者講述了茶的分類、制作再到傳播的故事。借助“茶”這種意象,導演給予觀眾更多的感性認知,也許就是關乎故鄉之情、抑或是茶的人情所在。與其說王沖霄在講述茶的故事,不如說導演是借助“茶”來抒發自己內心的情感。紀錄片主觀鏡頭的運用,使得意象在畫面中的表達由感性層面上升到理性層面。在保持紀實的基礎上最大程度完成紀錄片的敘事,同時將茶所包含的詩意通過導演的主觀化表達,展現觀眾面前。
(三)聲音的表情達意
除了紀實、拍攝、剪輯等工作之外,聲音在紀錄片的詩意構建中,同樣承擔著重要的角色,
1. 聲音:傳達現實的詩意
聲音能夠輔佐紀錄片創作中詩意的表達。聲音是紀錄片創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與視覺注意力是伴隨在一起的,能有效地影響我們對于紀錄片的領悟與理解,觀眾可以僅僅依賴于其感受現實的詩意。紀錄片《美麗中國》中,風吹、鳥鳴、流水聲、勞作的聲音等等融為一體,憑借著聽覺上的享受,我們接收到寧靜致遠的生活信號,感受到了田園般的詩意生活。
紀錄片中的詩意傳達是通過聲音來界定的。聲音在紀錄片中的重要性不可否認,也是其詩意呈現的一個重要因素。在紀錄片《四個春天》當中,父母上山勞作所唱的山歌,不僅是貴州傳統文化的象征,更是父母娛樂消遣的方式。山歌通過攝影機的記錄呈現在畫面當中,我們通過聲音傳遞的情感與通透性判斷人物的狀態以及畫面的景別,在此處延伸了現實的詩意。
2. 音樂:詩意氛圍的渲染
著名美學家莫·卡岡認為:語言體現并傳達以理性為主的信息,而音樂能夠準確地體現和傳達以情感為主的信息。[5](P230)聲音和畫面的巧妙配合,能夠使得紀錄片的視聽語言更富有創造力與表現力。
音樂能夠烘托影片的情緒,奠定影片的基調。紀錄片《西南聯大》對于樂器的使用十分考究,運用西洋樂器作為背景音樂的部分較多。當大提琴與鋼琴出現,低沉的聲音伴隨著黑白畫面的呈現,將歷史的畫卷配合現代語境出現在故事當中,苦澀的回憶就以這樣一種詩意的方式展現在觀眾面前。當影片的畫面定格在西南聯大的學員回憶過去在學校出現的種種事情時,彩色動畫配合輕松愉快的管弦組樂器演奏,將我們帶到過去的那段生活里,給人以美好的感覺。
紀錄片中的音樂本身就是紀錄片內容的一部分。在張以慶導演的紀錄片《幼兒園》當中,一首主旋律音樂《茉莉花》多次響起,它或許是環境的渲染、兒童內心的真實寫照,抑或是導演的主觀性表達。音樂《茉莉花》貫穿始終,保持了影片的整體性,激發觀眾想象力的同時,呈現了真實的生活動態。
3. 解說詞:詩意的補充
解說詞在紀錄片創作中起著補充說明畫面的作用,同時也是其體系構成的重要組成部分。解說詞分為文字解說與旁白解說,文字解說在紀錄片創作中充當字幕,而旁白解說又分為評論性旁白、說明性旁白以及詩意旁白。
詩意紀錄片創作需要詩意旁白的配合,才能夠達到情緒的渲染以及情感的認同。觀眾通過優美的解說詞感受配音員的情緒變化,正是這種變化才能夠賦予創作獨特的蘊味,以期通過導演營造的情感認同,達到精神層面的深度交流。徐蓓導演的紀錄片《西南聯大》,其詩意模式,是通過旁白與畫面相互配合而來。該紀錄片的特色就在于詩意的解說,其提到了聞一多、沈從文、朱自清等人的經典文學作品,導演的解說詞參照原始文本加以配音員旁白解說,凸顯其中的詩意。中國導演徐蓓力圖在敘事的過程中,將解說詞作為表達的工具,將畫面中隱含的“詩意”提煉出來,讓觀眾不受直觀影像的束縛,更為深刻地理解感知紀錄片的“詩意”價值。
三、中國紀錄片詩意建構的審美變遷
隨著創作實踐的探索與發展,人們對于“詩意模式”紀錄片的需求與審美也在不斷變化。中國早期紀錄片由于受社會多種因素的影響,政治化色彩較為濃厚,強調宣傳性和思想性,創作題材單一內容同質化,缺乏藝術色彩。如今在紀錄片創作實踐的發展過程中,社會變遷和受眾變化對紀錄片審美傾向持續施加影響,使得紀錄片的“詩意”愈加被創作者尊奉為嵌入本體維度的圭臬和準則。
(一)從單一到多元的詩意表達
通過對中國紀錄片發展歷程的梳理,可以看到其創作在題材選取上的大致分類,即社會人文類、歷史文獻類以及自然地理類。中國紀錄片的詩意表達也滲透到這三種類別當中,其審美方式的變化也深受社會現實變遷的影響。
1978年改革開放時期到來,紀錄片意識形態的宣傳功能開始逐漸淡化,而其此時紀實主體則聚焦于山川、河流、長城等意象。這時期創作者旨在通過對祖國大好河山和人物的紀實影像,注入人文觀照以及創作者的情感表述。通過觀眾對主要對象或者載體的解讀,以期達到寄情于景、移情于景、情景交融的創作訴求。于是紀錄片的詩意也就在此基礎上結合鏡頭、解說詞等相互配合應運而生。如1983年拍攝的紀錄片《話說長江》,將“長江”作為貫穿始終的敘事載體,而當畫面定格在奔流不息的江水,激情飽滿地解說卻延伸了畫面的意境之感。長江在創作者與受眾心中不單只是河流,更是哺育華夏兒女、滋養土地、意喻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象征。這部紀錄片的“詩意”正是通過創作者對長江的歌頌吟詠傳遞給觀眾的。1992年拍攝的紀錄片《最后的山神》,呈現了鄂倫春族人孟金福原始的生活方式,向我們拋出對“消失的邊緣文化”的思考。創作者旨在通過作品的紀錄影像,保留文明進程中即將消失的薩滿儀式與信仰,并將一種對自然的敬重之情傳達給觀眾。
從1993年至1999年,紀錄片的創作主題立足于對“人”的思考。無論題材選擇,還是主題立意,都從“人”的角度出發。這一時期的紀錄作品更多表露出創作者的個人化傾向。陳曉卿導演的《龍脊》記錄了一個發生于廣西山區的故事。龍脊的資源短缺與惡劣環境,切斷了人們與外界的聯系。基于對現狀的客觀描述,攝像機將紀錄主體對準一群渴求知識的孩子,通過紀實將創作者對于孩子們的觀察展現在畫面當中。其中創作者隱匿自己在紀錄片中的觀點,對于所選對象進行客觀地拍攝、記錄、觀察,以更好地還原龍脊地區的現實生態。紀錄片這樣的處理方法賦予觀眾感性的認知,并在此上升至理性的思考,從而讓其更加關注“人”這個主題而產生情感上的共鳴。這個時期的紀錄片詩意從“人”出發,創作所追尋的真實性,就是其創作的美學基礎。
20世紀90年代前期,由于受中國新紀錄運動的影響,紀錄片的創作主題集中于社會人文方面。21世紀以來,紀錄片的創作再次回歸到紀錄本身,強調在紀實的基礎上尋求當時、當下與觀眾本身能夠產生共鳴的紀錄作品,所以其創作內容開始偏向于受眾的審美趣味。無論是《舌尖上的中國》《風味人間》《人生一串》等為代表的美食紀錄片,還是《國家寶藏》《我在故宮修文物》《如果國寶會說話》等為代表等人文歷史紀錄片。其創作風格都是在紀實的基礎上,通過創作者挖掘獨特的視角,并結合當下現狀做出的思考。隨之而來的是,觀眾與紀錄片娛樂根性的深度融合。紀錄片如果要進一步發展,那么就要在保持紀實的基礎上,繼續挖掘其“詩意”特質,這樣才能夠保留內在的深度和文化品質。正如“愛浦斯坦相信電影是表現詩意的最有利的手段,紀錄片作為影視藝術中的一個獨特品種,在 20 世紀 20 年代即產生了一種獨具美學風格的紀錄片類型——詩意模式紀錄片,而在之后的紀錄片創作實踐的發展過程中,對詩意的追求成為普遍的審美趣味和藝術自覺”[6](P123-127)。
從中國紀錄片的發展歷程來看,題材雖然逐漸由單一轉向多元,但主題依舊圍繞著“人”這個主體。紀錄作品試圖在客觀紀實的基礎上,將人、事、物以藝術化的形式來延伸其內涵,而其關鍵所在就是“詩意”的滲透,只有開拓紀錄片的詩意意境,才能夠使創作內容與時俱進,永葆生機與活力。
(二)由宏大敘事轉向日常生活敘事
隨著時間的推移,紀錄片的主體內容也在發生變化。從20世紀70年代末至20世紀90年代初,紀錄片的創作著眼于對整體的記錄,所以在此階段的紀錄作品內容,大都集中于山川河流、人文地理。創作者旨在通過寄情于景,抒發自身對祖國大好河山的仰慕之情。從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10年代初,中國紀錄片人的創作傾向于對普通人的記錄。紀錄片的記錄主體從整體到個體,通過“以小見大”的方式反映創作者的主觀意圖。21世紀10年代至今,中國紀錄片的內容建設不再局限于以上類型的探索,而是透過紀錄片這種藝術手段反映現實生活。
紀錄片創作的基礎是透過紀錄作品反映現實生活。紀錄片的創作應在記錄現實生活的同時,反映當下普羅大眾最為關心的社會問題。2017年,趙青導演的紀錄片《我只記得你》,雖然將創作的內容立足于“養老”問題,但卻以獨特的視角切入現實的一隅,反映了當下人們最為關注的“空巢”老人與患有“阿爾茨海默病”的生命個體的狀態。該紀錄片一經上映,就迅速引起公眾對于失智老人“專業照護”的關注與討論。樹鋒和味芳的故事,不再單純是一對老人的愛情故事,而是中國深度老齡化后不得不直面的課題——高齡老人的居家照護、醫養結合,養老制度等的探索和完善。[7](P22-24)該紀錄片的詩意,在于還原真實瑣碎的同時,融入真切的美好,讓我們感受到相愛相守、相互扶持的老年生活。
2020年,在紀錄片《人生第一次》的創作當中,導演選取了人生十二個重要的橫截面,反映其中每一個重要時刻。該片的主創曾在訪談上談及自己的創作初衷,明確指出現在人們更關心的是當下的中國、個體的命運以及和自己有共情的真實故事。所以其創作的內容緊緊圍繞著與人們相關的十二個“第一次”,而這些都是基于現實生活,其“詩意”的來源還是聚焦于“人”這個主題,“意象表達”被廣泛運用到這類紀錄片的創作中,所散發的詩意意境,往往易于引起觀眾的情感共鳴。
(三)受眾從文化接受到精神交流
紀錄片創作形式的探索,離不開創作者對于受眾審美習慣的研究。20世紀70年代末至20世紀90年代,紀錄片偏向于人文地理、歷史文獻等類型的拓展,創作者更為強調其文化輸出功能,旨在通過其視聽功能向觀眾普及人物、山川、河流等歷史文化信息。受眾經由紀錄片知識普及達到文化接受的效果。21世紀以來,隨著新技術的不斷發展,紀錄片的創作也在其影響下回歸紀實美學,使得其更為追求影像的美感。新技術為影像帶來了豐富的質感,并潛移默化影響了觀眾群體的審美。舌尖系列的紀錄作品以形式美、意境美、真實美涵蓋其中,為今后的“美食文化品牌”的紀錄片建構樹立了標桿。在不斷摸索的過程中,紀錄片的“詩意”也逐漸被熔鑄在作品當中。2017年以來,隨著短視頻的興起發展,紀錄片也在改變傳統的表達形式。在紀錄片《如果國寶會說話》中,導演迎合當代人的審美,開頭用年輕態的口吻,拉近觀眾與紀錄片的距離,而將文物的介紹壓縮至5分鐘,內容短小精悍,更適應互聯網時代碎片化的傳播方式,同時配合動畫技術,向更多年輕受眾介紹文物,打開歷史探索的大門。該紀錄片與之前的創作形式有所不同,它拋棄了紀錄片冗長乏味的解說,立足于紀實本身,根據大眾的審美習慣進行創作,正是對國寶背后故事的不斷挖掘,才得以將文物的相關信息,以全新的視角傳遞給受眾,拓展了其詩意所在,同時滿足了受眾精神層面的需要。
從20世紀70年代末至今,受眾的審美習慣一直在發生變化。觀眾群體主動由文化層面的接受者,轉為精神層面的交流者,這也是紀錄片創作發展的必然趨勢。
四、詩意紀錄片的人文關懷與哲學思考
詩意的紀錄片與其他類型的紀錄片有所不同,它在呈現客觀世界的同時,也將作者的主觀性表達、人文關懷與哲學思考,通過意象、意境、主觀鏡頭等多種藝術手段,隱藏在紀錄作品當中。
(一)人文關懷
紀錄片作為一種獨特的藝術文化產品,其“詩意”的根本,體現在是否真實地表現了普通民眾工作、生活等狀況,是否反映出較為深刻的人文歷史內涵。[8](P193)人文關懷的核心在于人為主體。與西方的人文主義有所不同,中國的人文關懷落腳于社會對人的關愛的層面上。張同道導演的紀錄片《零零后》歷時12年,在相同的時間跨度下,拍攝記錄了兩個孩子在不同教育方式下的成長與蛻變。影片著力表現了孩子們身體到內心的變化。在紀錄片中,男主人公池亦洋面對成長的煩惱,而經由家長與老師的引導找到興趣所在,并為夢想付諸努力,其與女主人公柔柔面臨生活的種種困難,而在成長道路上的自省,形成鮮明的對比。紀錄片中的男女主人公就是零零后孩子們的縮影,它旨在通過紀實的方式,引導觀眾正確對待成長中的挫折與困難,同時創作者希望通過這樣的紀錄作品,與受眾進行精神層面與文化層面的對話與交流。《人生第一次》第5集《上班》,將攝影機的記錄主體對準特殊人群,創作者旨在通過紀錄片這種形式記錄他們的生活,引導人們正確對待他人,學會尊重他人。紀錄片的人文關懷無處不在,創作者們堅守著以人為本的原則,通過紀錄作品的傳播,將這種“詩意”傳遞給了每一個觀眾。
除了以不同的紀錄語言觀照現實、傳遞創作者的人文關懷之外,紀錄片的人文精神,還表現在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紀錄片《南宋》《我在故宮修文物》《本草中國》等,以民族傳統題材為創作出發點,尋求中國文化在當代的新價值取向。紀錄片《本草中國》是一部與傳統工匠精神相關的紀錄片,其展現的是中醫傳承人對醫藥事業赤誠的愛。作品的形式采用了主題式分集的形式,每集圍繞一個既定主題展開,從現代人生活的角度出發,尋找符合內涵的相關中藥材。作品對于藥材從生長采摘炮制入藥全過程的精準復現,讓我們深刻領悟到每一味中藥背后是相關工作者付出的大量心血與無私奉獻。正是紀錄的力量,讓這些普通人的故事,能夠更為貼近觀眾的感受,激發情感的共鳴。
(二)哲學思考
紀錄片作為客觀世界記錄與反饋的一種藝術形式,在借助其藝術手段的同時,與現實世界形成觀照。其“詩意”的傳達,不局限于淺層的意象表達,而是更側重于觀者對于紀錄片本質的哲學思考。紀錄片的藝術價值,在于通過紀錄作品,建立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指涉建構。如《我在故宮修文物》《了不起的匠人》《匠心》《工匠精神》等作品,都都將“匠人”作為紀實的主體,讓觀眾感受他們執著、堅韌、精益求精的工作狀態和精神境界,也給給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創作者認為,紀錄作品背后折射出來的東西,才是紀實的真正內容,紀錄片導演旨在將“匠人精神”上升至每一個人價值觀的建構。
“對任何事物都要有清楚的認知”,這是哲學層面賦予紀錄片創作者的思考。在紀錄片的創作過程中,創作者有意將紀實的內容呈現在畫面當中,并向觀眾暴露問題所在。導演個性鮮明的主觀表達,雖引導我們理解與思考,但并不是將這種主觀性表達強加在觀眾身上,而是導演賦予觀眾對于現實判斷的能力。杜佳唯導演的紀錄片《美麗中國》,在令觀眾欣賞祖國的清水綠岸、藍天白云等美好事物的同時,也毫不諱言地披露了生態環境污染、空氣污濁、水土流失等問題。并在作品中提出,只有走“生態文明之路”,提高每位公民的環保意識,才能夠達到人與和諧自然共生的狀態。紀錄片創作者一直在創作的過程中,賦予作品一定層面的哲學思考,正是這些留白,給予了觀眾對于現實生活的反省之力。
對于紀錄片的詩意構建,不應只停留在創作層面,還應深入思考以何種方式把握其本質。紀錄片作為一種藝術表達方式,所堅守的觀念與本質就是“真實”。紀錄作品應本著紀實的原則,進行藝術創作,有些紀錄片的創作過分追求精美的場面調度、優美的畫面、詩意的解說詞,雖讓其表現得更加具有藝術氣質,但這些看似“詩意”的創作,卻忽略了紀錄片的記錄本性和“真實原則”,反而不利于其構建,更會凸顯虛假。這種現象的出現,應讓今后的創作者產生警醒。那么如何將紀錄片中的“詩意”與“真實”完美融合在一起,既反映當下的現實生活,又能夠站在一定的高度進行反思與批判?這就要求紀錄片的創作者還應具有一定的哲學思維,將孤立的事物聯系在一起,由此紀錄作品就不僅僅承擔了紀錄現實的功能,還能夠在觀眾群體觀看時候,引發自身對于現實的思考,這也是紀錄片透過創作實踐,實現詩意建構的根本所在。
結語
中國紀錄片創作的詩意建構,離不開文學與詩歌賦予的寫意特性。同時我們還應在紀實拍攝的基礎上,挖掘詩意化的影像表達。只有不拘于紀錄片淺層的“意象表達”,才能夠讓紀實和影像體現出深層的詩意。同時詩意化紀錄片創作者,也應避免刻意營造詩意,而違背紀實的原則,進行作品創作。只有真實與深刻融合于影像的客觀表達中,才能夠將紀錄片的“詩意”,通過人文關懷與哲學思考得以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