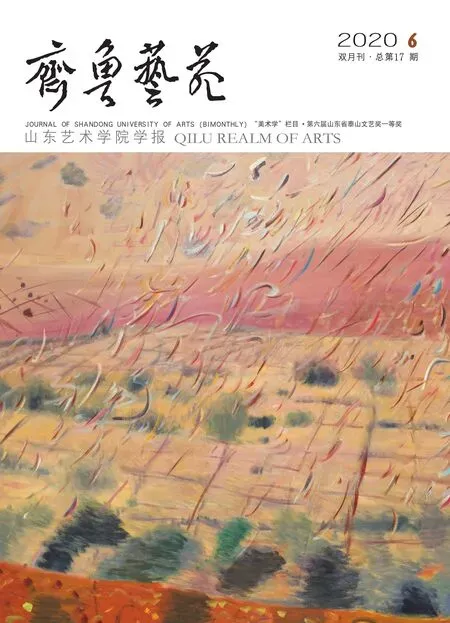中國傳統美學的現象學還原
——兼論現象學視域下的中國美學話語體系建構質料
桑東輝
(黑龍江大學哲學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80)
現象學還原是德國哲學家胡塞爾提出的一個重要的哲學方法論。其核心是將“一切評價的態度,一切有關作為主題的人性的,以及人的文化構成物的理性與非理性問題”全部排除掉[1](P16),恢復被認識事物“實在的內在”。運用哲學方法對中國傳統美學進行現象學還原,不僅有利于祛除附加于中國美學之上的林林總總依附物,還中國美學精神的本來面目,更精準地把握中國美學本質之絕對的、明證的被給予性,而且還可為建構中國美學話語體系提供質料。本文中的質料一詞也是從胡塞爾現象學意義上講的,意指規定著中國美學精神的最原初、最基本的東西,具有立義意義(Auffassungssinn)。因此,這種質料某種程度上就是所謂的立義質料(Auffassungsmaterie)。
一、對中國傳統美學的現象學還原
按照胡塞爾的現象學原理,絕對的被給予性是一個存在之物作為此物(Diesda)被給予的,而不是夾雜著各種前科學的、科學的、人本的等對被給予之物真實意義的超越認識。在胡塞爾看來,所謂現象學還原就是“將所有有關的超越都貼上排除的標記,或貼上無關緊要的標記、認識論上無效性的標記,貼上這樣一個標記,這個標記表明:所有這些超越的存在,無論我是否相信它,都與我無關。”[2](P37)或者說是一種“加括號”的方式,將科學的、人文的成見放入括號中,存而不論。胡塞爾認為,只有通過現象學還原,“才能獲得一種絕對的、不提供任何超越的被給予性。”[3] (P40)胡塞爾現象學還原思想為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包括中國傳統美學精神提供了一個有益的視角和工具。
在當今中國學術界,嘗試運用西方哲學方法特別是運用現象學原理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現象學還原的,當推鄧曉芒。在《哲學研究》2016年第9期上,鄧曉芒發表了《論中國傳統文化的現象學還原》一文,對中國傳統的人生觀和世界觀,以及中國傳統文藝和語言進行了現象學還原。按照鄧曉芒的觀點,遮蔽中國傳統人生觀和世界觀不是“非人的科學邏輯,而是人性本身的特化和固化形態”,是倫理方面的問題,因此他主張“把自古以來一切天經地義的倫理預設置于括號中存而不論”。而對文學藝術,鄧曉芒認為實際上中國傳統文化自身就一直在進行著文學藝術層面的現象學還原,因此,對體現“美”的方面之文學藝術,他是抱有某種“具體繼承”的欣賞態度。[4](P35-42)
筆者對鄧曉芒先生運用現象學還原理論分析中國傳統文化的思路和實踐是認同的,也基本認可鄧先生對中國傳統人生觀、世界觀的現象學還原嘗試,但對于文學藝術特別是美學方面的現象學還原,筆者認為還有進一步深入探討的必要。在筆者看來,中國傳統美學精神雖然相對于人生觀、世界觀而言,往往更接近于其自身被給予性,但受中國傳統文化的諸多影響,其中亦附加著大量需要排除和廓清的依附物,積淀著大量應予超越的“超越之物”。概言之,主要應從三個大的方面,對附著在美之存在物上的宗教的、政治的、倫理的等人本觀念加以祛除和剝離。
一是將美與宗教(巫術)剝離。從藝術起源上看,最早的藝術是與原始宗教包括體現原始宗教和原始崇拜的原始巫術,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在有關藝術起源的諸種說法中,巫術說在20世紀的藝術學理論界占據一定地位。在列維—布留爾看來,原始人思維是混雜著互滲律、聯想律等神秘觀念在內的原邏輯思維。在這種原始思維下,藝術的美被原始宗教和巫術所遮蔽。布留爾列舉了巫師木像的例子。在羅安哥,雕刻有巫師形象的木頭雕像,被引進“力量”后,由徒弟們帶在身邊,以便在巫師生前或死后行巫時使用。以此來說明肖像在“物質和精神上”和它的原型同一起來,主要是“因為傳統的集體表象給肖像的知覺以及給原型的知覺帶進去的是同一些神秘因素。”[5] (P40)克萊夫·貝爾也認為藝術和宗教都是人類感情的表現,藝術所表現的感情“正是五花八門的宗教信仰中最有生命力的力量。”[6](P62)在中國本土的傳統文化中盡管宗教性不強,但在中國上古史時期,學界普遍認同于大致經歷過一個巫史時期。學術界大多認為,傳說中的氏族部落首領很多都是最早的巫師。如大禹就是巫師,有研究者提出史籍記載的所謂“禹步”實際是一種類似薩滿舞蹈。又如,很多出土的器皿和圖案都不是從藝術的角度來表現,而實際或是出于宗教巫術儀式需要,或是原始氏族部落的圖騰。如仰韶文化早期墓葬中出土的蚌殼鋪就的龍虎圖案就是有關巫術的。隨著顓頊時期發生“絕地天通”的重大變革,中國古史由全民巫史進入到世俗社會。此后,原始宗教信仰和巫術崇拜被作為明明在上的“天”而成為指導人類社會的“道”。現實的人類社會生活進入到世俗的人倫日用。盡管隨著中國上古社會的發展,巫史時代被世俗社會所取代,但原始宗教和巫術仍以祈雨、禳災、厭勝、蠱毒等不同形式存在于民間。
針對中國上古時期藝術與宗教的復雜關系,運用現象學還原來剝離美與宗教(巫術),首先就要澄清哪些是美的絕對的、被給予性,哪些是非實在內在的、被原始思維所附著的超越之物。正如法國諾克斯洞穴一萬多年前壁畫中所表現的被矛刺中、被箭射中的野牛并非完全是藝術作品而是兼具藝術和巫術意義一樣,山頂洞人將佩戴的石珠和魚骨染成紅色,也不僅僅出于審美的需要,而具有魔法辟邪的巫術意義在其中。[7](P7)以現象學還原方法來審視藝術起源,與其說藝術與原始宗教糾結不清,毋寧說原始巫術滲透和附著于原始藝術之上。還原的目的就是要將原始思維中的交感、通靈等神秘巫術附加在藝術作品(壁畫、飾物、祭祀禮器等)和藝術形式(如體現原始生殖崇拜具有性暗示的舞蹈以及雩舞等祈禳舞蹈和祈求五谷豐登的“葛天氏之舞”)上的超越之物剔除出去,存而不論,從而恢復原始藝術對美的本質追求。也就是說,盡管山頂洞人以紅色涂抹飾物更多的體現一種巫術意圖,但不可否認其中已經具有朦朧的審美意趣和價值追求。
二是將美與政治剝離。中國上古時期結束巫史時代后,就進入一個政教分離的時代。盡管在中國古代歷史中,封建帝王始終強調“君權神授”,并每逢朝代更迭、改元正朔、乃至新帝繼位都會行封禪大禮和祭祀天地、山川、日月等神祇,但那只不過是為自己的統治尋找宗教意義上的合法性。同時。儒家也強調祭祀祖先,主張“祭神如神在”,但根本點也是為了通過神道設教形式來闡揚孝道,以施行“孝治天下”的治理手段。因此,整體來說,中國古代社會是一個政教分離、并以政治統治為主宰的社會治理形式。在這樣的社會中,藝術不可避免地被打上政治的烙印。最能體現政治對藝術的附加和影響的莫過于對“中”的崇拜。中國、中原等詞已經表達了一種“尚中”的文化意蘊。即便是今天,河南方言中的“中”也無疑是中國傳統尚中觀念的遺存。武王滅商后,由于周人政治文化中心在今天的陜西,因此其定都西部的豐鎬。但對東部中原一帶缺乏有效的管控,從而滋生管蔡聯合武庚的叛亂。周公平定武庚叛亂后,選址建設東部政治文化統治中心,就是采取土圭測天下之中而立城的辦法,最終測得天下之中,建造了成周洛邑。《逸周書·作雒》載:“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這個“土中”就是《周禮·大司徒》所說的“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的方法得出來的。周公營洛邑的目的就是居中以制天下四方,并為四方諸侯所拱衛。《漢書·地理志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為在于土中,諸侯藩屏四方”。這種地中崇拜在上古政權建立中是很普遍的。就像《呂氏春秋·慎勢》所說的,“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其實,尚中的政治學意義在更遠的上古時期或許就已經出現了。考古學家唐蘭先生考證后指出,“中”原指旂旗旐等,最初是氏族社會的徽幟,上古時用來集合人眾。“蓋古者有大事,聚眾于曠地,先建中焉,群眾望見中而趨附,群眾來自四方,則建中之地為中央矣。”[8](P52-53)此說在甲骨文中亦多有印證,同時也得到甲骨文學者徐中舒先生的認可。有研究者認為“中”最早來源于原始社會普遍存在的“神秘中桿”,是古代巫師通天之“宇宙樹”和“中柱”的符號化擬象物。[9](P32)而隨著中國由原始氏族社會進入到階級社會,這種由“神秘中桿”所演化來的“建中”“中旗”等尚中習俗逐漸變成一個權力的象征符號。隨著天子、帝王、君主等等級制度的強化,尚中的思想逐漸成為一種政治語言。如以九五之尊來指代君權和君位。五在《易經》中處于上卦的中爻,《易經》是尚中的,中爻往往是吉祥的,《易·系辭傳》所謂的“二多譽”“五多功”就是肯定中爻的。以九五來比喻帝位凸顯的就是中的權威價值。舉凡世間萬物都與中相關聯,也都相應地被賦予政治上的意義。如土在金木水火土五行中居中,色彩中以黃色代表中,《易·坤·六五》所謂“黃裳元吉”。因此,帝王的服飾都尚黃色,而一旦“黃袍加身”就等于榮登九五。
其實,在尚中問題上也最能體現藝術與政治的關聯。這種尚中的政治文化首先從建筑、服飾、御輦、禮制等方面滲透到藝術審美層面。如古代城市規劃設計講求“中”,特別是皇宮內城更嚴格要按照中軸線對稱設計。如北京的天安門、鐘鼓樓、萬歲山、太和殿等都是一條南北縱貫的中軸線上。其他建筑都圍繞中軸線對稱布局,如南有天壇,北有地壇,東有日壇,西游月壇。除了建筑,書法、繪畫的布局也講求對稱與和諧,但在書法、繪畫中的尚中和對稱有時候不是絕對的、僵化的“取中”,而是強調的輕重、虛實、均衡、靈動中的“中和”。同樣,音樂方面也非常重視“中”。在宮、商、角、徵、羽五音中,宮為中,為君,其對應的是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土,東、西、南、北、中五方之中,此皆處中位,故而宮為五音之君。中國傳統音樂也非常強調“中和”,這點可以從《荀子·樂論》、《禮記·樂記》、以及嵇康《琴賦》等音樂論述中得以佐證。在古人看來,只有中才能和。以上,我們以“中”為例,運用現象學還原原理,層層剝脫附著“尚中”這一審美價值之上的政治色彩,即祛除尚中所具有的帝王權力等政治符號意蘊,以期還“中”以藝術美的本來面目。
三是將美與倫理剝離。中國傳統文化是以儒家為主導的。傳統儒家強調的是仁義禮智信等道德意蘊,追求的是修齊治平的政治理想。如果說西方文化的本體基礎是形而上學的思辨,那么,中國傳統文化則是一種倫理型的文化。在儒家為主的倫理文化觀念主導下,天地萬物都要與倫理聯系起來。譬如,圍繞天人關系這個基本問題,中國古代很早就產生了“天人合一”的觀念。在《周易》構建的天、地、人三才結構中,人居其一。天地之道是為了人道服務的。因此,仰觀俯察目的都是要為人倫日用服務。所謂“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的根本規律是道德,而天地的道德是生生不息。所以,人倫日用首先要立足于人的生存和發展。甚至于天道和天命也同人類社會一樣存有好惡的擬人化傾向。如在小邦周剪滅大邑商的過程中周人就從天命改易的角度注意從意識形態上顛覆和變革原有的天命觀。在姬周以前,殷商時期的天命觀是天命不易說。在時人看來,殷商的祖先死后都變成上帝神,來庇佑殷人。所以殷商帝王對自己的統治很自信,自言:“我生不有命在天”(《尚書·西伯戡黎》)。而弱小的周部落要打敗殷商統治,首先就必須為自己尋找政治上的合法性。為此,周人提出了“天道無親,惟德是輔”的天命改易思想,不僅徹底顛覆了商人的天命不易說,而且將天命所歸定位在德上,從而確立了以周代商的合法性,并一舉奠定了中國倫理文化的價值取向。
重德的倫理文化不僅立基于政治領域,而且還全面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文學藝術等領域。在文學、藝術領域,中國傳統倫理文化的主基調是提倡倫理與美的結合,所謂“盡善盡美”。在孔子看來,武樂徒具藝術形式的美,而由于其暴力殺伐主題造成內容上的倫理缺陷,故而“盡美矣,未盡善也”。只有韶樂體現了倫理與美的統一,達致盡善盡美的最高境界。在傳統文化中,藝術往往作為倫理的教化工具和手段。在這方面,“樂者通倫理者也”奠定了傳統樂教思想的主基調。傳統音樂的功能被儒家定格于倫理教化功能。《荀子·樂論》所謂音樂具有“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的移風易俗作用,能收到“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的效果。這一理論在《禮記·樂記》中也有基本類似的表述。以音樂為例,運用現象學還原理論,我們不難發現,音樂是由聲、音、律等音聲旋律與人心相關作用而成的。在音樂產生過程中,人的心靈感官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禮記·樂記》所謂“音者,生于人心者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至于音樂所謂的“善民心”“以道制欲”的音樂教化和移風易俗功能都是倫理文化設計者后天人為比附上的。經過揭去這些后天人為貼上去的“標記”,去除這些“括號”里的內容,就能發現音樂“實在的內在”,發現音樂自身、原初所具有的“絕對的、明證的被給予性”。這種明證的被給予性其實就是音樂作為人情感表達而由人心所創作和感發的本然狀態。
二、現象學還原的中國美學回歸本真之路
盡管我們借助西方的現象學原理,采用現象學還原的方法,從宗教(巫術)、政治、倫理文化等方面嘗試祛除附著在文藝美之上的“超越之物”,以實現對美的內在本質之再發現。那么,我們如何達致美實質的內在?或者換句話說,我們經過現象學還原后的中國美學如何才能回到其本真狀態?筆者認為,路徑主要有兩條:回歸日常生活;回歸生命本體。
一是回歸日常生活。回歸日常生活也是現象學和實踐哲學、文化哲學的共同趨向。本文既然是以現象學理論來檢視中國傳統美學精神,那么,在此,筆者就側重介紹一下胡塞爾現象學對生活世界的理解及其對中國美學精神的影響。胡塞爾是從對歐洲科學危機的自覺反思而開始關注日常生活,構建其現象學理論大廈的。在胡塞爾看來,歐洲的科學主義(特別是實證主義)以及人本主義等已經遮蔽了生活本質,引起了深刻的文化危機,事實上,也造成了人的生存方式的危機,引發存在危機。所謂只見事實的科學造成了只見事實的人,從而忽視了人生有無意義的問題。也就是說,歐洲的科學主義特別是實證科學割裂了人的存在意義,悖離了人的“生活世界”。在胡塞爾看來,實證主義構建的世界缺乏給定性,而相反,被實證主義拋棄的生活世界是具有先在的被給定性的。生活世界的這種被給定性是邏輯在先的,而不是時間在先的,是原初的、本原的、根本意義上的在先。只有這種“直覺地被給予的”、“前科學的、直觀的”、“可經驗的”生活世界才是人的存在領域。在胡塞爾看來,“生活世界是自然科學的被遺忘了的意義基礎”。不僅如此,生活世界也是一切的意義基礎,是創造一切的意義基礎,同時也涵蓋了人的一切創造,所謂“盡管人屬于它的先于一切目標的存在,我們當然知道,人是有目的的,人的一切創作當然也屬于生活世界。”[10](P1088)無疑,文學藝術作品,乃至一切審美對象的創作都是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應該說,胡塞爾的生活世界理論對其后的文化哲學和實踐哲學產生極大的影響,同時也對美學思想提供了思想武器。
在哲學領域,胡塞爾現象學理論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具有很多理論視域上的交叉和融通,同時又有著一些本質區別。這種思想上的關系體現在藝術學和美學領域,則表現為對人的日常生活和勞動實踐價值的認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藝術起源說,最早的藝術起源于人類勞動。正是在勞動生產中,人類才產生了最早的原始藝術。多地發現的原始壁畫常見到原始人獵捕動物的場景,是藝術對現實狩獵生活的記錄和再現。出土的古代陶器、青銅器,最初不僅是作為禮器,更主要的還是生活用具。原始人的建筑更是主要用于日常居住。隨著人類社會實踐的不斷深入,日常生活中的內容被賦予了藝術化的表現形式。譬如,陶器、青銅器的制式和紋理不再僅僅是滿足于現實物質功用,而且具有了精神愉悅的作用。即便是被儒家津津樂道的音樂倫理之和諧境界,實際上也是始基于日常生活的飲食調味。譬如,《國語·鄭語》記載史伯論述和的觀點,即“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在這里,和是對自然萬物的雜糅,是生活百物的基礎,首先就是飲食味道的調和,其次才涉及身體和音樂等。晏子繼承了史伯的思想。據《左傳·昭公二十年》載,在論述君臣之和時,晏子特意舉了音樂之和的例子,認為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等這些要素的相和相濟才成為音樂,故而,“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而君臣、音樂之和最初都是來源于日常生活中的調味之和。所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同理,“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這種音樂之和產生于日常生活的觀點,一定程度也印證了胡塞爾的生活世界理論,為美的回歸指明了方向。
按照胡塞爾現象學的生活世界理論,客觀的生活世界是不夾雜著任何非給定性的先驗的世界。具體對于中國美學精神而言,也要回歸原初的本真的日常生活世界,祛除掉宗法禮制、儒家道德教化等層層附加于其上的非本質性、非給定性。現象學的這種思想觀念也對實踐美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按照實踐美學的理論,實踐是人的本質。同時,美是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因此,一方面審美產生于實踐;另一方面,實踐本身具有審美意味。日常生活作為人的最基本實踐活動,是審美活動所賴以存在的基礎。
二是回歸個體生命。胡塞爾的生活世界理論沒有停留在僅僅完成對實證科學的祛魅和對生活世界的回歸上,而是進一步明確了生活世界的主體性和主體間性,并落實了人在生活世界中的個體生命。在胡塞爾看來,現存生活世界的存有意義是主體的構造,是經驗的,前科學的生活的成果。世界的意義和世界存有的認定是在這種生活中自我形成的。每一時期的世界都被每一時期的經驗者實際地認定。也就是說,世界的存在,包括日常生活世界的存在,并不是自在的第一性的東西。事實上,自在的第一性的東西是主體性。因此,胡塞爾認為要真正理解客觀真理和現實世界,必須“徹底地追問這種主體性”。在高揚生活世界中人的主體性的同時,胡塞爾還進一步將眼光投射到他者身上,認為作為自在的第一性的主體性不是孤立的,而是交互的,是我與我之外世界和他者之間形成的交互主體性。因此,這個作為給定性的先在的生活世界實際上也就是一個交互主體性的世界。胡塞爾曾經發問道:“當我這個沉思著的自我通過現象學的懸隔把自己還原為我自己的絕對先驗的自我時,我是否會成為一個獨存的我(solus ipse)?”[11](P150)對于這個問題,在胡塞爾有關意向性闡釋中就能夠得出答案。在他看來,在意向性中,他人的存在就成了為我的存在。應該說,胡塞爾把生活世界界定為主體間性或交互主體性的世界,在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其不僅對于20世紀文化哲學和實踐哲學產生了重大理論啟迪,而且對實踐美學、生命美學等也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價值。
一方面,從某種意義上講,藝術是人的個體生命的沖動。作為主體,個體生命的沖動必須建立在實踐活動的基礎上。但歸根結底,藝術也好,審美也罷,只有回歸到生命本體,才能實現對附著于其上的他律性超越之物的祛魅,回歸藝術自律的實在內在。另一方面,藝術又具有一種參與性,是創造性與觀賞性的結合。也就是說,在美學領域不僅要有人的主體性的在場,同時也要有參與審美的主體間性的存在。按照胡塞爾的意向性理論,他者的存在成了為我的存在,我的存在離不開他者,同時他者也不能離開我而存在。應該說,運用意向性理論將人的主體性和主體間性引入到生活世界中,是胡塞爾現象學的重要貢獻,同時對美學特別是審美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價值。盡管胡塞爾的生活世界仍然沒有跳出先驗論的誤區,但“生活世界對主客對立的對象性思維的摒棄、對現實對象壓迫人的世界的反動極大地影響到人們對藝術審美功能的認識”。這種生活世界理論應用到藝術世界中,則極大地高揚了人的主體性。人可以充分發揮其審美主體的自由想象能力,從而擺脫掉世俗的功利性束縛,擺脫對象性關系的束縛,達致人的自由,實現對藝術和美的自由追求。在胡塞爾的理論體系中,“藝術的這種對現實的對象化思維的摒棄、對現實世界的超越與生活世界理論旨趣是一致的。”[12](P10-14)無論是文學還是藝術,抑或是審美,盡管都植根于日常生活中,但更為重要和根本的是,都離不開個體生命,離不開人的生命本體。也就是說,實踐只是美學的基礎,而美學的根本與核心最終還是要落在個體的人身上,是個體生命所展現出來的美的意趣。
胡塞爾的現象學特別是他有關生活世界、意向性、主體間性等理論,對其后的美學和藝術思想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如蓋格爾運用現象學方法研究審美享受;海德格爾受現象學啟發創建了存在主義哲學,開創了接受美學的先河;薩特和梅洛·龐蒂都受到胡塞爾的想象與知覺理論影響而提出了各自哲學和美學思想體系。此外,英伽登和杜夫海納也都將胡塞爾的意向性理論用于藝術分析和審美判斷。[13](P12-17)應該說,胡塞爾的現象學不僅產生了現象學美學,而且對存在主義美學、解釋學美學、實踐美學包括后實踐美學等都有重大的理論借鑒和推動作用。
三、現象學視域下的中國美學話語體系建構質料
如前所述,本文所采用的質料概念并非是亞里士多德、康德哲學中的質料,而是現象學大師胡塞爾所說的質料,即決定事物本質的立義意義。構建中國美學話語體系,不僅要進一步明晰和完善相關概念、范疇、形式等,首要的是要明確對中國美學精神具有內在規定性的質料。某種程度上,如果說美學范疇決定了文學藝術作品的風格和品次,決定了審美的旨趣,那么,質料則是規定著文學藝術的美學特質和審美旨趣,質料是范疇后面的決定性因素,是中國美學精神的決定因和區別于其他地區、其他民族美學精神的根本因。關于中國美學話語體系建構中的質料,筆者認為主要包括道、神、心。
1.關于道。道是中國文化的基本概念。儒釋道包括墨家、法家、雜家等先秦諸子百家幾乎都講道,而且無一不推崇道。盡管各個思想流派和眾多思想家都將道推至到無以復加的崇高地位,但對于道的界定和言說卻彼此迥異,各不相同。即便就是一個儒家而言,其對于道的闡述也不盡相同。既有天道,也有天地之道,還有人道。既從境界說的角度,講“極高明而道中庸”,又從修養論的角度,談“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從文藝學的角度,更是提出“文以載道”的使命和責任。儒家的道來源于《易經》,強調“一陰一陽謂之道”。并提出“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儒家的道器說,主張道以制器,強調“從容中道”的中和特質。道家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是講道最多的。這不僅表現在道家學派也好,道教也好,都有個“道”字,也不僅在于老子的著作名為《道德經》,更主要是道家特別是老子對道的形上特質進行了深刻思辨和高度概括,并將無確定為道的本質特點。所謂“道可道,非常道”。道是老子思想的核心范疇,是“玄牝之門”,“眾妙之門”。在老子看來道的本質是自然,是無為。強調“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那么,圍繞建構當代中國美學話語體系,筆者認為必須繼承和發揚傳統文化資源,將中國傳統文化中“道”的精神內涵融入到藝術和美學精神中,使之成為規定和指導美學范疇概念的立義意義,成為構建美學話語體系的基本質料。在今天,繼承和發揚傳統“道”的精神,必須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一方面,將儒家道論中的中道、中和等思想與道家道論中的自然、無為等思想結合起來。另一方面,將傳統文化中的道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結合起來,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道與中國美學緊密結合起來,使之成為中國美學的指導思想,并以之作為全球美學話語體系中的中國元素和中國方案。
在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對于道,很多美學研究者將其歸之于美學范疇,認為道與意境、風骨、神韻、意象等都一樣屬于美學范疇。但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道的地位和性質十分特殊,道往往是產生意境、風骨、神韻等美學范疇的思想來源和精神淵源。也就是說,在美學理論體系中,道與一般的美學范疇不是一個層次。道不僅在層次上高于這些美學范疇,而且處于中國美學精神的最高層次,甚至在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中,道也高居頂峰。故而,也有學者看到了將道與美學范疇混列一排的尷尬,而將道界定為中國美學的元范疇。[14]但即便這樣,道仍屬于美學范疇中的組成部分。而事實上,按照《周易》有關道器關系的辯證思想,美學范疇相對于道而言,都是屬于器的層面。只不過相對于具體的文學藝術作品而言,這些美學范疇又具有一定層級的“道”的屬性。因此,作為具體的美學范疇,意境、風骨、神韻等等是具有雙重角色的。相對于文藝作品而言,其是“道”;而相對于中國文化根本精神的“道”而言,它們又都是“器”。是受“道”制約和規定的。
相對于美學范疇和藝術形式而言,只有絕對的、明證的被給予性才是最根本的質料。而不加任何修飾詞的“道”無疑最具有這種絕對的、明證意義的被給予性。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只有道是高高在上,代表著宇宙及萬事萬物的根本規律。這個根本的道有時也被冠以道、天地之道來言說。代表著世界根本規律的天道或天地之道可以作為道的另一種表達。但如果這個天道與正義等倫理精神結合一起則不再是絕對的被給予性,作為質料就會大打折扣了。至于其他的王道、君道、臣道、婦道、孝道等就更是加括號的所謂“超越之物”,也就沒有資格成為規定中國文化精神的基本質料,就更別提對中國美學精神的質料意義了。相對于美學領域而言,所謂的書道、茶道、畫道、琴道、文道等,無疑是對道的類型變異,其對具體美學領域而言,具有質料的特點,是屬于道這一根本質料下的子質料。
2.關于神。盡管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也不乏鬼神觀念,但從深層意識上講,中國傳統主要還是泛神論,乃至無神論,而對于神的界定,也往往是非人格神,這點是中國與西方在對神的理解上的主要不同之處。《易傳》解釋神的概念是“陰陽不測之謂神”。而孔子更是直言“祭神如神在”,一個“如”字無疑已經挖掉了神實有的根基。實際上,以孔子為主的儒家思想是不語怪、力、亂、神的,對神是置而不論的。不僅是儒家,對中國藝術美學精神影響至深的道家也對神不肯多談,即便是《莊子》中提到眾多傳說人物,莊子也不以神明視之,而只是為了借他們表達其自然無為的思想。在民間觀念上,中國人對神也是敬而遠之的。明白了上述道理后,我們就會清楚,盡管在中國傳統藝術范疇中,多次提到與神有關的概念,但這里的神都不是作為人格化的神明,而是指代一種不可言說、難以界定的內在精神。這種精神具有現象學所謂的先驗性,具有邏輯在先的給定性,是不證自明的藝術美學精神。
與道一樣,神在中國美學話語體系的建構中,也具有基本質料的屬性。道作為基本質料,與相關藝術形式結合,從而形成了藝道、書道、畫道、茶道、琴道、舞道、劍道等。同樣,神也作為一種基本質料,因其表現形式的不同,而形成了神韻、形神、暢神等美學范疇,而諸如意境、空靈、風骨、飄逸、逸格、氣韻等亦不乏道和神等精神特質。無論是書法中的筆斷意連、還是繪畫中點睛的神來之筆,抑或散文中的形散而神不散等都是強調的是“神”這樣一種文藝美學精神。總的看,神主要針對的是視覺藝術所要表現的美的本質。特別是在老莊及玄學影響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繪畫藝術在道的精神下,更注重對神的表現和追求。因此,顧愷之“以形寫神”的傳神論、宗炳“萬趣融其神思”的暢神論等繪畫理論都出現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這一時期確立的重神的畫論觀念也影響了此后直到今天的中國畫創作和欣賞。如杜甫在《丹青引·贈曹將軍霸》中,稱贊曹霸畫馬時也著重描寫其傳神之處,所謂“將軍善畫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真”。
一方面,在藝術美學上的神主要是一種自然和外在于人的本質。如鬼斧神工、自然天成所表現的都是陰陽不測、非人力可為的神妙境界。同時,另一方面,神又是藝術所極力要予以表現和表達的。因此又是藝術家這個創作主體所要追求的藝術效果。神來之筆、傳神之作都是對優秀藝術作品的最高贊譽。盡管在中國文化精神體系中,神不及道,但仍屬于質料層面的,是規定者美學特別是視覺藝術、造型藝術基本精神的立義意義。盡管中國美學中的“神”具有先驗的神秘色彩,但卻是作為一種基本質料,是達致道的重要途徑,所謂以形寫神,暢神才能體道,才能傳道。
3.關于心。如果說神主要是針對視覺藝術而言的質料,那么,心則主要針對聽覺藝術而言的質料。《孟子·告子上》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耳目盡管都具有各自的功能,但都要受心的支配,只有心能思維,能激發情感。《管子》亦有“心之在體,君之位也”的說法。既然心是思維的主要器官,那么,相對于藝術而言,心也具有質料的作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儒家所談論的心不是僅僅作為知覺器官而言,亦不是感性的心,而是作為道德本體的心。這樣的心無疑是胡塞爾所謂加了括號的,需要我們擱置不論的。而作為中國美學質料的心則是作為知覺的心,是思維的心,是對文學藝術特別是音樂之美的情感呼應。關于音樂與心的關系,從古至今一直不乏論述。前面所引述的《禮記·樂記》中“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就已經關注音樂和人心的關系。此后,嵇康的《聲無哀樂論》更是將音樂與人的情感以及喜怒善惡的關系進行了界說。在當今學界也一直圍繞音心論進行討論,有的學者認為音心可以對映,有的反是。
事實上,作為思維器官,心不僅統攝著眼、耳、鼻、舌、身等器官和肢體,而且綜合人通過各種感覺器官所抓取的色、聲、香、味、觸等信息,從而產生認知和情感。以音樂為例,無論是演奏者還是欣賞者都需要用耳朵去聽,用心去體會,因此,往往更集中在抓取音聲的器官——耳和最后合成知覺和情感的器官——心上。有時候,為了不目騁神馳,甚至要閉目聆聽。這也就是為什么調律師往往是盲人,為什么古代的很多樂師也都是盲人的原因。《國語·周語上》所謂“瞽獻曲”。春秋時期的晉國樂師師曠據說就是為了更好地專精于音律而自殘其目的。王褒在《洞簫賦》中特別描繪了盲樂師演奏的情景,所謂“夫性昧之宕冥,生不睹天地之體勢,暗于白黑之貌形性”,這樣可以排除外界干擾,專心致志地感受天地精神,融入于音樂之中,收到“愍眸子之喪精。寡所舒其思慮兮,專發憤乎音聲”的藝術效果。從本質上看,音樂更多的是心靈的感悟,是情感的表達。而這個情感在主體性上是創作和演奏主體的思想表達。但在審美角度而言,從聽者的角度上,又存在一個音與心之間的影響關系。在這點上,古代就有所分歧。按照傳統儒家樂教理論,音樂具有“感人也深,化人也速”的“移風易俗”的教化作用,所以王褒在《洞簫賦》中極力夸大音樂的教化功能,所謂“貪饕者聽之而廉隅兮,狼戾者聞之而不懟。剛毅強燭反仁恩兮,啴唌逸豫戒其失。鐘期牙曠悵然而愕兮,杞梁之妻不能為其氣。師襄嚴春不敢竄其巧兮,浸淫叔子遠其類。嚚頑朱均惕復惠兮,桀跖鬻博儡以頓顇”。但嵇康卻不十分認同這種儒家提出的主流音樂美學觀念。在《聲無哀樂論》中,嵇康提出音樂的本質是自然的,所謂“音聲之作, 其猶臭味在于天地之間。其善與不善, 雖遭濁亂, 其體自若而無變也。豈以愛憎易操, 哀樂改度哉? ”至于人的音樂情感則人心的作用結果,所謂“心動于和聲,情感于苦言”。具體而言,就是“夫內有悲痛之心,則激切哀言。言比成詩,聲比成音”。說穿了,就是“哀心藏于苦心內,遇和聲而后發”。我們如果用胡塞爾現象學來分析,不難看出,儒家的樂教思想無疑是人本主義等附加在音樂之上的非本質的、不具有給定性的東西。相比而言,嵇康“情感于音”的“聲無哀樂論”則更好地表達了藝術自律的主張,符合音樂作為藝術的給定性特點。而要達致音樂這種先天的給定性的本真,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不同的人的心不同,所以所感發的情感不同。一方面,音樂是具有先在給定性的,是純粹的現象存在。另一方面,心作為連接主客觀的思維器官,是產生美和鑒賞美的主體。從產生美的角度看,作曲者和演奏者對音樂的詮釋體現的是一種藝術創作的主體性。而從鑒賞美的角度看,聆聽者和欣賞者對音樂的感悟和理解,則體現的是一種對音樂欣賞的主體間性。正是主體性和主體間性共同構成了藝術美的世界。因此,某種意義上講,心具有質料上的意義,對藝術美特別是音樂藝術的美具有根本的規定性作用。如果說神代表的是一種獨立于主體性之外的客觀存在,需要主體性去體會和表達,而心則是主體性和主體間性得以存在的基礎,是主體性和主體間性內在所具有的。
概言之,在中國美學話語體系中,道、神,心具有規定著中國美學精神的質料性作用。其中,道是最根本的質料,神和心是分別側重于不同領域的質料。(1)當然,神與心分別對應視覺和聽覺藝術方面的質料特點并非絕對的不可跨越。也就是說,神只是相對側重于視覺藝術,這并不是說聽覺藝術等視覺以外的藝術形式不需要神作為質料。同理,心也會成為視覺藝術或其他藝術的質料。這點是必須要加以說明,否則就陷入到一種形而上學的僵化框架中。三者在理論上都是自洽的,前科學的,前邏輯的,具有一定的先驗性。同時,道、神、心不僅催生了中國美學諸多的概念范疇,而且深刻滲透到日常生活實踐中,左右著中國美學的精神方向,并在世界美學史上代表了中國聲音,中國風格,中國氣質。
綜上所述,胡塞爾的現象學還原理論對還中國傳統美學精神的本來面目,對追尋和挖掘中國傳統美學中所具有的超越階級、宗教、政治、倫理等歷史局限的普世價值具有方法論意義。同時,在現象學視域下,探索中國美學話語中那種最本真的、最原初、最恒定的質料也是大有裨益的,有利于推動具有中國特色的美學話語體系的構建。當然,作為一種先驗哲學,胡塞爾的現象學理論也是有其自身缺欠性的,但作為一種方法論,其對中國美學精神和美學話語體系構建還是具有一定的理論借鑒和現實指導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