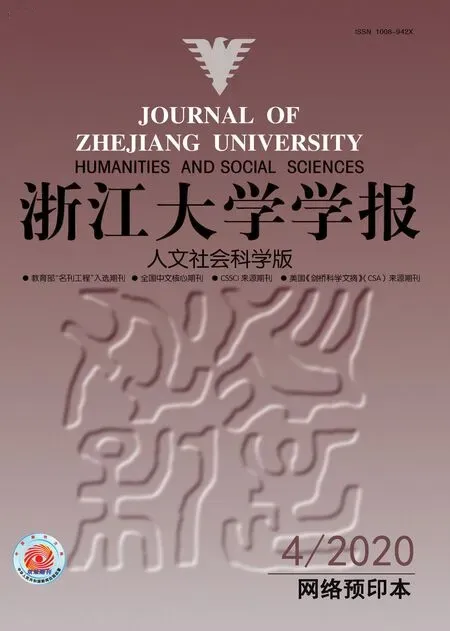理想主義的限度與超越
——基于馬克思對《斯考爾皮昂和費利克斯》自我評價的考察
劉同舫 佘梅溪
(浙江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 浙江 杭州 310028)
青年馬克思于1836年10月初到柏林大學時依然保持理想主義的思想底色,一年之后卻實現了從康德和費希特的理想主義向黑格爾哲學的轉變,這一重大的思想轉變并未引起學界足夠的重視。究其原因,主要是這一時期馬克思以文學創作為主,而文學作品與學術研究之間在話語體系上存在較大差異,更重要的是,文學作品缺少學術研究的學理性和嚴謹性。從馬克思這一時期的詩歌和劇本等文學作品中,我們無法尋找到馬克思理想主義實質性變化的蹤跡:詩歌創作的主旋律是“純理想主義”[1]6的,并未實現對理想主義的超越,其折射出的理想主義變動非常細微;劇本被馬克思認定為“不成功”的作品,其篇幅僅有一幕,且內容并未直接涉及黑格爾哲學及理想主義轉向。然而,在這一時期唯一的一篇小說《斯考爾皮昂和費利克斯》中,馬克思揭示了理想主義限度的表現形式,追溯了理想主義限度的浪漫主義根源,先后摒棄了康德、費希特抽象的理想主義,轉向對黑格爾哲學的批判性繼承,實現了對理想主義限度的實質性超越。本文以馬克思對小說的自我評價“理想主義滲透”[1]12為分析起點,試圖闡明該小說雖具有理想主義的表現形式,但并未局限于抽象的理想層面,其內容落腳于非理想主義的現實因素,內含馬克思的理想主義思想糾葛的獨特見解。通過文本形式的選擇,剖析馬克思早期的理想主義轉變,進而厘清馬克思對黑格爾理想主義的傳承和超越,有助于發掘馬克思的早期思想,明晰青年馬克思的思想轉變過程。
一、 “理想主義滲透”: 馬克思對小說的自我評價
馬克思對《斯考爾皮昂和費利克斯》的自我評價是“理想主義滲透了那勉強寫出來的幽默小說”[1]12。對其中“滲透”一詞的理解,將直接影響對小說中理想主義把握的準確度。“滲透”一詞比較微妙,它有兩種不同程度的釋義:一種是“滲入、透過”;另一種是“逐漸進入”。結合理想主義特質審視小說文本可以發現,馬克思在自我評價中所說的“滲透”更貼合后一種釋義,即理想主義雖然滲入了小說的表達形式,卻并未徹底滲入其內容。
《斯考爾皮昂和費利克斯》在形式上具有明顯的理想主義的非現實性、抽象性特征,表明理想主義已然滲入它的文本形式。首先,小說在章目形式上結構混亂,背離現實敘事的客觀需要,存在理想主義的非現實性特征。小說共計10 000多字,自第10章開篇至第48章收尾,僅有24章,中間存在大量缺章;各章篇幅不平衡,部分章字數多達2 000余字,而部分章卻僅有幾句話,無序散漫,失之規整,同現實事件的演進不盡契合。其次,小說采用符號化形式塑造主要人物,具有理想主義的抽象性特征。小說以人物的名字為基線揭示人物的內在特性。例如,默騰(Merten)與馬特(Martel)發音相似,而Martel在歷史上有“錘子”之意,所以,默騰的出場動作就是擊打費利克斯;瑪格達萊娜(Magdalene)被視為仙女,就在于德語“Magdalene”與“抹大拉的馬利亞”即耶穌忠實的女性門徒的名字拼寫一致。抽象的符號化描述雖然在形式上豐富了人物的象征意義,但在實質上卻剝離了人物的現實存在,以致小說人物的具體形象與現實發生割裂,在內容上呈現出理想主義的非現實性。
盡管理想主義已滲入小說形式并對其內容產生一定的影響,但是小說因其內容的現實性“抵御”了理想主義的徹底“滲入”。一方面,小說的環境背景具有現實色彩。小說對自然環境描寫著墨甚少,而對社會現實環境描寫格外豐滿。如小說中描述道:“我內心深處感到激動,我端詳著天地萬物、自己的內心和上述這二十五塔勒(這三個詞包含著一個多么了不起的實體啊!它們無所不在,它們發出的聲響宛如仙樂,它們使人想起末日審判和國庫)”[2]807;“愛司已成了一切近代法學的基礎”[2]822(撲克牌中“愛司”的德文“Aβ”與拉丁文的“As”即“金錢”發音相近);“他們遠遠地坐著,使執政者和平民之間保留一定的空隙”[2]823;“他是懷著迷信的崇敬心來侍候這條狗的,它在桌旁的座位是最雅致的”[2]824;等等。小說描述了“二十五塔勒”對人的吸引,刻畫出金錢致人癲狂的狀態;強調“愛司”的法學地位,揭露社會中的物質崇拜;展現不同階級的日常生活,批判無處不在的階級壓迫;神化狗的存在,譏諷封建迷信……使現實的“光束”透過理想主義形式,讓小說呈現出現實主義的黑色幽默性和深刻諷刺性。另一方面,小說內容的展開依托現實依據。默騰與德語“Martel”(錘子)諧音,他的所作所為均與現實的錘子及其基本功能存在一定的必然聯系,如小說中寫道,默騰的手掌在觸碰費利克斯時讓“費利克斯確實相信他受到了錘子的撫愛”[2]810。狗與圣使徒博尼法齊烏斯同名,以致它的失蹤使“大家都被罩在一片漆黑中,接著一個充滿不祥之兆的、急風暴雨的夜晚降臨了”[2]824,如同圣使徒消失一般引發令人膽戰心驚的軒然大波。主人公“我”的觀點和行為具有明顯的解釋信息、推進情節的作用,增強了現實在小說中的存在感和影響力。
《斯考爾皮昂和費利克斯》雖具有理想主義的表現形式,但內容卻落腳于非理想主義的現實存在。理想主義只達到滲入小說表層的程度,這是馬克思曾經堅持的理想主義對意欲表達現實的小說創作產生影響的結果。馬克思思想深處的理想主義糾葛充分表現在小說形式的理想主義同內容的非理想主義的沖突中,其矛盾心理與復雜情感加大了小說創作的難度,馬克思自身也承認這篇“幽默小說”是“勉強”寫出的。馬克思在小說創作中的思想沖突使其進一步察覺到理想主義“變成一種大部分沒有鼓舞人心的對象、沒有奔放的思路的純形式藝術”[1]12。其理想主義思想遭遇非理想主義的現實沖擊,馬克思正是在現實沖擊下展開了對理想主義的反思性理解。
二、 馬克思的理解: 何種意義上的“理想主義”?
“理想主義滲透”了的小說《斯考爾皮昂和弗利克斯》不同于“純理想主義”的詩歌,它以現實為航標,運用理想主義形式呈現現實內容,表明馬克思曾經堅持的理想主義發生動搖,勢必導致他對理想主義及其現實意義的理解隨之發生相應的變化。
馬克思利用小說的現世性(1)現世性是指文本是客觀存在于世界中的現象,投射并構成現實世界。小說能夠實現理想主義要素與現實要素的共存,其所展示的虛構幻想不等同于應然的理想存在,幻想看似與現實對立,實則是扭曲的現實。著名文學理論家與批評家薩義德就曾指出:“文本是現世性的,從某種程度上說是事件,而且即便是在文本似乎否認這一點時,仍然是它們在其中被發現并得到釋義的社會世態、人類生活和歷史生活各階段(moments)的一部分。”參見[美]愛德華·W.薩義德《世界·文本·批評家》,李自修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7頁。特質,結合現實理解理想主義,從三個方面剖析理想主義限度的表現。首先,馬克思披露理想主義之理想對人的創造物——財富的侵占。小說第10章從現實的物質生活出發,指出財富由凡人創造,但“凡人的權力不能享有這筆錢,只有那統治天宇的最高權力”[2]807,即理想的上帝才有資格享有。其次,揭示理想主義之理想對現實的人的侵占。小說第19章寫道,“我們看到遠處宏偉高尚的、光芒四射的思想,我們預感到著了魔的痛苦”[2]810。理想本應是現實所趨向的模范,但理想主義之理想只能帶給現實人類被操縱的痛苦。再次,揭露理想主義之理想的存在基礎與現實對立。馬克思在小說第39章指出,理想存在的合理性源于神圣權力,但神圣權力存在的基礎并非現實,而是幻想。理想一旦離開幻想的遮掩,內在的虛無性便暴露無遺。即使理想依憑幻想獲得存在,它本身對現實的脫離也必然造成理想的非現實性,致使其與現實對立乃至割裂。因此,理想主義中理想的生成和存在均與現實處于對立且無法彌合的矛盾狀態。
理想主義是有限度的存在,而其限度的產生根源與浪漫主義密切關聯。馬克思在波恩大學求學期間曾受到浪漫主義的影響,而理想主義源于歐洲啟蒙運動的浪漫主義,帶有浪漫主義的種種痕跡,因而他在小說中不自覺地從浪漫主義視角探尋理想主義限度的根源及其解決方案。一是揭示理想主義的本體是源于浪漫主義的抽象的普遍精神。小說描寫最高權力統治宇宙的狀態時認為,作為理想主義本體的最高權力只是虛構故事中的角色,看似涵蓋現實萬物,卻并不具有現實支撐,反倒以抽象的普遍精神為存在形態。“在本體意義上說,浪漫主義始作俑于萬物的一(oneness)。這種普遍的一在自然的多樣性中展現自身,并作為精神——神圣的精神拂過萬物。”[3]6理想主義的本體淵源是抽象的普遍精神而非現實世界,這勢必造成理想與現實既相互脫離又彼此對立的外在關系。二是揭示理想主義合理化自身存在的方式的抽象性。理想主義采取了同浪漫主義一致的生成路徑:“實在的第一范疇是生成。生成被認為是一種流動”[3]64,通過抽象生成的方式將世界存在的根源歸于抽象自身,證實自身存在的現實意義。鑒于此,馬克思通過小說表達對理想主義生成路徑合理性的否定態度。在小說中,如流動的河水一般普通平常的雙眼的靈魂是“藍色染匠”[2]809,“藍色染匠”(Blauf?rber)在德文中有“撒謊者”之意。斯考爾皮昂和默騰受到神圣存在的影響,但未發生具有創造性意義的生成,“正像一個胚胎尚未掙脫世間關系而形成一種特殊形狀那樣,他倆身體各部分的聯結力在一片正在膨脹的混沌狀態中也完全松散了,結果是他倆的鼻子跌落在肚臍上,而腦袋掉在地上”[2]821。無論抽象的普遍精神采取何種形式的發展演變,都屬于思辨的邏輯,而邏輯的嚴密性不能改變其抽象本質,抽象邏輯創造的仍是虛假現實。馬克思利用熟識的浪漫主義視角剖析理想主義如何通過抽象性本體與抽象性生成,構建起非現實的、抽象的理想世界,意識到理想主義非現實的抽象本質,決定了理想與現實的對立是理想主義的固有限度[2]7。
在認識理想主義的限度和質疑理想主義的合理性的基礎上,馬克思重新審視理想主義的意義,將理想主義從意欲表達的思想內容轉變為表達思想的手段。他運用理想主義慣用的象征手法,但摒棄了這一手法的虛構性質,將象征改造為輔助理解現實的工具。默騰象征擁有錘子般權力的統治者,斯考爾皮昂象征蝎子般狠毒的統治階級,瑪格達萊娜象征無批判思想的衛道女等,馬克思通過賦予象征以現實內容,基本否定了理想主義試圖構建的具有欺騙性質的存在。與此同時,馬克思還結合現實因素,利用理想主義抽象邏輯推演的優勢,表達自身對現實發展演進的理解。在小說第21章中,馬克思推演默騰(Merten)一家可能是戰神瑪爾斯(Mars)的后代:“Mars的第二格為Martis,希臘語中的第四格為Martin,由此而得出Mertin和Merten”[2]811,且職業為裁縫的“默騰”與能夠實施暴力的工具“錘子”諧音,“戰神的技藝同裁縫的技藝相像之處就是截裁,因為他截手裁腳,截掉人間的幸福”[2]811。默騰的兒子名叫斯考爾皮昂(Scorpion),“Scorpion”這個詞的本義是“蝎子”,蝎子是“一種能用眼光殺害人的有毒動物,它所造成的傷害是致命的,它的目光能摧殘破壞——這是對戰爭的絕妙諷喻,戰爭的目光是致命的,戰爭的后果會在受害者身上留下內部出血、再也無法治愈的斑斑傷痕”[2]811-812。繼而依據默騰的信仰、社會文化演變、當地風俗習慣、民族血統等綜合要素再次確證推演的合理性。馬克思將理想主義象征表達與現實因素相融合,將抽象邏輯推演與社會歷史發展相結合,在創作“理想主義滲透”了的小說中實現對現實的分析反思,比較客觀地肯定了理想主義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擔當現實表達工具的基本功能。
三、 馬克思對理想主義限度的超越
在小說的邏輯展開中,馬克思逐漸表現出對康德和費希特式理想主義的抵觸,反倒對黑格爾邏輯學式的現實主義較為青睞,這鮮明地體現出批判現實的創作旨趣和深入歷史的現實精神在馬克思此時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但是,馬克思并沒有止步于從抽象中把握的現實,小說同樣內含對黑格爾被理想主義同化的虛假現實的批判,這進一步凸顯出馬克思以理想與現實的統一為特征的、對理想主義限度的實質性超越。
馬克思通過對康德理想主義中理性認識之斷裂的指認,否定實踐理性的能力,摒棄了康德的理想主義。馬克思在小說第19章中直接描摹現象界與物自體的斷裂狀態,“我們喜愛展現在我們面前的這個萬木蔥蘢的世界,我們看到遠處宏偉高尚的、光芒四射的思想”[2]810。“萬木蔥蘢的世界”代指康德的現象界,而現象界是物自體展露于世人面前的形式,世人在現象界中能夠認知模糊、不真切的物自體,但是“一旦我們認出它們,它們就像美麗、優雅、歡樂三女神一樣,羞怯地畏縮后退”[2]810。物自體在康德理想主義中是理性認識能力無法直接把握的存在,所以現象界顯現的并非物自體本身,只是看似觸手可及的鏡花水月。馬克思對康德理性認識的描述并非意在表達認同,而是力圖展開批判。他系統批判了康德理想主義割裂現象界與物自體的目的,即開發實踐理性以形成能夠指導人類進行科學判斷、實施合理行為、建構理想世界、獲得不受認識形式限制的自由理想領域的絕對命令(2)康德的理想主義試圖通過割裂現象界與物自體明確人類理性認識能力的界限,為信仰留有余地,實現對實踐理性的開發,讓實踐理性的道德意志形成絕對命令。。小說第27章引用《新約全書》中“山羊置于左,綿羊置于右”的典故以探討“左右問題”。山羊與綿羊在《新約全書》中代表擁有不同信仰的人,左或右是人選擇不同信仰的結果。馬克思對“左右問題”的探討看似在研判信仰問題,實則是探尋人對理想性存在的選擇。他指出“左”與“右”“不過是兩個相對的概念”[2]816,否認了確切的理想性存在,直接取消了康德理想主義的追求目標。即使理想真實存在,現實根基薄弱的人類實踐理性也不能形成具有指導意義的絕對命令,無法做出獲取理想性存在的正確判斷。“如果靡菲斯特斐勒司在這時出現,我就會變成浮士德,因為很清楚,我們大家都是浮士德,原因在于我們不知道哪個方向是右,哪個方向是左……”[2]817馬克思深刻揭示了康德理想主義所導向的理想是與現實相對立的虛幻假象,康德對實踐理性的開發也難以實現理想并解決理想主義的限度問題。
面對康德理想主義內部明顯的斷裂,馬克思曾試圖從費希特的思想中尋求化解斷裂的理論支撐。他肯定費希特思想的“絕對自我內部存在非我”這一具有辯證關系的觀點,在小說中發出“啊!我是自己的替身”[2]828的感嘆,以表明他對自我與非我之同一性觀點的把握。但是,馬克思所欣賞的僅限于費希特的辯證關系,他并不認可費希特為了彌合康德理想主義的內部斷裂而創造“絕對自我”的解決方案(3)費希特發展了康德的理想主義,他認為物自體是自我設定的非我,將物自體與現象界統一于絕對自我的辯證運動,通過強調人的自我意識的實踐創造能力彌合康德理想主義內部割裂的缺陷。。馬克思認為,“絕對自我”實現統一的基礎是徹底的主觀性,純主觀的“絕對自我”不能夠創造任何現實存在,主觀性基礎將導致客觀現實更加遙遠,依然無法打破理想主義限度的對立性桎梏。于是,馬克思轉而試圖在現實的生活中找尋人的存在依據,展示人的現實生活對人之存在的影響。他在小說中將人的生活描述為圓形的競技場,“在我們摔倒在沙地上,角斗士即生活把我們殺掉之前,我們一直繞著圈子奔跑,尋找它的左右兩邊”[2]817。圓圈中左右的位置根據人的奔跑不斷發生變化,人的現實活動能夠打破理想與現實的對立狀態,超越理想主義設定的理想性存在。馬克思通過將現實因素引入反思理想主義,促使自我走出主觀世界,走向現實的生活世界,超越費希特“絕對自我”的狹隘性。他反思的基礎已然扎根于現實,徹底否定理想主義中抽象理想的存在,形成了基于現實的批判意識。
為了徹底解決理想與現實對立的問題,青年馬克思繼續探尋協調理想與現實關系的理論道路。他欣賞黑格爾將歷史、社會等現實因素與理想辯證融合于一體,運用辯證思維調和理想主義內部對立的高明之舉。但隨著對黑格爾哲學的深入理解,馬克思察覺到黑格爾哲學在實現自身圓滿的同時,也暴露了絕對圓滿外部的現實缺陷,即黑格爾哲學中的歷史、社會是被理想主義同化的虛假現實,不具備解決理想與現實對立問題的可行性和發展性。他立足現實的歷史發展批判了黑格爾哲學中的虛假現實,找尋到一條由現實走向理想的發展路徑,最終實現了對理想主義限度的超越。
第一,否定黑格爾理想主義中虛假現實的歸宿——以意志為根據的國家。小說在第27章結尾呼喚“我們需要一個新的救世主”[2]817。于是,第28章的開篇出現了一位國家官僚的代表恩格爾伯特。恩格爾伯特像一條干癟的蜥蜴,有著駭人的高顴骨,火紅的鼻子,嗓音嘈雜含混,講話邏輯混亂還結巴,認為“鴿子的眼睛是最聰慧的,他本人雖然不是鴿子,但至少對于理智來說他是個聾子”[2]819。在西方,蜥蜴是權力、邪惡的象征,紅色是暴力的象征,而鴿子的眼睛就是紅色的,且在德文中“Taube”(鴿子)與“Tauber”(聾子)發音相近。究其旨意,在于抨擊黑格爾的救世主是依靠邪惡權力和暴力爬上統治地位的小丑,否定黑格爾理想主義的國家觀,即國家是人的目的及最高義務,人能夠在維護國家中獲得理想性存在(4)黑格爾認為,國家是人“在世上行進的神”,“國家的基礎就是作為意志來自我實現的理性的權力”,是理想主義中理想性存在的現實形態,服務于理想主義的普遍精神(理性)。維護國家就是遵循理性的發展,而理性與人的發展具有統一性,因此,人能夠在維護國家中實現自我。參見[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鄧安慶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88頁。。
第二,批判黑格爾哲學中國家的現實統治形式即長子繼承制的理想主義本質。馬克思在小說第29章中剖析了長子繼承制,揭示出缺少現實存在合理性的國家的維權奧秘。他嘲諷“長子繼承權是貴族政體的小浴室”[2]820,直指長子繼承制作為國家展現理性力量的現實形式,是在封閉的理想主義普遍精神保護下的國家制度。長子繼承制盡管在形式上賦予長子絕對的權力,保障了權力接續的穩定性,但這種封閉式的維護只能起到短暫的效果,且對人的現實創造能力造成實質性的摧毀,在給“一家的長子鍍上一層銀”的同時也給整個政體“印上一層愁苦的浪漫主義慘淡色彩”[2]820。長子繼承制看似是保障國家長期穩定存在的現實制度樣態,實則是逃避現實、陳舊迂腐的表征,它以抽象普遍精神構筑的密閉體系將統治階級與現實歷史發展隔絕,創造虛假現實的抽象永恒,以致“當今之世是寫不出敘事史詩的”[2]820-821,結果只能是理想主義的虛假現實與歷史發展的現實之間發生徹底的斷裂,無法走向真正的理想。
第三,探究國家現實的歷史發展,理清現實走向理想的基本路徑。馬克思追溯國家的歷史淵源,解析影響其發展的現實因素,以歷史發展的現實取代理想主義抽象普遍精神的邏輯發展的“現實”。他以裁縫出身的默騰為例剖析“默騰國家機構”[2]823的發展史。一方面,馬克思詳盡推敲默騰的民族血統,將他認定為戰神的后代;另一方面,馬克思探究默騰早期的財富積累,將他描述為法蘭克王國的奠基人克洛維的馬褲裁制者,且因克洛維穿了此條馬褲贏得普瓦捷會戰的勝利而獲得兩百金幣的獎賞,最終建立起自己的“默騰國家機構”。馬克思筆下默騰發家的因素包含民族、勞動、暴力以及資本等,他指出人的現實勞動創造的物質財富構成最初的資本積累,并借助暴力與勞動分工產生階級,最終構建了暴力機器——國家。由此可見,馬克思不僅否定黑格爾哲學中普遍精神發展的動力內核,而且較為真切地揭示出資本、暴力和資本主義國家產生的內在規律。
第四,打破理想主義的抽象性,在現實勞動中探尋理想存在。馬克思認為,個人可以通過勞動爭取理想的生活,但個人一旦凌駕于他人權利之上,便會失去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小說宣揚了那些“普通的人,即沒有長子繼承權的人,得跟生活的急流搏斗,投身波濤澎湃的大海,在幽深的海底奪取普羅米修斯右手中的明珠”[2]820。相反,默騰卻因實施貪婪的掠奪、錘子般的暴力而使自己在那只與圣使徒同名的狗患病時落入無人相助的孤立境地。這表明,馬克思已經發現蘊藏在人民群眾內部的現實力量,認識到人的活動能夠推動現實走向理想進而打破理想主義限度。
總之,馬克思批判理想主義的起點是以思想的銳利目光去觀察今昔,以便在現實的歷史維度中認清自己實際情況的自我反思。他運用文學的表達方式,在自由創作中反思自我、反思先哲、感知現實、認知理想,跳出先哲構建的理想主義世界,追溯理想主義的浪漫主義淵源,在理想主義與浪漫主義一致性的生成方式中認識到理想主義的限度,形成了獨立的基于現實的批判意識,完成了對理想主義所構建的虛假現實的實質性超越。馬克思摒棄康德、費希特抽象的理想主義,轉向對黑格爾哲學的批判性繼承,是其獨立的現實批判意識覺醒的必然結果。這種基于現實的反思和批判精神貫穿于馬克思思想發展始終,成為其不斷突破超越的內在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