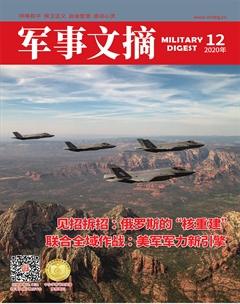對美軍聯合全域作戰概念要點的思考
文予
當前,美軍高層宣傳的聯合全域作戰概念尚處于初級的研討和開發階段,雖然參聯會高層借由媒體吹風預計于2020年底發布聯合概念初版文件,但從美軍作戰理論研究視角看,未來聯合全域作戰概念的性質和層次尚未有定論。在“多域”向“全域”升級演進的洶涌波濤之下,各軍種圍繞“How”引出的主導權問題的爭鳴卻暗流涌動。例如,“全域戰”中哪一個作戰領域最為關鍵?聯合全域作戰中各軍種之間的主次地位如何劃分?聯合全域作戰的指揮與控制將依托于哪個或哪幾個軍種的技術架構?現有戰區聯合司令部的體制能否實現聯合全域作戰?軍種的“全域”能力和聯合“全域”能力劃分和使用的邊界在哪里?……一連串的問題的背后是利益的切分、技術的屏障和文化的藩籬。
美國陸軍和空軍最積極
關于多域戰或聯合全域作戰概念的開發,目前美軍中最為積極的當屬陸軍和空軍這兩個軍種。這種互動的背景可追溯至20世紀80年代的空地一體戰。在80年代以前,美軍雖然設有多個聯合作戰司令部,但這些司令部大大受制于各軍種之間的利益爭斗而淪為軍種部的附庸,對各軍種之間的聯合訓練及作戰并沒有實際指揮權。
20世紀80年代初,在深入總結第四次中東戰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美軍提出了空地一體戰作戰概念,以應對蘇聯坦克集群在歐洲平原給北約帶來的巨大安全威脅。空地一體戰概念要求地面部隊和空中力量甚至部分海軍兵力高度協同,陸軍主要負責前線進攻性機動防御作戰,而空軍這個之前以“投送戰術核武器或進行空中格斗”為主的軍種也開始調整定位,通過打擊敵軍后方和阻滯其充實前線兵力來為陸軍提供戰役及戰術支援。
這是美軍歷史上陸軍和空軍這兩個軍種的首次深度協作,美軍以空地一體戰在戰場的全縱深對敵人進行打擊,實現了作戰空間和進攻兵力的一體化,把時間、空間和力量等3個基礎要素進行了重組,實現了作戰效能的系統性增強。因此空地一體戰作戰概念實際上首次真正開辟了美軍聯合作戰的理論架構,該作戰思想一定程度上也對美軍聯合作戰理論的完善和確立發揮了催化劑的作用。
此后不久,1987年,美國國會就通過了著名的《國防部改組法》,在機構設置和權力分配上為聯合作戰的實施掃清了障礙,也促進了這一概念的繼續發展和演化。雖然空地一體戰作戰概念的主要目標是當時蘇聯可能在歐洲發動的閃擊戰,但卻在1991年的海灣戰爭中得到了極致演繹。從1981年空地一體戰作戰概念提出,經歷十年磨劍,到1991年的實際運用,聯合作戰的概念已經深入人心。
近年來,美國陸軍和空軍在概念開發上積極協作,兩軍種高層密切互動,在設計“多域”或“全域”行動框架時互有借鑒,其密切程度讓人不禁聯想起當年開發空地一體戰概念的輝煌情形。但細研深思,當前空軍和陸軍的互動還比較膚淺,實際上都是在基于自己的軍種架構和認知去開發相關概念,如陸軍強調自己在陸域持久作戰的傳統,凸顯自己作為前沿部署力量在“拒止”條件下“突破和瓦解敵人的‘反介入/區域拒止系統,并利用由此產生的機動自由達成目標”的軍種優勢;而空軍則基于自己“空天一體”的制高點優勢,聚焦“空、天、網”和“電磁頻譜”這幾個領域重點開發聯合全域指揮控制項目。兩個軍種對自己目前“多域”或“全域”開發的定位都是邁向聯合的一種探索,這種過程必然帶有濃重的軍種色彩。這絕不僅僅是一種軍種藩籬的本位主義,更是他們的認知的局限和組織架構的限制。
“網、天”兩個領域是重點
在聯合全域作戰概念的構想下,不同“域”中的作戰節奏、作戰樣式和作戰能力千差萬別,其時空特性也千差萬別。例如,時間上,地面的特種部隊隊員以每小時5千米左右的速度步行接敵,而海上的航母戰斗群航行速度可達到時速30海里,空中戰場的F-22戰機能夠以馬赫數2.25的超聲速飛行,太空戰場上衛星以每秒7.9千米的第一宇宙速度環繞飛行,網絡空間的信息流轉則以光速進行;空間上,未來聯合全域作戰中,軍事大國的武器系統在打擊速率、精度、距離等方面已經遠遠超出區域性地理空間的限制,從海洋表面到大洋深處、從陸上高地到大氣空間與外層空間,從小范圍影響作戰行動的地貌特征,到影響遠程精確火力作用的“地球曲面”等,整個地球乃至部分太空環境均可能變成軍事空間。聯合全域作戰構想力圖去無縫式聚合“陸、海、空、天、網”所有領域的能力,考慮到各領域復雜的時空特性,其實現絕非易事。
此次發聲中,參聯會副主席約翰·海頓著重強調了新概念中“網、天”兩個作戰領域的特殊性。他認為,“‘聯合全域作戰涉及空中、陸地、海上、太空、網絡和電磁頻譜,一切未來作戰的要素都將被考慮到。其中,最大的區別是網絡和太空這兩個領域的加入。”在現有的美軍聯合作戰體系中,特定作戰區的“陸、海、空”傳統領域的作戰協同由相應的戰區司令部負責,這3個領域的聯合美軍早已“爐火純青”,加上近30年來,美軍在戰爭實踐中所面對的均是比自己弱小太多的對手,從未遇到真正的來自網絡和太空領域的軍事威脅。但未來大國競爭的背景下,美軍將面臨在所有領域激烈對抗的條件下去聯合“網、天”和“陸、海、空”的全新挑戰。現有的美軍指揮體制設置中,網絡和太空這兩大新興作戰領域均有著各自獨立的指揮機構,即太空司令部和網絡司令部,陸、海、空各軍種也都有自己的網絡和太空作戰能力單元,這種指揮機構的設置和作戰能力的重復將使得加入了“網、天”兩域的聯合全域指揮控制面臨嚴峻的挑戰。
“跨域協同”仍是核心思想
聯合全域作戰所面臨的核心問題是未來大國“反介入/區域拒止”體系對聯合部隊機動自由的挑戰,而當前美軍聯合作戰理論中,破解“反介入/區域拒止”體系的核心概念正是“跨域協同”。所謂“跨域協同”,是指“轉變思維模式,采取跨域的視角審視問題,將不同領域內的能力予以互補而非單純疊加性利用,弱化力量的軍種來源,通過各領域能力的互補,使各域互相增效,從而建立起聯合領域優勢,最終實現聯合部隊的火力和機動自由。”
“跨域協同”代表著一種“基于領域而非基于軍種”的思維方式,它強調“不對稱作戰”,即避免與敵在某一領域“針尖對麥芒”硬碰。以己之長,擊敵之短,通過不同領域的能力互補而非簡單疊加,使各領域之間互補增效,從而建立優勢,獲取完成任務所需的行動自由。例如,使用F-35戰機摧毀敵方反艦導彈,利用海軍力量打擊防空系統,運用電磁網絡戰武器癱瘓敵防空系統,使用艦對地導彈摧毀敵陸上指控中心,利用地面部隊打擊針對空軍和海軍的陸基威脅,利用網絡行動打擊太空系統等等。
利用“跨域”優勢克服未來介入挑戰,需要一種極高的整合度,且這種整合必須在更低的戰術層級進行,并將太空戰、網絡戰更為全面靈活地融入到陸、海、空戰場,以生成作戰所需的所謂“機器到機器”的急速。未來的聯合全域作戰構想中,美軍期望通過機器人、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顛覆性技術,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全域態勢感知,在所有作戰領域把握破壞敵人系統的稍縱即逝的“機會窗口”,爾后運用聯合全域指揮控制技術,從不同的作戰領域調用最有效的作戰資源加以應對,達成跨域制衡之目的。
實際上,廣義的“跨域”協同不僅適用于部署在戰場、從外向內打擊敵方反介入體系的聯合部隊,也適用于部署至戰場、由內向外毀傷對手的前沿部署部隊;既可以是聯合部隊的內部融合,也可以是聯合部隊與外國軍事盟友的相互融合,因為外軍盟友能為多國任務貢獻各種力量,聯合部隊必須能夠與這些盟友協同融合。此外,雖然聯合協同注重各軍種能力的整合,但是“跨域協同”注重各個領域間的整合,而非某一軍種提供某種行動或能力。因此,這一概念將綜合運用各領域的作戰力量,與當前的聯合作戰相比,聯合的速度更快、聯合的程度更細、聯合的層級也更低。
聯合全域作戰的實現,道阻且艱
對美軍而言,作戰概念的提出只是一種理論驅動,要想真正將理論轉化為實踐絕非易事。正如美軍參聯會副主席在接受采訪時坦言,“各領域的無縫融合和有效指揮和控制仍是一項艱巨的挑戰,我們還不清楚究竟要如何做到,沒人有現成的答案。”聯合全域作戰的實現也將面臨一系列挑戰。
首先,戰爭實踐的限制將使得“軍種至上”的本位主義重新抬頭。美軍以聯合作戰為主的歷史已有近30年,從巴拿馬到伊拉克再到阿富汗,戰時需求的倒逼和戰爭實踐的砥礪使得美軍更加深刻地認識到聯合作戰的重要性,于是采用各種方式整合軍種作戰能力,使作戰行動收到了大于個體之和的作戰效益。盡管如此,美軍從“以軍種為中心”到“以聯合為中心”的艱難轉變仍未完成,各軍種仍然存在堅守軍種能力所有權而不是心甘情愿提供這些能力的傾向,而聯合全域作戰從聯合的層次、程度和速度上都遠遠超過現有的聯合作戰樣式,就好比讓一個孩子還沒有學會走路就練習田徑項目,其實現難度可想而知。加上目前美軍已結束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海外用兵,沒有了戰時需求和作戰壓力,“以軍種為中心”的思想必然抬頭,軍種利益便會高于聯合利益,從而影響聯合全域作戰向深度和廣度發展。
其次,預算緊縮可能導致各軍種導致優先滿足軍種需求而不是聯合需求。由于建立和規范美國武裝力量的法律強調以軍種為中心,美國的軍費,主要是按軍種和國防部直屬機構分配,而不是按軍種作戰職能和聯合作戰職能分配,若這項制度設計不改革,在日益收緊的預算韁繩下,分到各軍種和國防部直屬機構的錢,有多少可以用于聯合能力建設,有多少可以用于軍種能力建設,基本上是各軍種說了算。國防預算減少,分攤到各軍種的錢也會相應減少。錢少了,各軍種必然優先滿足軍種能力需求,而不是聯合能力需求。正所謂“屁股決定腦子”,即便是那些贊成聯合的人,也傾向于從加強自己軍種的角度來界定聯合,這樣,聯合能力建設就會遭到削弱,難以達到聯合全域作戰思想對各軍種聯合能力的要求,“跨域協同”理念也就難以落到實處。
再次,軍種文化或成為“跨域協同”的一道坎。在考察多域戰或聯合全域作戰概念之時,軍種視角和聯合視角可能會得到不同的答案。打個通俗的比喻,如果說陸、海、空、陸戰隊等軍種是形狀各異、特點不同、味道有別的“雞蛋、鵪鶉蛋、鴕鳥蛋和鴨蛋”,現有的“聯合作戰”好比是把一個個蛋放在同一碗里,重點是消除軍種的分歧,而未來隨著人工智能、高超聲速技術、納米技術和機器人技術等新興技術的發展,這些蛋的表殼將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裂縫”,不同“蛋”中的“蛋黃”和“蛋清”會慢慢交融在一起,而“多域”或“全域”等概念所追求的“多域聚合”是把這些軍種“蛋殼”界限徹底打碎,讓各種“蛋黃”和“蛋清”徹底融為一體。對食客而言,當你把蛋汁放入油鍋里烹飪而后噴香入口的那一刻,你或許不會在意這一口美味的“蛋”到底來自于“雞蛋、鵪鶉蛋、鴕鳥蛋或是鴨蛋”中的哪一個。但從軍種的視角看,這些“蛋”們一個個都有一股內在孕育獨立生命的強烈意愿,可能并不希望被“開膛破肚融為一體”。在美國武裝力量的現有軍種架構下,每一個軍種都在基于自己的“軍種文化”看待“多域戰或聯合全域作戰。在所有作戰領域中,陸域是惟一一個有人類生存活動的空間,陸軍也常是其他軍兵種誕生的母體。歷史上,每當“大規模軍事沖突”出現的時候,戰爭也就越發回歸其暴力和對抗的本質,和人最為貼近的陸權力量——陸軍也常回歸到血腥廝殺的戰爭角斗場的中心。技術越發展,對人的沖擊和影響也越大,著眼于“大國競爭”的多域戰概念最早由陸軍提出,或許也有這方面的原因。
最后,國防部權力有限,難以獲取和整合美國政府機構和盟國的能力。無論是多域戰還是聯合全域作戰,說到底,都是大國之間綜合國力的較量,大國之爭不僅要依靠軍事能力,還包括政治、經濟、外交、情報等綜合實力的對弈,這種層面的“跨域協同”要求遠遠超出了純軍事的范疇。而美國防部作為一級軍事機構,沒有足夠的權力和能力去獲取和整合各個領域、各個方面的能力,難以對國務院、財政部、國土安全部、中央情報局等政府機構發號施令,只能通過溝通協調來獲取和整合所需能力,這必然耗時費力,影響作戰進程。此外,美軍的作戰多是跨國性質的聯軍作戰,但國防部不僅沒有根據作戰需求獲取和整合盟國獨特作戰能力的權力,而且使用盟國和伙伴國提供的作戰能力時還受到種種限制,這必然對聯合全域作戰帶來負面影響。
從作戰理論視角看,多域戰、聯合全域作戰等未來作戰概念代表著美軍在戰略轉型期的一種積極探索,這些概念的醞釀、提出和發展中蘊含著許多有益的啟示,值得深入研究并學習借鑒。然而,自二戰以來,多域戰、聯合全域作戰等概念所設定的所謂“高端大國之間在多個領域間的激烈對撞”尚未有任何歷史先例可以借鑒,況且自核武器研制成功以來,“確保相互摧毀”的恐怖核平衡像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一樣懸掛在脆弱的人類文明之上,有核大國之間的所謂“多域”“全域”戰爭究竟是一場何種性質的戰爭?這種大國對撞會不會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局部的沖突會不會失控釀成全面的常規戰爭或是核戰爭的悲劇?大國之間的競爭應如何避開“修昔底德”陷阱?這些問題值得每一位愛好和平的人去深深思索。
責任編輯:張傳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