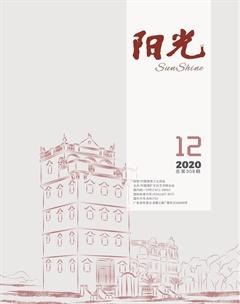“生活是礦井,愛是礦燈”
2020年11月7日上午,由中國煤礦文聯、中國煤炭報社、中國煤礦作協聯合主辦的“生活是礦井,愛是礦燈——著名作家劉慶邦長篇小說《女工繪》分享會”在煤炭大廈五樓會議室舉行。
中國煤炭報社黨委書記、中國煤礦作協副主席崔濤主持分享會。中國煤礦塵肺病基金會理事長、中國煤礦作協顧問黃毅,國務院僑辦原副主任、作家任啟亮,中國煤礦文聯副主席、煤礦作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徐迅,中國煤炭報社副總編輯封雪松,中國文聯特聘副主席、煤礦作協副主席劉俊,《中國煤炭報》專刊部主任楊凱,《中國應急管理報》消防與減災部副主任孫寶福,煤礦作家和朋友桑俊杰、付曉豫、姚喜岱以及中國礦業大學人文與藝術學院研究生共20多人參加了分享會。
“地火今又見烈焰,四部長篇繪礦山”“煤炭文學旗何在,慶邦小說領風騷”。煤礦文學老作家、老領導李士翹、吳曉煜分別向劉慶邦發來賀詩。分享會上,大家以文會友,熱情洋溢,紛紛暢所欲言,對劉慶邦這部煤礦題材長篇小說《女工繪》的問世給予了高度評價。
最后,劉慶邦對煤礦“自己人”舉辦的這次分享會表示了感謝。他深情地說:“我寫她們,因為愛她們。”他說:“《女工繪》中所寫到的女工,我跟其原型幾乎都有交往,有些交往還相當意味深長。在寫這部小說的好幾個月里,我似乎又跟她們走到了一起,我們在一個連隊(軍事化編制)干活兒,一個食堂吃飯,共同在宣傳隊里唱歌跳舞,一起去縣城的照相館照相。她們的一眉一目、一喜一悲、點點滴滴,都呈現在我的記憶里。”
因篇幅關系,不能全部發表與會者對《女工繪》的評價和感悟。這里節錄部分與會者的發言以饗讀者,并向劉慶邦為煤礦文學作出的巨大貢獻表示深深的敬意。
黃 毅
(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中國煤礦塵肺病防治基金會理事長)
藝術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這是藝術創作的普遍規律。慶邦先生就是沿著這條路而奮力前行的作家。他的作品始終植根于煤礦生活的肥田沃土,因而他的文學創作有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動力源泉。
能夠始終植根于煤礦生活的肥田沃土,源自慶邦先生對礦山的愛,對礦工的愛。正如冰心先生所說,“有了愛就有了一切。”我們透過慶邦先生的諸多文學作品,無一不是愛的產物,《女工繪》也是如此。
慶邦先生是從煤礦走出的作家。他長期在煤礦生活,深知礦工的喜怒哀樂。在他身上有著礦工的品質和情懷。在這一點上,我與慶邦先生有著相同的人生經歷。我們都曾與礦工朝夕相處、摸爬滾打,深深體會到井下作業的艱辛,也深深感受到蘊含在礦工身上的那種職業精神,他們就像一塊煤炭,質樸無華,一旦燃燒起來,卻釋放出無窮的能量。盡管把自己燒成灰燼,也要把光和熱奉獻給社會,奉獻給人民。可以說,礦工就是煤炭的人格化。
藝術源于生活,但源于生活的不一定都成為藝術。藝術是生活的理性思考和形象思維,是對生活感知的一種創造和升華。所以,藝術必須高于生活。能夠做到這一點的,絕非等閑之輩。必須通過艱苦的努力,提升自己的藝術創造能力。由此想到近代國學大師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談到,古今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須經歷三種之境界。我認為慶邦先生就達到了這樣三種境界。
其一,“昨夜西風凋敝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干事業、作學問,要有執著的追求,登高望遠,明確目標。慶邦先生文學創作方向很明確,就是植根礦山、心系礦工。不管風吹浪打,我自巋然不動。“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這種定力來自他的崇高追求,也來自他幾十年的人格修養。
其二,“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銷得人憔悴。”認準的事情就要干到底,鍥而不舍,孜孜以求,一往無前,奮斗不息。慶邦先生就具有這種百折不回、滴水穿石的精神品質。他能夠堅持寫作、筆耕不輟,能夠取得今天的文學創作成就,與他的奮斗精神息息相關。
其三,“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要想成就事業,必須耐得住寂寞,不被世俗所擾,不被名利所累,不被噪音所困。慶邦先生就是這種樸實無華、勤于筆耕的人。他始終專注于文學創作,專心于構思挖掘。他在煤礦這座文學創作的富礦里,幾十年如一日的開拓掘進。功夫不負有心人,功到自然成。
我們品讀慶邦先生的作品,既是分享他文學創作的快感,分享他精心釀造的如醇酒一樣的美文。同時,也感受到他高雅的品質和人格的魅力。
慶邦先生長我三個月,如今我們都在奔向古稀之年的路上。“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以此與慶邦兄共勉。有生之年,期待慶邦兄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問世。
任啟亮
(作家、國務院僑辦原副主任)
《女工繪》是慶邦的又一部長篇力作,她標志著慶邦煤礦題材創作的一個新的拓展,一個新的高度。初讀之后,有兩點深深打動了我:一是小說以一座煤礦為背景,通過一群年輕礦工的故事,真實而生動的反映了上世紀七十年代的礦山生活景象,形象化地真實地再現了當時的時代特征和社會風貌,在引起人們回憶懷舊的同時,更啟發人們回味反思。二是小說成功塑造了以主人公華春堂為代表的一批青年礦工形象,尤其是年輕女性礦工形象,在慶邦的煤炭人物畫廊中增添了一批血肉豐滿栩栩如生的藝術形象。
我就想圍繞以上兩點談談自己讀《女工繪》的粗淺感受。
上世紀七十年代前期,“文革”由狂飆突進漸入平淡,生產生活秩序基本恢復,但階級斗爭為綱和反修防修依然是社會主流意識,《女工繪》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展開的。當權者動輒以階級的觀念、斗爭的思維、政治的視角觀人論事;形式主義的天天讀,牛頭不對馬嘴的大批判充斥著日常政治生活;那是一個狂熱無序、真假不分、優劣難辨、黑白不明的時代。
在那樣一個大的背景下,人們的思想與行為無不深深打上階級的和政治的烙印。人因出身不同分為三六九等,所謂的地富反壞右不僅分配不到好的工作崗位,平時為人處世只能低調自律,找對象也要選擇出身講究根紅苗正。《女工繪》對時代背景的交待和描寫,并沒有在此止步,而是向深度和廣度挖掘,努力揭示生活的本質。那些青春煥發的青年男女,激情彭拜,不僅戰斗在生產一線,也活躍在體育場和音樂藝術的世界。在那樣一個變態的背景下,也無處不閃耀著正義的力量和人性的光輝。
這部小說對煤礦生產生活過程的敘述和描寫也非常全面到位。可以說是一幅煤礦生產的全景圖,也是一幅煤礦職工生活的風俗畫。慶邦的其它作品這種煤礦全景式的描寫不多。
所以,讀《女工繪》既一定程度上了解了上世紀70年代的中國,又比較全面細致的認識了一座煤礦。通過這些背景的鋪墊,一方面為書中人物搭建了一個既廣闊又具體的活動舞臺;又讓讀者多角度、多層面感悟那個特殊的年代,啟發人們進一步思考。
《女工繪》深深打動我的另一個原因,是那些青年礦工形象。他們來自各地經歷不同,他們興趣廣泛性格各異,他們上班下班、唱歌跳舞、說笑打鬧,有開心歡樂也有辛酸苦惱。他們懷揣夢想結局卻令人唏噓。這一個個人物在慶邦的筆下是鮮活的、生動的、豐滿的、個性鮮明的。這部小說的人物幾乎全是青年礦工,他們是上山下鄉和回鄉的知青,由于發展工業和煤礦建設的需要,他們從農村、農場來到礦山,成為一名建設者。他們身上帶著那個時代的深深烙印,有著各自不同的出身和經歷,各有各的愛好,各有各的心思,各有各的性格。《女工繪》塑造最成功的人物無疑是主人公華春堂。華春堂是工亡礦工的女兒,家庭的磨難加上姐姐無心無能,讓她小小年紀就成為家里的主心骨。她堅韌頑強,不向命運低頭,不服輸,不怯場,工作、生活、婚姻的目標都是更高,更好,最好;她精明過人,諳熟生存智慧,一心一意攀高枝,但不傷害他人;她慮事嚴謹,心細手巧,善解人意,能屈能伸。參加工作一報到,她就敢于與人事科長討論選擇自己滿意的工作崗位;她通過自己的努力如愿進入宣傳隊;宣傳隊結束,她又通過自己爭取調到化驗室;她靠自己的主動和誠意交上來自省會鄭州出身知識分子家庭的男友李玉清。天有不測風云,在李玉清工傷亡故后,她向前途無量的魏正方發起進攻,未獲成功后她又追求全礦最高的籃球隊員卞永韶,如愿以償。
華春堂最后死于一場意外車禍,香消玉殞,這場悲劇是一個偶然事件。不說這場意外,華春堂的人生是成功的,她想做的事,想達到的目標幾乎全部實現。她短暫的一生堪稱精彩,比她的那些同學、工友都強。
然而,我認為華春堂是一個悲劇人物。她的悲哀不在于一場車禍,而在于她個人的經歷和自身性格的缺陷,同時也是時代的悲劇。她個子矮小,沒有突出的音樂舞蹈天賦,偏偏使勁擠進宣傳隊,到了宣傳隊并無突出表現。她文化水平不高,沒讀過幾本書,不知道賈寶玉。劉德玉說出的“一文不名”不知道什么意思,連一封求愛信都寫不來。為了體面千方百計調進化驗室,來后沒見她學習過業務,也未見有什么長進。她把出身和來歷看的比什么都重要。得意于自己的好出身,對家庭出身不好的工友看不上,羨慕大城市的孩子。
華春堂的價值判斷和做出的選擇是現實主義的、甚至是比較世俗的,這些來自于她的過于自負,來自于自身缺乏自知之明,更是她不甘寂寞、爭強好勝、愛慕虛榮性格的表現。從找男朋友的過程充分說明這一點。找對象是要找一個愛和被愛的人,找一生的安全和幸福。而她一看家庭出身,二看來自哪個城市,然后才看他是誰,愛、感情在她心里排不上位置。在第一個對象李玉清工傷身亡,追求魏正方未果的情況下,最后賭氣把身高作為擇偶的唯一標準。
到了這里她性格的弱點終于徹底暴露出來。在她看來,她所有要做的事都達到目標,魏正方竟然以個頭矮為由拒絕自己,那我就找個全礦第一高給你看看。熟知,她與卞永韶走到一起成為一個笑話,試想這樣的婚姻將來能保證幸福嗎?
總之,華春堂是一個性格復雜、充滿矛盾的人,她堅強、聰明、能干、有進取心,但過于敏感、算計、虛榮、經不起挫折,這會不會為她的人生埋下悲劇的種子呢?當然我們永遠也不得而知了。
書寫女性、關注女性是慶邦創作的一個重要特征,在以往的創作中,塑造了一批性格鮮明各具特色的女性人物形象,這些人物傾注了作者深深的愛和悲憫之情。華春堂不同于《清湯面》中的向秀玉和楊旗,也不同于《黑白男女》中的衛君梅,她是慶邦筆下女性形象的“這一個”,值得我們細細品讀和琢磨。
劉 俊
(中國煤礦文聯特聘副主席、中國煤礦作家協會副主席)
自從離開煤礦之后,通過慶邦老師的小說回到我所熟悉的煤礦,要比我親身到煤礦的次數多得多,慶邦老師的新作《女工繪》,就帶著我再一次回到了那塊曾經魂牽夢繞的黑土地。小說里的金寶礦務局,在我的腦海里會置換成大同礦務局,小說里的東風礦,也會置換成我最初參加工作的王村礦。礦機關辦公樓前的馬路,就如同小說里描寫的一樣,只要拉煤車一過,即刻塵土飛揚。我自己的經歷,也和小說里那個男主人公魏正方大致相同,因愛好寫作而從井下調到井上,繼而調到礦機關、局機關。小說里的諸多女子,我也會在現實的礦山里,從女同學、女同事及礦工家屬身上找到她們的影子。礦山詩人桑俊杰曾說,《女工繪》是夢回青春、夢回礦山的一次文學浮世繪藝術大展,我以為這個比喻非常準確、貼切。
《女工繪》是一部以煤礦女性為題材的長篇小說,作家以女主人公華春堂為人物線索,講述了她身邊的眾多女工在剛參加工作之后,面對陌生的環境、復雜的人際關系所展示出來的焦慮、彷徨以及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我認為《女工繪》里的女工們不同于歌曲里唱的那種詩化了的礦山女人,也不同于在礦井口為下井礦工端茶送水送鞋墊的礦嫂式的礦山女人,更不同于推著輪椅,含辛茹苦照顧工傷丈夫的礦山女人。勞動布做的工作服,包裹不住她們或豐潤或婀娜的身姿,礦區上空飄灑的煤塵,遮掩不住她們容光煥發的臉龐。她們是一群迸射著青春活力的女子,是被礦山的風薰染了的具有煤的秉性的女子,是以黑色為主基調的礦區里一道賞心悅目、靚麗多彩的風景線。獨立自主、心思縝密的女主人公華春堂自不必說,含辛茹苦養育一男兩女的華春堂的媽媽,軟弱、謙讓的華春堂的姐姐,華春堂的室友陳秀明、唐慧芳,華春堂的同學張麗之、王秋云、楊海平,華春堂的同事周子敏,這些小說里的女工都栩栩如生、躍然紙上,給讀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就連傻明、鄭大姐、褚桂英、李玉清的姐姐,雖然著墨不多,但也性格迥異,格外傳神。在品讀《女工繪》的時候,我常常會想到《紅樓夢》里的那些女子,只不過場景變了。這里不是大觀園,也沒有怡紅院,吃的不是山珍海味,穿的不是綾羅綢緞,在“文革”末期依然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大背景下,在礦區條件艱苦、物質匱乏的大環境下,這些年輕女工的天性并未被完全束縛,她們的精神世界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愛心、友情、賢惠、活潑、聰穎等女性美得到了充分的抒發。對這群女工,作家并沒有居高臨下地給出價值判斷或社會批判,甚至看不到作家“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責怪和抱怨,因為在慶邦老師看來,“每個青年女工都有可愛之處,都值得愛一愛”。同《紅樓夢》結局充滿了悲情一樣,《女工繪》的結局也令人扼腕嘆息,作家在女主人公談婚論嫁的時候將其置身于重型拉煤大卡車的車輪之下,在殘酷的情節里敘述著人間的大喜大悲,在充滿震撼力的真實中,尋找著礦山女性精神的自由和自在。
與其說喜歡慶邦老師的小說,不如說喜歡慶邦老師的文字更為準確。慶邦老師的文字有其獨特的魅力。有一段文字,用在慶邦老師身上極為準確。“行文簡練而意蘊豐富,樸素的外表之下是內在的單純與明凈,簡單的對話如高手過招般盡是機鋒,尤其是敘事節奏的控制與敘事氛圍的營造,整體結構的布局與具體層次的分布,無一例外地顯示作家在小說藝術上的精深造詣與杰出成就。”從慶邦老師的文字里,可以看到錢鐘書的幽默,沈從文的憂郁,汪曾祺的隱秀,孫犁的清新。與外國作家相比,同樣是煤礦題材,不去追求戲劇性的曲折變化,只追求人物的氣質特點和精神心理,這一點有點像左拉,而他對男女性愛的描寫,不像勞倫斯那么激情、直白,而是更含蓄、內斂、細膩,也更值得品讀和回味。《女工繪》里很少寫到煤礦井下的場景,但卻到處充盈著煤礦的氣息。第三章就是作家繪制出的一幅礦山風俗畫。礦區物質雖然匱乏,但青春的氣息無處不在,這種氣息是通過礦山的文化、礦山的藝術呈現出來的。礦工們來自城市或是農村,男女性別不同,招工的批次不同,文化高低不同,家庭出身不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都處在青春期,用現在時髦的話說,到處是行走的荷爾蒙,到處散發著雌激素。在這一章里,那個年代煤礦普及的,司空見慣、耳熟能詳的,如體育類的籃球、乒乓球,文藝類的手風琴、二胡、口琴、笛子等,都囊括其中。讀罷這段文字,再閉上眼睛,腦海里頓時浮現出籃球場上生龍活虎的身影,耳畔定會回響著或高亢或悠揚的樂曲。這一章沒有對話,只是對礦區新招工人的地域分布、人員構成進行散文式的介紹、分析,行文流暢而不失情趣,看似平實卻意味深長,而且還發揮著對后續情節的推動作用(籃球隊員之于華春堂的對象,音樂之于宣傳隊成立)。而華春堂之死,雖然慘烈,但并沒有讓讀者感到突兀,這是因為作家從第十章王秋云回家路上被大卡車逼停在路邊開始,多次在之后的章節里描寫了運煤卡車對路人的危險之舉,這種鋪墊不露一絲痕跡,卻是匠心獨具。華春堂向魏正方借閱《紅樓夢》,也不是作家隨便拿來就用的道具,它在小說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隱含女工生活工作的礦區就是大觀園的女兒國之意。《紅樓夢》是曹雪芹的女兒國,《女工繪》就是慶邦老師的女兒國,我甚至覺得華春堂身上有著王熙鳳的影子,為人作事有著王熙鳳的風范。這種經過審美處理的情節安排、細節描述、伏筆預設,看似漫不經心,卻極見功力。
“地下生煤,地上長莊稼。礦工在地底挖煤,農民在地表種莊稼……礦工用礦燈指出一線光亮,走在井下縱橫交錯的巷道里,以為自己已經走得很遠了,出得井口稍一眺望,不遠處就是農村的莊稼地。地下的煤都是黑的,黑得一成不變。而莊稼剛出苗時都是綠的,一成熟就變成了黃色,黃得遍地流金,浩浩蕩蕩。”這一段描寫,既是《女工繪》的開篇,也是慶邦老師整個創作生涯的真實寫照。縱觀慶邦老師半個多世紀的創作,幾乎一直是交織于黑土地與黃土地之間,正如著名評論家雷達先生指出,劉慶邦的小說是農村題材與煤礦題材的輪唱,季風與地火的交響。農村和煤礦,都是慶邦老師所親歷、所熟悉的,都是中國的現實,而煤礦是最底層、最嚴酷的現實。經過數十年的思考和藝術審視,已經沉淀出思想厚度的《女工繪》,正是這樣一部反映煤礦現實、真誠袒露自我的非虛構實錄,是一部唱響那個時代的青春之歌,必將在中國煤礦文學史及中國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桑俊杰
(作家,中國煤礦作家協會原副主席)
很難想象,當今中國哪一位作家,能把長中短篇小說,如魚得水地由必然王國向自然王國,寫的如此風生水起。很難想象,一個小說寫作家,煤礦文學作品在其一生的創作中,占有如此重大的比重,除了被冠以短篇王,還被稱其為中國煤礦文學作家第一人。
如果說,劉慶邦的小說寫作,所關注的一直是生活底層的人和事。那么,其新出版的長篇小說《女工繪》,則更是從后知青時代,礦山女工青春史話的鉤沉中,用對青春致敬和祭奠之筆,向讀者充分展示了煤礦底層,鮮為人知的社會小人物命運,與對生活和愛情向往的艱辛過程。
回憶是作家寫作生涯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能在半個世紀后,用文學之筆把那個年代的人和事,原汁原味地呈現給讀者,除了作家非凡的記憶,還要靠作家卓越的寫作才華。劉慶邦坦言作品中有自己的影子,坦言因為愛她們,所以才寫她們。劉慶邦寫她們青春的年華,也寫她們青春的傷痕。因為,那個階級斗爭天天講的特定歷史年代,極左思潮和荒謬的行為,對人性的摧殘和思想的禁錮,是令人難以抗爭的。
劉慶邦《女工繪》筆下的人物是鮮活的,性格是鮮明的,盡管相同的青春年華,各自有各自不同的身世背景和對生活的憧憬。但她們走入煤礦,都不失為那個年代以黑色為基調的礦山,一抹生機盎然的新綠。盡管她們走進礦山穿的是勞動布做成的工裝,但是粗糙的勞動服掩不住她們的青春之美。她們的走入使原本是男人世界的煤礦,增添了使雄性荷爾蒙躁動的青春氣息。劉慶邦的寫作意圖顯而易見地告訴讀者,他就是要把那個年代心中沉積的愛,用審美的表達寫出來,盡管這種審美的表達,寫得不時伴著難以平復的心痛。
《女工繪》里,華春堂是作家筆下,貫穿始終的一個與命運頑強抗爭的藝術典型。她青春向上,追求美好,卻又充滿心機,不甘人后。礦上成立宣傳隊,走資派的女兒周子敏進去了,家庭成分不好的陳秀明、張麗之也進去了,最后連有隱私的王秋云和楊海平也進去了,只有歌唱好的華春堂沒人問津。這讓自信的華春堂不可接受。然而,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華春堂,最終還是抓住了讓宣傳隊長魏正方認識自己的機會,被招入了宣傳隊。在宣傳隊里,華春堂從對魏正方能力和才華的佩服,逐漸情竇初開,通過幫助魏正方打掃房間,向其示好。但魏正方接下來的行為,讓華春堂感到了一種拒絕,懂得堅守自尊的華春堂告誡自己,再也不跨入魏正方的房間,除非魏正方邀請她。
但是,這樣一個懂得自尊懂得追求美好生活的女性,卻被命運捉弄的一波三折。被魏正方拒絕之后,她好不容易與有知識分子家庭背景的李玉清確定了戀愛關系,可李玉清卻因為井下事故工亡了。本來李玉清已經接受了華春堂的邀請,大年三十會跟華春堂去她家過節,華春堂已跟母親商量好了接待李玉清的方案。除夕要給李玉清包餃子,還要做六個菜,請李玉清喝一點酒。然而李玉清過小年這天在井下出事故死了。似乎冥冥之中有預感,她曾多次對李玉清囑咐過,在井下一定要注意安全,因為井下事故不長眼,李玉清說自己一定會注意安全,請她放心。可李玉清還是沒有躲過井下事故這一劫,被運煤的溜子卷死了。華春堂與李玉清剛剛燃起的愛情火苗,就這樣被突如其來的噩耗無情地毀滅了。或許華春堂就是一個心比天高命比紙薄的悲劇典型。在接下來與全礦第一高度卞永韶的相處中,本來已經辦理了結婚登記手續,快到了談婚論嫁的日子,華春堂卻因為一場意外的車禍香消玉殞。毫無疑問,作者筆下的華春堂,是一個充滿悲劇色彩,且令人扼腕憐惜的悲情女性。
魯迅說,所謂悲劇就是把美好的東西撕碎給你看。與其說劉慶邦的《女工繪》所展示的是華春堂們豆蔻年華的青春,不如說是作家在用記憶與思想的利刃,解剖著那段灰暗的歷史年代,給人們帶來的靈與肉的摧殘。在當代中國作家群里,劉慶邦堪稱是寫悲劇高產作家。這一點從其作品中可以得到很好的印證。劉慶邦寫煤礦的作品,大多是在揭示人性的丑惡嘆寫命運的悲劇。諸如他的成名之作《走窯漢》、被改編成電影《盲井》并榮獲第53屆柏林電影藝術節銀熊獎的中篇小說《神木》等等,正是這樣,他的作品才對閱讀構成了力量的誘惑,才會在國內屢屢獲得各種文學大獎。
劉慶邦通過《女工繪》的寫作,打開了人們塵封半個世紀的記憶,使同齡人看到了自己曾經熟悉的那個年代,使后來人了解了那個時代人的生存與渴望,了解了那個特定歷史年代,對人性的制約和壓抑。使閱讀者驚心動魄,愛不釋手。這一切都源于作家細膩的文筆,詩意的描寫,現實的表達 ,憤怒的傾訴,悲憫的情懷和對青春美好的向往。比如他用細膩的文筆書寫著作品中的每一位女性,寫她們面對生活和命運積極向上的態度;比如他對礦山對農村景物及時節的詩性語言的描述;比如他對男人不在身邊女性,呈現的生理需求的特殊處理表達;比如他筆下的魏正方面對政工組長無情打擊,所反映的不屈與抗爭;比如他對筆下的女工們愛之痛的心里悲憫感受,訴諸文學語境的描寫;比如他寫礦山黑白世界黑白男女們,對青春向往的點點滴滴,都構成了對讀者巨大的閱讀誘惑。用茅盾文學獎得主,著名作家李洱的話說,劉慶邦勾起了自己對青春的記憶,能把20世紀70年代的社會結構,人的情緒和倫理關系等,在作品中有著非常鮮活精彩的呈獻,可謂纖毫畢現。表現出了作者對生活細節的驚人的記憶力,同時應該感謝劉慶邦,他用驚人的記憶力,為我們還原了那個久違的歷史年代,和那個歷史年代的礦山底層人的生活狀態,再現了一群風華正茂的煤礦女工,命運多舛的青春。把她們用愛之筆,永遠定格在那個令人難以忘卻殤情的歷史年代。
付曉豫
(博士、應急管理部培訓中心副處長)
慶邦老師的《女工繪》繪出的這幅畫,是暖暖的橙紅與冷峻的藍綠之間的撞色,總的基調卻呈現出一種灰,好像是有點心灰意冷的“灰”,年代久遠的老電影的那種畫面。這是一種“高級灰”,沉穩、高貴、永不過時,平和而詩意地在青春的欣喜間,透出深深的悲傷。當然,也許這種悲傷只是我這個讀者自己的悲傷,不同的人看同一部作品,會看出不同的情意來。但是在我們目前的浮躁的生活里,無論是喜是悲,都是一種寶貴的動心動情,值得珍惜。
生活是美好的,又是殘酷的,在慶邦老師后記中的“愛她們”的表述中,美好事物的最終逝去正是這殘酷的注腳。這是交織著愛的一個無奈的世界。但中國人只說“否極泰來”,不說“泰極否來”,在小心與善意背后,隱藏著生活的辛酸。
小說的主人公華春堂,一個本性善良、也頗有心機的女孩子,有的時候讓人贊賞,有的時候讓人不太贊賞。喜歡不喜歡她,正像喜歡不喜歡我們自己。其實女孩子們內心大都會愿意做她那樣的人,因為她身上充滿著向上的氣息,散發著活潑的生命張力。從故事開頭兒的包粽子開始,她說的那個話:“吃不吃棕子在其次,包粽子包的是節氣,一包就把節氣包住了。”這就奠定了她作為故事主角兒的一種氣度。正是通過她,慶邦老師提醒了我們,無論怎么進取、成功,宿命的安排是誰也逃不過的。
不管在哪個年代,作為人,對生活的欲望也好、向往也好,在方向上都是一致的。像華春堂,包括魏正方這些人,他們雖然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一座煤礦,但是今天在北漂的年輕人身上,我們又何償不能看到他們的影子呢?但在我們今天的許多人身上,又何嘗沒有看到他們的影子呢?是煤礦,又是一個廣闊的社會;是那個時代,也是每個人追憶的人生片段。
作品的敘述舒緩從容,故事性卻很強,吸引人一口氣地讀下去。寫作的手法很樸實、很傳統,就好像是手工制作的那種精品。閱讀的時候,絲毫不覺得那些優美的一段又一段的文字散漫,文字中呈現的特殊的美,仿佛正是為了匹配這個故事,是跟著這個故事與生俱來的。
我看到很多寫作的人都很有理想。尤其是今天有了電腦和互聯網,打字的速度更快,查閱資料更方便,這就使得人們的理想更加宏偉了。多少人都夢想著寫一部當代的《紅樓夢》,尤其是寫長篇的時候,這種愿望會更加強烈。但是別人還在做夢的時候,慶邦老師已經編排好了“正冊”、“副冊”、“又副冊”。表面上只是一座煤礦的一群人,而且主要是女工,但卻寫出了煤礦人的整體性格和煤礦人的整體命運,不,這樣描述不夠確切,應該是說寫出了真正的“人”,全方位的、立體的“人”,他們的奮斗、無奈、渴望、焦慮、隱忍……這一切感受,跨越時代,跟今天的生活高度吻合。
現實主義作家的作品,往往都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自己是把《女工繪》當作那個特殊時期的煤礦歷史來讀的,是用非常具像的、生動的描述手法來呈現的一段歷史。馬克思1854年的一篇文章中說過,英國以狄更斯為首的一批小說家,“他們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寫生動的書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會真理,比一切職業政客、政論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還要多。”
小說讀完了,我的心卻仍然停留在“地下生煤,地上長莊稼”的那個地方。順帶說一句,我不滿意那個結尾,被那個噩耗狠狠地打擊到了,非常失落。我想抱怨一下,但應該抱怨誰呢,想來想去,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對接下來的命運都沒有做好準備。要非常感謝慶邦老師的提醒。
姚喜岱
(作家、中國煤礦作家協會原秘書長)
我們一家三口都是從煤礦出來的。我在京西煤礦工作了21年,上世紀90年代初攜妻兒從煤礦回歸京城,算上調入煤炭報社工作的時間,我已在煤炭行業足足浸淫40年。劉慶邦這部小說雖寫的是中原煤礦,但與我所在的京西煤礦生活絲絲入扣。我和劉慶邦都在煤礦工作多年,妻子也是礦工子女,后來又在報社共事,同在副刊部工作。他寫的書我覺得特別親切,貼近煤礦生活,原汁原味兒,溫暖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