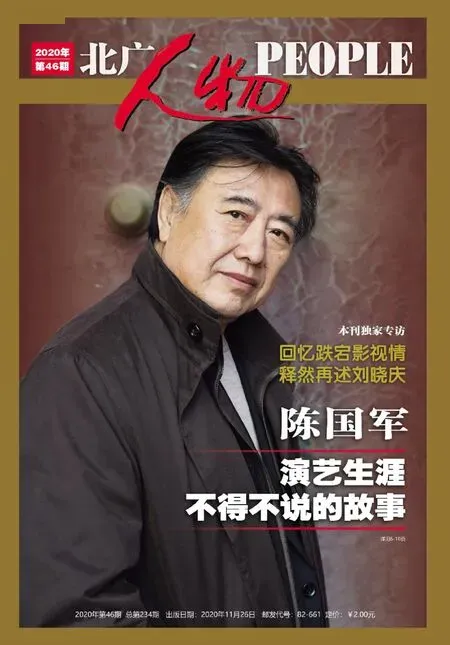錢世明:大隱隱于市
韓小蕙


在人際交往中,我們都見過這樣兩種文化人:第一種,琉璃球,表面上花里胡哨,晃人眼目,實則內心是一塊死疙瘩,什么學問也沒有;第二種人,悶葫蘆,表面上青青白白不見色,內心里實實在在有造詣,是真正的飽學之士。而生活常常跟我們開玩笑,把第一種人推到榮譽的寶座上,什么“鴻儒大師”“著名學者”“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專家”……一頂頂高帽全被他們搶到手;而對第二種真正的學問家呢,則讓人隱忍,苦熬苦干,嘔心瀝血,把艱難的書生路留給自己,把名譽、地位、享受、好處讓給別人。古往今來,代代年年!
這樣的兩種人,你愿意做哪種人呢?
本文的主人公——雜家錢世明先生,義無反顧選擇的是第二種。
上篇:扎扎實實做學問
什么叫雜家啊?
雜家就是實在不好用一種、兩種或三種名銜歸類的一家——人稱“文壇怪杰”的錢世明,當年我采訪時64 歲,是北京藝術研究所的研究員。怎么“怪”呢?單看其開設的課程,計有:周易、儒學、藝術欣賞、文學創作(包括舊體詩、新詩、小說、劇本、兒童文學等);其授課的經歷計有:在北師大、外交學院、外語學院、戲曲研究所、戲曲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講授儒學、易經、佛學、戲曲美學、音韻學、古詩詞欣賞等;其主要著作計有:詩詞文集《大明詩稿》《望汾樓詞》《大明古文稿》《錢世明詩詞選》等,學術著作有《儒學通說》《易象通說》《易林通說》等,長篇小說和中短篇小說集有《穹廬太后》《李清照》《玄奘傳》《原上草》等,劇本有昆曲《辛棄疾》《東行傳》、木偶劇《大鬧天空》(獲1978 年南斯拉夫國際戲劇節最佳節目獎)、京劇《梁祝》《風雪寒江恨》等;他還曾在北京舉辦過《錢世明詩書畫印展》……你道他不是雜家,還能怎么歸類呢?


而且,錢世明的學問是真學問,不像有的人雖然著作等身,卻是東抄西抄拼湊出來的。有時候,他還特別愛“較死理”,比如有一次,一位著名老詩人寫了幾首古體詩,別人都吹捧不迭,錢世明卻率直地指出:“他那韻都用錯了,說明他肯定是不懂古音韻學的。這也是現在詩壇的一個流行病,人皆以為寫古詩只要掌握平仄、對仗就行了,殊不知平仄是好掌握的,聽一次課就能學會;而平水韻的106 個韻部,今天卻沒有幾人肯下功夫研究了。”
說著說著,他激動起來了,也不管周圍都有誰,竟自大聲說:“這么著名的老詩人,其國學底子尚且如此單薄,今人的學術水平實在是令人擔憂啊! ”為此,他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呼吁“研究國學必須從識字開始”,首先得通“小學”——“小學”者,文字、語言、音韻之學也,乃國學研究的基礎之學。錢世明說,這不是聳人聽聞,而是必須實實在在下的苦功夫,不然,急急慌慌忙著發表論文,著書立說,可是他們連字都不認識,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音都念不準,這不是笑話嗎?
錢世明說:《十三經注疏》《史記》《漢書》《五臣注文選》《經典釋文》《一切音經義》……這些基本的典籍,你都得通讀啊。我聽學生告訴我,說現在的小青年,碩士、博士寫個論文,連書都懶得打開,只在網上動動鼠標,摘抄幾句他用得著的話,就糊弄過去了,這不是既騙別人又騙自己嗎?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錢世明就是看不得國學“受委屈”。別的什么都好說,但你若是當著他的面“黑”中國傳統文化,他那張老是笑嘻嘻的臉頓時就黑下來,管你是天王老子,也不饒過你。上世紀80 年代中期,正是現代詩崛起的風頭時期,一個詩歌討論會上,有的慷慨激昂的“先鋒詩人”越說越走了板,居然渾說“從屈原到郭沫若,整個中國詩壇都是一條干涸的河流。”錢世明不干了,一如大河開閘地開了講,不但用中國圣賢們的例子加以批駁,還“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學著“先鋒”的路數大談西方詩學和美學——蘇珊·郎格是怎么怎么說的,科林伍德是怎么怎么說的,克萊夫·貝爾是怎么怎么說的,他們的話是在哪本書、第幾頁、第幾行,你們好好讀去吧! 結果,當場把“膽大妄為”的后生小子們震住了,技(學問) 不如人,誰也不敢“叫板”了。會后,有心人還真的去查了第幾頁、第幾行,果然一點都沒錯。
有人說錢世明有特異功能,最早讓人領教是在20 世紀70 年代,那時“文革”還未結束,有日本學者來北京訪問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座談時,人家提到清代一位不怎么有名的詩人,故意只說號不說名字,結果在座的中國專家面面相覷。有關負責人給錢世明打電話,錢先生當即說出此人是誰,他有什么著作,其詩集的名字是什么。負責人大喜,說小錢你趕快下點功夫把清詩弄弄清楚,我把你調到我們所來就負責這段的研究。當時錢世明剛三十出頭,還正在木偶劇團當編劇呢,他拔腳就上北圖借了一部《清詩選》,花了一個禮拜時間,從第一首背到了最后一首。
到現在,錢世明居然還能把解放前的小學國語課文背下來,至于古文典籍,更是張嘴就來。他講課從來不用講稿,滔滔如江河之水,隨手拈來。有時突然忘了,一閉眼一拍腦門,那書、那詩文就全在眼前“現身”了,就像能看見一樣。其學問之好,用已故老作家嚴文井先生的話說:“現在怎么還有你這樣的年輕人?”
錢世明說,其實我也是普通人,絕沒有什么特異功能。我不過是要求自己把學問做扎實了,別那么浮皮潦草,讓人笑話! 我這記性也差著呢,今早上吃的什么早忘了,帽子呀、車鑰匙呀不知丟了多少次!
不蒙人,不蒙事,不蒙學問,這是錢世明做學問的三條金原則。要讀圣賢書,先做圣賢人:焚香沐浴,敬惜字紙;以學治愚,死而后已;夙興以求,夜寐以思;惡不可積,過不可長;以銅為鏡正衣冠,以人為鏡正言行……這些“規矩”都是不能破的。連他的學生也不能破,連他的朋友也不能破——那日我在他家小坐,他拿出沈從文先生給他的信讓我看,我隨口念道:“……蔓(Man)延”,不等我念下去,錢先生就糾正說:“不是Man, 應該是Wan,古音都念Wan, 指爬蔓兒的藤科植物。《左傳》里有‘蔓草難圖’,《廣韻》解‘蔓’字是‘無販切’。大蔓大蔓,應該就是這個蔓,現在都寫成大腕,錯了,意思不通呀。”
我說哎喲真慚愧,我真是只知其“Man延”,從不知其“wan 延”,我還是正牌大學中文系出來的呢,老師從來沒提起過,字典也都是這么教導我們的。
錢先生說,現在真的是謬誤甚多。比如“栩栩如生”,莊子的原話是“栩栩然,蝴蝶也。”其“栩栩”是“歡暢、高興”的意思,莊子是說自己變成蝴蝶后,就像飛翔的蝴蝶那么歡暢和高興。但是現在都給解釋成“如同活的一樣”,到處亂用。早年是嚴文井告訴我,葉圣陶先生對此濫用提出過不同看法。
下篇:久久長長做賢人
幸虧錢世明是個散淡的人,又是一位保持著天真、童趣的“半癲”。他活得可瀟灑了,興致來了,一個人在家里又唱又跳,“玩”得極開心;碰上對心的朋友,手舞足蹈沒個正形。他有著自己的一片爛漫、瑰麗、獨立的內心世界。
著名俄羅斯文學專家藍英年先生曾著文,說剛剛去世的張中行先生家是他“到過的最簡陋的住宅”;套用這個語式,錢世明家也是我的文人朋友們最簡陋的住宅。渾身是真學問的錢世明,卻還住在北京東直門內一座簡陋的居民樓里,兩室一廳,也就六十來平米吧。四白落地,原裝的鐵窗,原裝的木門,原裝的廚房水池、衛生間馬桶,原裝的燈管,只在洋灰地上鋪了一層薄薄的瓷磚。暮春時分,外面已是暖陽高照,屋子里因為是一層,卻還有一股股寒氣直浸體內,小坐了也就兩個來小時,竟使我的感冒加重了。
就說君子固窮吧,在改革開放已28 年、全民奔小康的21 世紀的中國北京,君子也不該“享受”這待遇呀! 我忍不住一遍又一遍跟錢先生說:“您得買塊地毯墊在腳底下,不然寒氣浸身,容易得關節炎呀! ”
他“唉,唉”地答應著,轉瞬,又把他的“寶貝”們抱出來,讓我一飽眼福。
善本書——一函一函的,都是用藍布包面的硬殼套著,一邊一枚小小的象牙扣,像忠誠的國門衛士一樣盡職,竭力把歲月的灰塵鎖在外面。最珍貴的一套是明萬歷年間版的《戰國策》,紙都已經發酥了,碰都不敢碰,而墨跡卻依然清麗,漂亮極了。還有清代的一些版本,有《詩經》《聊齋》什么的,都是雕版印刷,一函函被精心置放在一個頗有年紀的大書柜里。
這些都是錢世明祖上留下來的藏書,“文革”時候被“掃地出門”,集中拉到北京體育館的院子里,后來被他悄悄“盜”回。“這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都沒搶救回來,可惜呀!”
錢世明是世家出身,祖籍浙江山陰(今歸紹興市),曾祖父是咸豐乙未科進士,后任工部主事,全家遷居京城。錢家在前門外大柵欄附近的櫻桃斜街買了一個大院落,后來八國聯軍屠戮北京,兩位老人雙雙含恨身亡,子孫慢慢敗落下來。錢世明5 歲上學,7 歲喪母,一直跟著外祖父母長大,所居之所在北京崇文門外的一所大宅院,今已不存。三進院落,兩側廂廊,青磚漫地,草木森然。家中人口少,只他一個小孩子,有時小錢世明坐在院子里讀古詩,讀著讀著就覺得瘆得慌,下雨時,更讓他聯想到《西廂記》《白蛇傳》等戲曲里的情景……
錢世明還記得清清楚楚,7 歲時,他讀了人生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濟公傳》。他太佩服濟公了,別看他穿的是破衣裳,可他一拍腦袋,佛光、金光就出現了,行俠仗義,替人解危救難。當時小錢世明就領悟道:越有本事的人越有內涵,越應該謙虛……
世事無常。五十年以后,坐在他當年的陋室里,已是兩鬢見白的錢世明,又一次談起這位他人生中的第一個“大英雄”,同時解讀著自己:
——“我這輩子最不把錢放在心上,每個月3000 多塊錢退休金,夠吃夠喝,足矣。那年張火丁托人找我給她寫個本子,我喜歡她的戲,就答應了。我是邊唱邊寫,按譜填詞,實打實用了3 天時間,就把本子拿出來了。這之間張火丁好幾次打電話來,非問我要多少稿費不可?我一聽腦仁兒就疼,說不要錢……”
——“誰來了都問我為什么不裝修?我是真不講究,從小那么寬敞的院落都住過,現在還在乎這小鴿子籠?對吃、穿、住、用,我都隨便,家里給做什么就吃什么,給買什么就穿什么,我自己從來不去商場,只去書店和琉璃廠……”

——“我為什么能淡泊名利?我認真想了想,有三個原因:一是從小受的教育,就是踏實讀書,一心不能想別的。我還記得自己讀的第一本書是白話《世說新語》,那里面‘陳平渡江’、‘管寧割席’、‘赤眉軍不打鄭玄宅’的故事等等,對我的教育極深。二是我外祖母對我的管束很嚴,從小就教育我不許動別人的東西,不許眼紅別人家有什么,不許挑吃挑穿,這些都給我打下了極好的人生基礎。三是我崇拜孔子,把他的一句話作為終生的座右銘:‘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不足與議也。’”
——“我這輩子最尊重的是什么人?當然是有真學問的人。打我年輕時起,就只愿意跟老先生們來往,上人家家里請教去,進門只談詩、詞、文,從來不閑扯別的。老先生們對我都非常好,手把手地教,像王昆侖先生、沈從文先生,給我寫信談劇本、談詩,都是用毛筆,一寫好幾頁,那做學問真是一絲不茍。冰心先生九十多歲動不了了,還重讀《十三經注疏》。1995 年,臧克家先生90 大壽,寫了一篇短文《說夢》,還寫信托我查‘損夢齡’之說到底是出自周武王,還是后人黃山谷用了‘夢齡’的典故之后才有了此說?……”
最讓錢世明一輩子銘記于心的,是他的老師田名瑜老先生的一件逸事:田老先生是著名的鴻宿大儒,解放初期共產黨進北京城,毛澤東主席曾在中南海宴請兩位文化名人,并親自為二老操槳劃船,其中一位是他的老師,另一位就是田老先生。“文革”期間,田老住在一間只有六七平方米的小平房,這對年事已高的老先生來說極為困窘不便,黃永玉就出了一個主意,請田老給毛主席寫信,田老先生斷然拒絕說:“孩子,讀書人不興那樣做。”……
這一點一滴的言傳身教,好比春風化雨,點點滴滴全被錢世明吸納到自己的心田,滴滴點點照著去做,幾十年來從不敢懈怠。他覺得苦嗎?不苦,凡圣賢都是如此,安貧樂道,死而后已;他覺得難嗎?不難,君子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省之。況錢世明是天性使然,一輩子追求的就是讀圣賢書,整理和研究中華文化,沉浸其中,熏熏然,悠悠然,津津樂道,甚至是“五迷三道”。有時讀書讀得興奮了,就手舞足蹈地來上一陣“老夫聊發少年狂”,然后沖著外部世界“嘿嘿”一樂,曰:“妙處難與君說”呀! 還有時興致來了,大早起來就上地壇公園拉胡琴玩,搖頭晃腦,自得其樂,常去那里遛早的人都認識他。
那年春節,一位當了大官的熟朋友來家給錢世明拜年,老伴兒說他“出門吃飯去了,馬上就回來。”等了七八分鐘,就見他騎著他那輛舊自行車,邊唱著戲文邊回來了。見到好幾年沒見面的老朋友,自然很高興,忙不迭道歉:“今天我老伴不舒服,我就自個兒到胡同口吃了一碗鹵煮火燒。”
客問:“怎么還騎車呢?”
笑答:“身體還倍兒棒,就愿意騎車,自在,方便。有一天我一高興,騎著車跑通州大順齋買糖火燒去了,一個來小時就到了。”
客又問:“怎么還住這兒呢,房子還沒解決?”
反問:“都退休的人了,誰還給你解決呀?”
客復問:“錢老師,您現在有什么愿望?”“有,有。”這回錢世明快言快語,一下子打開了話匣子:
第一個愿望:凈化學術。有一天我聽廣播,有一“專家”講《聊齋》,愣說“賈人之子”是姓賈的人的兒子。這從古至今,誰都知道這里說的是“商人的兒子”,商賈商賈,行商坐賈呀,這不是基本常識嗎!連這都不知道,他還敢上電臺去講?又有一次偶然看電視,正有“專家”講古人作品,好幾處講錯了不說,那“專家”還突然冒出一句,說這位古人“裝孫子”,真把我嚇壞了,這種語言實在是欠商量!
第二個愿望:凈化語言。俄羅斯總統普京曾提出凈化語言,我覺得咱們中國的語言環境也存在很大問題。現在好些詞兒都不通啊,比如什么叫“感動”某某地,地名又不是人稱名詞,怎么感動啊?連詞性都不顧了;“時尚”某某地就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還有什么“詩文”某某地、“戲劇”某某地,白紙黑字就那么印,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真是把中國語言都搞亂了。
第三個愿望:收幾個高足。現在讓我苦惱的是,我們單位級別低,我想招收幾個研究生都不行。我真是想把自己懂的這點東西傳授下去,還是有好孩子想學的,中華文化傳統得后繼有人啊。
第四個愿望:自己再抓緊時間多做點兒事。我真是愛國者,太熱愛自己的民族文化了,那年我去俄羅斯文化交流,行前自己把古陶文扎在肚子上了。我高興“安貧樂道”,只是覺得自己的力量太微薄了,中國文化浩如煙海,回頭一看我的那點兒東西,簡直太少了,這輩子能把傳統文化研究出一星半點就知足了。
結篇:留與后人評
在錢世明家四白落地的客廳兼書房的墻上,掛著一幅他的自題詩:“移文好去彥倫前,人靜結廬地自偏。群鵲時臨窗外叫,老貓總依腳旁眠。讀書樂忘暮將至,作畫狂來意在先。即使遷居沂水上,得風不復舞雩邊。”
這即是他當下生活的寫照,也是他的襟懷所向——“自朝至暮,飲食起居,言語動靜,皆所謂學。”滿足于做個純粹的讀書人。
錢世明據實以告:“我想的是不與今人爭,留與后人評,我對自己有這個自信,自信詩必傳世。我曾有一句詩是‘安知千載下,人間不仰首?’有人罵我狂,須知‘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至于那些蒙事的、胡說八道的,雖然見了他們我就腦仁疼,但老老實實的讀書人歷朝歷代都是少數,也不足為怪。我只要求自己‘商歌未云賤,脫穎抱國危’,這是1962年我寫的《呈王昆侖師》五言排律的首句,那年我剛好20 歲,意思是立志做一個真正能為國家做事的人。”
當年,王昆侖先生給年輕的錢世明寫信,稱贊他“不類少年詞語,極有大家氣派。”葉圣陶贊其“詩多巧思。以足下之才,想學生獲益匪淺。”臧克家贊揚他“你,有才華,強記。方方面面都介入,而且成績斐然。”嚴文井更是贊揚他的人品“鄙薄勢利,對朋友忠誠。潛心治學,是典型的學者型作家。”還有章士釗、俞平伯、夏承燾、顧頡剛、張伯駒、錢鐘書等前輩、名家,都紛紛閱讀錢世明的作品,為他的詩稿題字,并欣欣然于“錢世明是青年中不易才也。”(趙樸初語)
四十多年來,錢世明把老先生們給他的這些手跡都珍藏著,裝訂成冊,名為《手教集》。每每念及老一輩大師巨擘對自己的教誨和鼓勵,他都深感知遇之恩,更堅定地在“不求名利,但求學問”的境界中,做一名緊隨其后的薪火相傳者——自古以來,這一脈文人在中華文化的歷史天幕中,層出不窮,群星閃爍,匯成了一條粗粗壯壯的、激情的銀河。
我想起來一個比喻:學界都稱張中行先生為“布衣大儒”,錢世明先生亦是隱于民間的“平民學者”。《昭明文選·反招隱》有句:“大隱隱朝市,小隱隱藪澤。”在萬樓林立、人頭攢動的北京城內,錢世明是一個高貴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