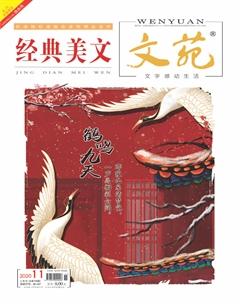從小紅說“奶奶”想到人的口語交際

人 物 檔 案
名片夾:孫志毅,1983年畢業于內蒙古師范大學中文系,曾從事中學教育7年。1991年調入自治區教育廳《內蒙古教育》雜志社做采編工作,歷任副總編、主編,正編審。已經出版《教育的悖論》《做有策略的教師》《教育,就是做好普通的事》等教育專著,在《中國教育報》《中國新聞出版報》《師道》《內蒙古教育》等報刊發表文字五十余萬字。
《紅樓夢》中要論口才好,鳳姐肯定是排第一位的。先看一段出自《紅樓夢》第27回的文字。
(紅玉,即小紅)到李氏房中,果見鳳姐兒在這里和李氏說話兒呢。紅玉上來回道:“平姐姐說,奶奶剛出來了,他就把銀子收了起來,才張材家的來取,當面稱了給他拿去了。”說著將荷包遞了上去,又道:“平姐姐教我回奶奶:才旺兒進來討奶奶的示下,好往那家子去。平姐姐就把那話按著奶奶的主意打發他去了。”鳳姐笑道:“他怎么按我的主意打發去了?”紅玉道:“平姐姐說:我們奶奶問這里奶奶好,我們奶奶還會了五奶奶來瞧奶奶呢。五奶奶前兒打發了人來說,舅奶奶帶了信來了,問奶奶好,還要和這里的姑奶奶尋兩丸延年神驗萬全丹。若有了,奶奶打發人來,只管送在我們奶奶這里。明兒有人去,就順路給那邊舅奶奶帶去的。”
話未說完,李氏道:“噯喲喲!這些話我就不懂了。什么‘奶奶‘爺爺的一大堆。”鳳姐笑道:“怨不得你不懂,這是四五門子的話呢。”說著又問紅玉笑道:“好孩子,難為你說得齊全。別像他們扭扭捏捏的蚊子似的。嫂子你不知道,如今除了我隨手使的幾個丫頭老婆之外,我就怕和他們說話。他們必定把一句話拉長了作兩三截兒,咬文咬字,拿著腔兒,哼哼唧唧的,急得我冒火,他們哪里知道!先時我們平兒也是這么著,我就問著他:難道必定裝蚊子哼哼就是美人了?說了幾遭才好些兒了。”李紈笑道:“都像你潑皮破落戶才好。”鳳姐又道:“這一個丫頭就好。方才兩遭,說話雖不多,聽那口聲就簡斷。”說著又向紅玉笑道:“你明兒服侍我去吧,我認你作女兒,我一調理你就出息了。”
庚辰本與程乙本文字有所不同,但大致意思差不多。
“小紅說奶奶”是一段繞口令,基本可以當作相聲演員的“功課”去練。總共出現了十五個“奶奶”,其中九個指的是鳳姐,其余六個分別指舅奶奶、姑奶奶、五奶奶。這里既有小紅的角度,又轉述平兒的話,還有五奶奶捎來的口信,復雜之極,不仔細甄別,真搞不清這些奶奶誰是誰。
貴族之家規矩多,下人當然不能對主子直呼其名,用的都是身份。這兩段話不僅反映著小紅的靈牙利齒、擅長表達,更符合鳳姐這個文化水平不高、但能力極強的管理者的人才觀——凡可用之人首先得思路明晰、口齒清楚,準確地傳達主子的意思,文化水平高低倒在其次。小紅是賈府管家林之孝的女兒,林家夫妻用鳳姐的話說是“一對錐子扎不出聲音來的天聾地啞,哪承望生出一個伶牙俐齒的丫頭”。可見口齒既有遺傳,也有變異。后來,小紅確實從寶玉房中調動到鳳姐手下工作了。
《紅樓夢》此后對小紅的描寫不多,據脂硯齋評語稱,原本有小紅到獄神廟探望被囚禁的鳳姐一說。
這段描寫對“課改”以來倡導的“口語交際”(語文教學四大目標之一)訓練是頗有啟發的。
“好剛口”(即好口才)的二奶奶鳳姐,基本概括了口語訓練的幾個大要素:說話神態要從容大方,不可“扭扭捏捏”,這與“課標”中所提出的“與別人交談,態度自然大方,有禮貌”同出一轍;一句話不能斷成幾截說,要主、謂、賓一氣呵成;說話要“簡(捷)(果)斷”、響亮明了,達到一定的音量,不能“哼哼唧唧的”“裝蚊子”,這與“課標”中“表達要有條理,語氣、語調要適當”,“做到清楚、連貫”的要求極為相仿;口語表達與書面語不同,不能咬文嚼字、拿腔作調,大觀園內的寶玉和姐妹們交談可以引經據典、一語雙關,可以用借代、拈連、反語、雙關等修辭手法,從而增加不少趣味,也反映著他們的文化修養。但跟丫環、婆子、劉姥姥說話就得直白明了。這不就是“課標”強調的口語交際“要注意對象和場合” 嗎?
《紅樓夢》里有不少“會說話”的小姐丫環,也有不少拙嘴笨舌的人。前者如鳳姐、寶釵、探春、黛玉、劉姥姥;后者如趙姨娘、邢夫人以及那么多的男人。
新課改后,語文教學十分注重口語交際,與以往教學大綱的也提法不同,《九年義務教育語文課標準》(2011版)將先前聽說讀寫中的“聽說”改為“口語交際”。為啥這樣改?已故的丁培忠先生是這樣解讀的:“口語交際是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它不是聽與說的簡單相加。口語交際不僅是語言交際,同時也是情感態度的交流。”
盡管語文教學應該聽說讀寫并舉,不可厚此薄彼,但實際上在應試教育的左右下,多年來聽說能力無法納入書面考試體系,“考什么,就教什么;怎么考,就怎么教”。“口語交際”能力無法考,自然也就無法真正進入教學視野,能力培養自然形同虛設,文字表達還算流暢,但“訥于言”的學生出現自在情理之中。
基于此,我特別佩服那些脫口秀的演員,如楊笠、思文,更敬仰那些演講時出口成章的外國政要。
張志公先生曾在魯寶元的《聽與說》一書的序言中說過:由于孔子說過“巧言令色,鮮矣仁”、“剛、毅、木、訥,近仁”的話,后世儒家誤以為老夫子不講究說話,甚至把不善于說話當成一種美德。其實不然。孔子反對的是口是心非、花言巧語的不好的品質,提倡的是樸實淳厚的好品質。在他看來,聽說能力被邊緣化源自中國人對“會說話”者的偏見。
其實春秋戰國時期,理念仍然是“不學文,無以言”,“言而無文,行之不遠”,誕生出一批侃侃而談、縱橫開闔的演說家、外交家,如蘇秦、張儀、唐雎、魯仲連。中國民間也有“好漢出在嘴,好馬出在腿”的熟語。在當代信息社會,人際交往更頻繁、更便捷,更需要高效。
上世紀八十年代,讀美國作家塞林格的小說《麥田里的守望者》,發現在四十年代的美國中學就開設一門叫“說話”的課程。后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見到一份中國香港的中學語文考題,其中便有“口語交際”的考察:上了公交車,因某事與其他乘客發生了糾葛,你如何傾聽、表達、應對,化解矛盾?
雖說用文字表達考察口語表達仍與初衷有相當的距離,但重視人際交流的語文教學思想值得肯定。我們為何不能在高考試題中加入一點這樣的題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