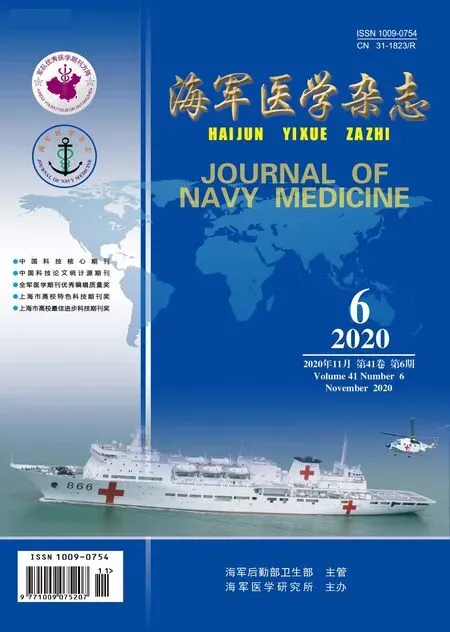右美托咪定與丙泊酚-瑞芬太尼在經皮左心耳封堵術鎮靜中的比較性研究
陳 玲,汪 惠,王嘉鋒
經皮左心耳封堵術(left atrial appendage closure, LAAC)是一項對中高風險的房顫患者以及長期口服抗凝治療禁忌證患者進行的一項手術。手術過程包括經房間隔穿刺,左側附件的血管造影,和封閉裝置的定位[1]。在所有這些操作階段,患者不能有體位的變動,突然的運動會增加包括心房穿孔和心包填塞在內的嚴重并發癥的風險。為了保持患者體位并允許長時間的經食道三維超聲心動圖(3D-TEE)檢查,經皮LAAC通常需要在全身麻醉下進行[2]。全身麻醉不僅帶來了氣道控制、肌松藥殘余及圍術期肺部并發癥等風險,還導致了手術周轉率和費效比的降低。有利的藥理特性如快速起效和蘇醒,使得丙泊酚常與阿片類藥物聯合使用成為介入手術治療期間鎮靜的首選[3]。然而,不良反應如低血壓、低氧血癥和高碳酸血癥被文獻多次報道[4]。由于不具有呼吸抑制和對氣體交換的不利作用,右美托咪定被認為是用于鎮靜高危患者替代丙泊酚的藥物[5]。本文探討了2種鎮靜技術代替全身麻醉用于LAAC術的可行性和安全性的小型實驗性研究。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本研究已獲本院醫院倫理委員會的批準,并與患者簽署知情同意書。本臨床試驗納入行LAAC術患者共60例,采用隨機數字表法分為丙泊酚-瑞芬太尼聯合鎮靜組(PR組,n=30)和右美托咪定鎮靜組(DEX組,n=30)。2組患者一般情況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見表1。

表1 患者一般情況
1.2 麻醉方法 2種鎮靜技術由3名心臟介入手術麻醉主治醫師實施。根據隨機化結果決定鎮靜技術的選擇。所有患者在到達手術室前30 min接受2 mg咪達唑侖靜脈預先給藥。入室后,置入橈動脈導管,通過面罩給予高流量吸氧(8 L/min),常規監測心電圖、動脈血氣及有創動脈壓。PR組患者以1~2 mg·kg-1·h-1開始輸注丙泊酚并滴定以達到中度鎮靜水平,以0.01~0.04 μg·kg-1·min-1輸注瑞芬太尼。DEX組患者放置橈動脈導管后立即以0.7 μg·kg-1·h-1的速率開始輸注右美托咪定;20 min后,將劑量調整在0.2~1.4 μg·kg-1·h-1的推薦范圍內,以達到中度鎮靜水平。
在接受鎮靜的患者中,記錄對鎮靜“補救治療”的需求,并且定義為在該過程期間(由主治麻醉師評估)需要推注給予丙泊酚和/或阿片類藥物的量。通常,在患者不適的情況下,給予丙泊酚以加深鎮靜作用;然而,還建議介入醫生在受影響的一側用1%利多卡因重復局部麻醉。在持續疼痛的情況下,則補充阿片類藥物。“成功的鎮靜性挽救療法”被定義為在不需要轉換為全身麻醉的情況下實現成功鎮靜的情況。
按照ASA的定義,將深度鎮靜作為目標鎮靜深度,并由麻醉科主治醫師進行臨床評估。每位患者的鎮靜水平通過鎮靜警覺評分(observer′s assessment of alertness/sedation scale,OAA/S)進行評估,范圍為0~5,其中0=患者對斜方肌的擠壓沒有反應,5=患者聽見自己名字做出反應。一旦患者的OAA / S評分為1,即置入TEE食道探頭。
介入治療醫生在手術開始時用1%利多卡因10 ml進行腹股溝局部浸潤麻醉。轉換為全身麻醉被定義為圍手術期氣管內插管的需要,但需要排除與手術相關原因的插管病例。手術相關病例原因包括血管損傷、心包填塞、冠狀動脈阻塞和瓣膜栓塞等。
1.3 結局指標 設定2組的主要結局指標為動脈血氣二氧化碳分壓(PaCO2)和氧分壓(PaO2)。其他次要結局指標包括圍術期血管活性藥物使用率、圍術期電除顫及心肺復蘇的發生率。圍手術期低血壓[平均動脈壓低于65 mmHg(1 mmHg=0.133 kPa)]無論何時發生,均用單次5 μg靜脈注射去甲腎上腺素治療。在需要超過5次推注去甲腎上腺素的情況時,開始連續去甲腎上腺素輸注。在同時出現心動過緩(低于40次/min)和低血壓的情況時,或血管加壓藥難治性低血壓(平均動脈壓力65 mmHg)的情況下,給予腎上腺素治療。
1.4 統計學處理 數據經Excel 2003軟件錄入,采用SPSS 16.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組間數據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組間比較采用卡方檢驗。在能檢測到組間5 mmHg差異的前提下,設定檢驗效能為0.8,顯著性水平為0.05,P<0.05表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組患者術前動脈血氣PaCO2和PaO2數值無顯著差別;術后DEX組動脈血氣PaCO2值顯著低于PR組,且動脈血氣PaO2值顯著高于PR組,差異均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2組患者圍術期血管活性藥物使用率、圍術期電除顫及心肺復蘇的發生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PR組和DEX組患者手術及麻醉情況
3 討論
評估左心耳的大小和解剖結構,確認LAAC裝置的最佳定位需要TEE指導。這就需要全身麻醉的配合來減少手術過程中患者的疼痛和不適[6]。然而,這一要求增加了LAAC術的復雜性和成本,同樣重要的是,全身麻醉有一定缺點。吸入麻醉劑可能具有神經毒性,在老年人群中可導致術后認知功能障礙[7]。本研究結果表明,單純應用右美托咪定的中度鎮靜對于促進TEE指導下的LAAC術既安全又有效。
盡管在各項標志性研究中均推薦使用全身麻醉,而在最近發表的歐洲調查中,約有50%的LAAC操作在鎮靜下進行[8]。但這些報道中,沒有關于鎮靜藥物類型,步驟和結果的詳細描述,或并沒有麻醉醫師的現場支持。最近在一項涉及80名患者的研究中,LAAC過程中使用了靜脈丙泊酚和咪唑安定的聯合[9]。之前也已經探索了在LAAC程序中避免全身麻醉的其他方法。Niselsen-Kudsk等[10]報道了使用心內超聲心動圖指導10例患者的LAAC植入。他們的結果表明,與TEE相當的最佳圖像可以通過位于冠狀竇內的心內超聲心動圖探頭獲得。在Wang等[11]報道的一份病例報告中,嘗試使用經鼻微小食管超聲心動圖探頭在清醒下引導LAAC裝置植入。
吸入性肺炎是深度鎮靜的潛在并發癥[12]。同樣,其也可以發生在全身麻醉或TEE檢查本身。在本研究中,通過胸部X線和血細胞計數監測,特別強調了對這種并發癥的監測。本研究患者沒有發現吸入性肺炎。深度鎮靜與全身麻醉相比,在LAAC手術中是否更常發生吸入性肺炎需要在更大的患者人群中進一步調查。全身麻醉在LAAC裝置植入術中的優勢,廣泛支持的觀點是其在裝置放置期間能夠產生短暫的呼吸暫停的能力[13]。然而,根據這項小型研究中的經驗,裝置釋放在呼吸運動方面并未受到任何重大影響。在第1天通過TEE監測,在一名患者中檢測到Amplatzer cardiac plug(ACP)裝置的移位。在該患者中,所有裝置釋放標準,即預期著陸區處的葉片位置,至少三分之二位于左回旋動脈的遠端,除了葉片的形狀出現過度壓縮之外,滿足與左心耳頸部對齊的裝置的取向,瓣與瓣膜之間的良好分離,盤的凹度以及由盤沒有泄漏覆蓋的左心耳開口。ACP裝置的過度壓縮可能會導致葉片上的穩定導線無法鉤到左心耳壁上,存在立即或晚期移位的風險。因此,其被認為與采用深度鎮靜或全身麻醉無關。
本文是一個關于采用右美托咪定中度鎮靜代替全身麻醉用于LAAC術的可行性和安全性的小型實驗性研究,結果可能需要在大樣本隨機對照研究中進行證實。 最后,并未在這項研究中評估患者對鎮靜過程的滿意度。盡管如此,本研究所得出的數據表明,LAAC術可以安全有效地在右美托咪定鎮靜下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