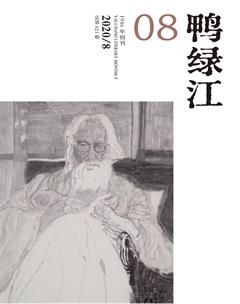與樹終老
我看見了那些樹。城市如水,不可避免地沉下去。漣漪漸消。水落樹出,突兀于荒漠之中,散發著神性的光輝。
披著國際大都市的外衣,深圳的內核其實是城中村。深南大道、北環大道、濱海大道、寶安大道……藍色的高樓大廈后面,城中村連接成片。有點前店后廠的意思。一個對外,一個對內。對外整潔嚴謹,對內節儉鮮活。經過幾十年的顛簸,大拆大建模式逐漸沉寂下來。低矮的城中村和光鮮的寫字樓、綜合體、商業小區各安其位,不再是你死我活的對峙。
都有點累了。
處于劣勢的城中村終于可以稍微大聲一點喘息。它們如海上漂泊的小船,起起伏伏,時隱時現,不知道方向在哪里,終點在哪里。好在每條小舟上都有一只錨,重達千斤,可令其隨時停下來。
此處的錨,就是榕樹。
幾乎每一個城中村里,都有一棵被崇拜的“神樹”。說每一個,也許并不嚴謹。沒人專門統計深圳有多少棵“神樹”,但確實很多,時不時就會遇到。它們像一顆顆釘子,把這個繁忙的、隨時要飛起來的都市緊緊地釘在大地上。
不同品種的榕樹,大葉榕、小葉榕、橡皮榕、雀榕等,大同小異,都是闊大的陰涼。陽光七繞八繞要跳下地來,葉子擺陣阻擋,拉住它的腰帶,使其懸于半空。
樹干上拴著幾條紅布。四周圍一圈低矮的欄桿,或木制,或鋼制,欄桿內擺放著神像。一尺多高,彩塑。有的單供一菩薩,有的單供一關公。有的供著渡海的八仙,有的供財神爺。多數是放幾個神像,菩薩、關公、財神爺坐一起,各收各的香火和祭品。更奇者,樹下擺四五個關公像,或坐或站,或持刀,或捋髯,或呆萌,仿佛若干片段的拼接,一個人的一生集合于此。
原住民的崇拜是開放的,絕不偏執。凡是你能想到的神靈,天上的,地下的,海上的,河里的,欽定的,民間的,在這里幾乎都能找到。神仙太多,各管一攤,都比凡人力量大,都能影響凡人的生活。隨手一指,土坷垃就變成黃金。即使一時求不著,將來沒準兒用得上。即使一輩子用不上,也不能得罪。雖幫不了你,但因為神通廣大,分分鐘置你于死地,傷害力有甚于“有求必應”,所以見神就拜準沒錯。
如此,也不需什么完備的教義。崇拜嘛,歸結為一個詞,即敬畏。燒香拜神,心中多存非分之想。這一部分,神仙能否滿足,自古見仁見智。有所求的另一面是有怕。世俗中人,有個怕頭,挺好。天不怕地不怕,也許才是最可怕的。
農耕社會,拜神乃百姓日常,如油鹽醬醋,如吃喝拉撒。神在每個人的身邊,深度介入具體生活,掌管各種生活禁忌:不能踩門檻,容易受窮;不能說瞎話,會爛嘴角子;不要說喪氣話,容易成真;不孝順父母,天打雷劈……舉頭三尺有神明,神在高處打量著眾生,默默給出評價,一個都不落下。
如今,人們的生活被金錢牽引著,沿另一個方向疾速行進。地鐵、創業、抖音、房產,成為另一種生活方式。神紛紛離去。背影蕭瑟。他們掌控的那個世界漸趨崩塌。怎么辦?
也許沒這么悲觀。擺放在樹下的、數不多的塑像,每個晚上都會復活,檢視人間。他們可以被打碎、被挪走,但有這棵大榕樹在,他們隨時可以回來。身負眾神的責任和寄托,他們以一當十。
越來越少的崇拜者,則因危機感而更緊地抓住神的衣襟。豈止是信仰,還有鄉情、親情和時代的痕跡。城市發展得太快,他們一路跑著追,一手護著兜里的糖。如果吃掉,不過就是一塊糖。你要從他手里搶走,那就是他的尊嚴和全部牽絆。他用這一塊糖來維護自身所有的過去和未來。
所以,神樹越被擠壓,就會被擦得越亮。
城中村的主人是原住民。蜂擁而來的外來人口漸漸稀釋了他們。他們有的老去,有的掙夠了錢,到更舒適的地方定居。而客居城中村的人,故鄉已經回不去了。此處彼處,他們已然用腳步投票,對此地有了歸屬感。耳濡目染,也被這樸素的信仰所凈化和同化,有了恭敬之心。當年我們一行人去內蒙古玩了幾天,獲知牧民喜唱歌,酒桌上,大巴車上,隨時高歌一曲。在此地生活了幾代的漢族人,不知不覺也都愛上歌唱。他們承接了這個地方的風情。一塊土地自有一塊土地的神性。土地的氣息和傳承,似乎要大過人類自身的努力與抗爭。
我所居住的小區附近就有個城中村。我經常從那棵神樹下面走過。“神樹”一詞不知是否準確,我圖方便才如此簡稱。為何要拜樹?本地人提供了一種說法:古人相信大樹底下好乘涼。茂盛古老的大榕樹附近,都是風水極佳的地方,把觀音菩薩安放于此,是對神靈的照顧。菩薩住得舒服,自然回報信眾。另外,一些宗祠、廟宇旁邊也都種有榕樹,意義相同。廣府人一般每月農歷初一、十五要去上香。做生意的潮州人則習慣在每月農歷初二、十六上香祭拜。如果心有所求、事有不順,祭拜的時間可隨機。
明明是拜神,拜來拜去,成了拜樹。其實想想,塑像亦非神的真身,用以寄托而已。久而久之,樹可代塑像,塑像可代樹。無論拜誰,只要虔誠即可。信則靈。應驗了,是神靈保佑。沒有應驗,是神靈力有不逮。以同情心深愛神靈,而非斤斤計較。誠心誠意地信奉點什么,一輩子過得都踏實。
神樹的樹干上掛著“某某街道名木古樹”的鐵牌,小字為“保護等級:三級;樹齡:150年;責任單位:某某居委會”。這個牌子是它的身份證和保護傘,它不是因為“神”而被保留下來,是現代生活中的考古、環保等要素留住了它。但在居民心中,這棵樹葆有靈氣,聚天地之精華。他們像祖輩一樣崇拜它,在那里燒香許愿。現代和傳統就以這樣自然的方式結合了。
神樹大多在城中村的廣場中央,莊嚴肅穆,居高臨下。葉子因高遠而顯得渺小,樹冠因為龐大而遮下一片陰涼。但那陰涼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只可遠觀而不可近享。走近了,膽怯、自責之情便油然而生。
另有一種,像鄰居一樣坐在人群中間,成為休閑之地。旁邊有違停的汽車、垃圾桶和馱著煤氣罐的三輪車。一只散養的雞跑來跑去,兩歲的娃娃在樹根旁邊蹣跚學步,年輕的母親坐在石凳上刷手機……天地祥和,榕樹造就了這一切,又仿佛一切與它無關。
所有重大社區活動——文化演出、廠家直銷、一早一晚的廣場舞、飯后閑聊等,都在這棵樹下或者附近舉行。哪怕它實際位于城中村的門口或東北角,但它始終是人們心理上的中心,是眾人心之所倚。有了這棵樹,這個村子就散不開了,始終是一個堅固的整體。
有必要說一說城中村。千百年來,它們原本是一個個獨立的村莊,懶散地躺在嶺南湛藍的天空下。這個村子和那個村子之間,大片的稻田自由自在。轉眼之間,廠房拔起來了,新的規則建起來了,打工的人紛紛趕來。村民們匆匆忙忙在自家宅基地上蓋上樓房,樓和樓緊貼在一起,俗稱“握手樓”。流水線工人、保安員、清潔工、快遞小哥、機關里的臨時工在這里可以租到便宜的房子,買到廉價的生活用品。這些城中村成為城市的濕地。城市靠它呼吸。原住民坐收漁利,有時候又不滿足于此。一幫畫家朋友住在一個城中村。他們有個龐大的計劃,用手中彩筆給臟兮兮的墻面涂抹上一幅幅畫作,所謂城市涂鴉。有些居民聽說后,明確表示反對,理由是,畫得這么漂亮,萬一成為管理部門邀功的定點社區與旅游景點,將來就不好拆遷了。
他們的想法已經改變,對凌亂的城中村也不再留戀。
但對神樹的崇敬一直堅守著。
南方科技大學校園里有三棵“神樹”。我見識過其中的一棵。
這一年春天,天氣暖得特別早。本應三月份盛開的木棉花,提前到了二月。天空一片紅。南科大位于長嶺陂水庫旁邊,一直禁止開發。建校時,附近三個村莊搬遷。村民提出的要求之一便是不要砍伐這三棵樹,給他們留個念想。攪拌機轟鳴,挖掘機穿梭,一所清新脫俗的大學很快矗立起來。新栽種的各類樹木,列隊打量對面這棵孤獨的四百多歲的古樹。高大如彼,也被空曠的藍襯托得不再高大。一朵朵白云從頭上飄過。老樹臨風而立,沉穩老練,不卑不亢。
每年固定的某些日子,村民們從四面八方趕來,祭拜神樹。
問,具體哪一天來?答曰,不清楚。
旁觀者僅僅知道他們有這個信仰。為何?如何?都不重要。每個人都沉浸于自己的生活,能轉頭瞥別人一眼,已經占用了時間。多問便是多余。這種散淡,有助于各自維護自己的內心。
別處的塑像都是露天擺放,此處略微莊嚴,用水泥抹出一個臺子。高約一米,四四方方,三面遮掩,一面沖外,猶如戲臺。墻壁貼著一個“福”,里邊端坐兩尊像。土地公公和土地奶奶,懷抱手杖,臉上都笑瞇瞇的,像隔壁的老爺爺老奶奶。塑像底座居然還寫上名字:“土地奶奶”,證明不是凡人。旁邊站一個財神塑像,戴著官帽,右手托金元寶,左手執一豎幅,上書“財神到”三個字。
塑像前面擺放著新鮮的水果。一束塑料假花。一束真花,名為水塔花,鮮紅。真花很鮮艷,假花也很鮮艷。不仔細看,分不清誰真誰假。兩個塑料酒杯。一瓶北大倉白酒,剩了半瓶,另外半瓶估計已祭灑在地。一個香爐,積滿香灰,上面還插著香,但未點燃。一個鐵桶,我在墓地見過這種鐵桶,用來燒紙錢的,防火外溢。
榕樹主干已有些歪斜,下面用很粗的鐵管子支撐著。氣根有的垂在半空,有的一條條粘連在樹干上,七扭八歪,成為樹干的一部分,仿佛繩索捆住了歲月。捆綁者和被捆綁者終究還是走到了一起,可體悟到“恨之切”與“愛之深”的關系。斑駁粗糙的樹干上,幾十片葉子正在長大。新綠,滴水一般。想到一個詞:生生不息。
樹干上掛著一個小小的牌子,上寫:“只吃貓貓食品(食堂的菜太咸,請勿投喂)”。友人說,這棵樹成了流浪貓的棲身之地。有些好心的學生經常來給它們喂食。愛護小動物的組織就專門掛了這個牌提醒。下面有一塑料盆,用來盛放貓食的。
抬頭,樹杈上有一只皮毛柔順的花貓正低頭瞅我。四目相對,我覺得它比我沉穩多了。它的前后左右,一定還有我看不見的生物:樹根下的蚯蚓、不知名的昆蟲、蝴蝶、蜻蜓、候鳥……古樹猶如樓房,構建了一個龐大的生態體系。眾生在其庇護之下,平平靜靜過一輩子。樹在,它們的家就在。
于是出現了兩個問題:其一,有人討論在南方科技大學這樣一個理性學府,保留著拜神之地,是否合適。官方的答復好像是為村民留下“守得住的鄉愁”。其二,在樹下燒香點火,對樹木是否造成傷害。然而,我站在樹下,默默地看著它,春風拂面,問題漸漸消失。學生們到食堂打飯,天天從樹下走過。那就是他們的一部分,是校園中一以貫之的一個符號。農耕社會與現代社會邊撕裂邊融合,并非水火不容。火有時是水,偶爾點燃,小心翼翼界定在某個范圍內,對樹木何嘗不是澆灌?
樹木安好,心靈安好,人也安好。
這些神樹眼睜睜看著城市一天天變化,終有一天也會死掉。人禍之外,還有臺風、暴雨、蟲蛀。它們的命運不一定比人類更好。它們一棵棵干枯、倒下之后,敬畏就結束了嗎?
在一個城中村,我見到過一棵明顯年幼的樹。它僅僅兩米高,站在人行道旁邊,葉子也不似別的榕樹那般油亮。瘦弱,一副病懨懨的樣子,但是樹干上卻系著兩條紅綢子。不用說,這是被寄予厚望的一棵樹。假以時日,它也會成為居民心中的神樹,樹下也會擺出塑像。我憂心的是,這棵樹周圍的空間不大,地面被柏油封上,氣根從樹上垂下來,晃晃悠悠,尋尋覓覓,無法扎到地上。榕樹能繼續長大嗎?周圍人聲嘈雜,空氣污濁,它如何應對?它能否如那些百年老樹一樣從艱險中突圍,傲視周圍平庸的綠色植物?
【責任編輯】 陳昌平
作者簡介:
王國華,河北阜城人,曾居長春十八載,現居深圳。“城愁”散文的倡導者和書寫者。曾獲第五屆廣東省有為文學獎散文金獎、第八屆冰心散文獎、第八屆深圳青年文學獎、第六屆深圳十大佳著獎。已出版《街巷志:行走與書寫》《書中風骨》等二十余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