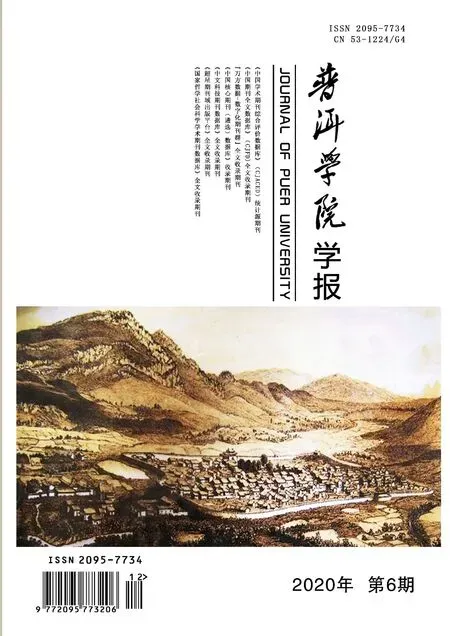“俗中尋圣”:安徽花鼓燈的儀式性表征
陳 萌
安徽藝術學院,安徽 合肥 230041
花鼓燈舞蹈是一種表演藝術,它通過具體的動作、韻律、造型,融合成舞蹈。表演者的身體曲線變化、身體在空間中的舞姿停頓,以及身體各部位的合理支配使用,都有著特殊的審美價值和獨特藝術風格。花鼓燈藝術集“歌”“舞”“戲”為一體,加入鏗鏘的鑼鼓,融合雜技、武術等元素,較好地保存了淮河人民對家園、土地的記憶,并以舞蹈藝術形式相傳承。這一表傳承蘊含著人性的本真,對研究人類文化具有重要借鑒和比較價值。
在安徽花鼓燈中探尋其儀式性表現,試通過分析其舞蹈流傳的程式化特色,尋找儀式性的蹤跡,從安徽花鼓燈這一舞蹈藝術,探尋其深刻的文化內涵和價值。
1 安徽花鼓燈的儀式性分類
1.1 民俗儀式活動
民俗儀式活動日期包括國家傳統重大節日和地方風俗節會兩部分。在安徽地區花鼓燈固定的表演日,前有“國家節日”中的“元宵節”,后有“地方風俗節會”中的“驚蛟會”和“禹王廟會”,都是花鼓燈表演的重要時刻。
在“國家節日”和“地方風俗節會”中,每年都有上百個班子的民間鑼鼓藝人和舞蹈藝人自發性的組成隊伍互相競賽,以賽促學,不僅是單純的表演現場,更是花鼓燈的傳播與繼承,同時也是眾多民間藝人得以出名的“擂臺賽”。表演中最優秀的“鼓架子”和“蘭花”會成為會后人們追捧的對象,同時優秀的花鼓燈班子在十里八鄉都非常受歡迎。所以“國家節日”和“地方風俗節會”中春會、廟會的舉辦,對于花鼓燈和相關藝術形式的發展與傳播,具有深遠的影響和重要的作用。同時,花鼓燈表演場合的空間以及時間限定,決定了花鼓燈的舞蹈性質和意義,同樣也對花鼓燈民俗儀式活動的研究有很大的影響。
1.2 社會儀式活動
民間舞蹈在社會儀式活動中具有“自娛性”的特點,在自娛中溝通著人與人之間單純的情感,體現著人類自我生命的價值。“鑼鼓一敲響,腳底板直發癢”“看起花鼓舞,忘了累和苦”。玩燈人可以在表演時以現場的熱烈氛圍即興發揮,幾次返場表演,不受場地、禮數的束縛和局限,表現出毫不矯揉造作的真實一面,這正是它在維系社會場域下具備的強大生命力。
據老藝人回憶,解放前每到陰歷的十三日,村里人匯聚到村頭、用玩燈的方式來緩解農耕的疲勞。男女老少輪流打鼓、跳舞,一直可以玩到深夜,稱為“村頭音樂會”。玩花鼓燈的高手層出不窮,有的比試鑼鼓,有的比試舞蹈、有的比即興對歌,就這樣一年年、一代代流傳下來。花鼓燈作為淮河文化發展軌跡和肢體語言,共有400 多個語匯、50 多種步伐,它不僅喜聞樂見,也表達出人們的訴求、理想和憧憬。花鼓燈作為社會儀式性的表征,也成為搭建人們溝通、傳播情感的橋梁。
2 安徽花鼓燈的儀式性差異比較
在安徽花鼓燈中,雖然自然形態的安徽花鼓燈都伴隨著儀式活動,但是就安徽花鼓燈自身來說,不同地域內的花鼓燈也存在著儀式性差異。以蚌埠花鼓燈和懷遠花鼓燈為例,二者相較會發現懷遠花鼓燈中蘊含的儀式性要比蚌埠花鼓燈鮮明,蚌埠花鼓燈更重視民間的小戲而儀式性則沒有懷遠花鼓燈的強烈。在此,主要通過橫向比較,將蚌埠花鼓燈與懷遠花鼓燈的儀式性強弱差異做出比較。
蚌埠花鼓燈注重舞蹈和后場小戲,而懷遠花鼓燈則重視舞蹈和燈歌演唱部分。同屬安徽懷遠地區的懷遠花鼓燈和蚌埠花鼓燈,是兩種毗鄰的藝術風格,雖然都有相應的人物角色,但表演講究卻有不同的程式;同是重“舞”和“戲”的程式規范,順序也是“舞”在先,“戲”在后,兩者呈現出迥然不同的特質:前者更注重儀式的程式化,后者則注重表演時的隨機性。另外懷遠花鼓燈和蚌埠花鼓燈中,有些花鼓燈的內容和特色還是有某些相一致的特點。
2.1 表演程式與人物角色
安徽花鼓燈角色繁多,分工細致,與其他地區相較而言,懷遠地區的花鼓燈是最注重禮儀的原生態分布區。幾百年來,懷遠花鼓燈仍保留著完整而嚴謹的表演程式。整個表演流程主持——樂大夫(地位居花鼓燈隊之首)指揮,儀仗隊先導的儀式活動開始,舞蹈班子編制也極具儀仗隊規模。舞班子角色多是以當地農民、漁民、樵夫、村姑等真實人物形象改編。這一看似雜亂實際有排布的陣容,是民間對宮廷祭祀禮儀的一種效仿,也受到了古代祭祀樂舞的影響。
首先,表演角色手持手巾、翎扇、拂塵和霸王鞭等道具,與羽、人、皇、干、旄等(宮廷雅樂“六小舞”)屬于一脈相承的流傳之物。懷遠花鼓燈中保留完好的典型的儀式性動作是“三拜九叩”,“三拜九叩”是花鼓燈表演過程中純儀式性的動作,還未融入舞蹈化的變形。
其次,懷遠花鼓燈的儀式性特點還表現在表演的前后順序和排布中。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一,懷遠花鼓燈首先開始祭拜祖宗、神靈及尊長,再與鄰居互拜;正月十五鬧元宵開始,各地春會、廟會都會有群眾自發組織的花鼓燈班子表演。表演程序為“拜進”——“串街”(雙縱隊的形式邊走邊舞)——“走大陣”(觀眾會自然地圍攏成一個圓圈,花鼓燈隊形成單隊“快走陣”),最后的表演模式與之前的嚴整儀式性不同,突出舞蹈的“耍小場”程序。
花鼓燈表演過程中的儀式行為在特殊的氛圍和場域中,形成了特殊情境中的符號意象。尤其是“樂大夫”這一角色,作為花鼓燈隊伍的靈魂人物,扮相要求莊重而體面,因為其衣著裝束代表了村落整體的禮儀,又象征了其在花鼓燈隊中的權威地位。樂大夫的常用道具是拂塵和傘。拂塵是民間清除灰塵的工具,在儀式性表演中被賦予驅邪逐疫、清潔的象征性含義;傘是生活中的常見道具,有實用價值并兼具象征意義。其簇擁式的結構是天神君主賜福于人間的標志,也是民眾表達擁戴與順從的特殊符號。
可見,懷遠花鼓燈的表演程序與禮儀規范已融入了鄉土社會的生活秩序,村際關系之中。除去“耍小場”部分的“非儀式性”之外,其他程序無論形式還是內容都較為中規中矩。雖然懷遠花鼓燈的節慶展演呈現出某些地域性、時代性的特征,貫穿始終的是花鼓燈儀式和反儀式中所承載的除穢納新、祈福同慶的含義,潁上當地的民眾也通過這一慶典活動,調節和恢復正常的秩序與生產。
2.2 地理位置與文化
懷遠與潁上相比,潁上的地理位置比懷遠稍遠,交通不及懷遠便利,民風相對保守。商業的較早繁榮使懷遠比潁上發展更快,經濟發展也影響到了文化藝術,淮南鳳臺花鼓燈自娛性較強,娛神性成分較少,反儀式的特點較為強烈。因為地理環境人文等特點較接近的緣故,兩地花鼓燈有共通之處:第一,都不是以宏大隊伍場面取勝的區域;第二,丑角人數相應精簡;第三,兩地花鼓燈隊男女角色都重視不同表演氣質的塑造(女性動作和唱腔普遍婉轉大氣,男性形象既有陽剛之美,又不失詼諧);第四,小戲部分兩地在故事、雙人表演上也有相似之處。
2.3 傳承方式及特點
師徒傳授是舞蹈藝術重要的傳播方式,而花鼓燈作為民間舞蹈的代表之一也是通過這樣的方式,最開始花鼓燈的教學法則和教學環境沒有形成規范和體系,花鼓燈的學習者們通過自己學完之后再進行自我研習,加之淮河兩岸區域廣闊,藝人們也形成了不同風格的特點。這其中形體特征、表演特色、性格情況、生活閱歷、師承關系的不同,也決定了他們風格各異,千人千面的特點。
鳳臺地區的花鼓燈,細膩、傳情、扇花多。馮國佩為其代表。以鑼為領奏樂器,舞蹈以雙人對舞形式居多,舞蹈情景表演細致,動作舒展大方,其“拐彎”“斜塔”“野雞溜子”等動作堪稱一絕。
懷遠地區的花鼓燈,重技巧,有灑脫、陽剛之美。以鄭九如、楊在先等人為代表。代表動作有“單拐彎”“雙拐彎”“三拐彎”等,舞蹈動作矯健敏捷、灑脫濃厚。
潁上地區的花鼓燈,質樸、表演粗獷、簡練。舞蹈風格古樸、結構嚴謹、節奏偏慢,代表動作有犀牛望月、白鶴亮翅、猴子抖月、獅子擺頭等。
3 安徽花鼓燈中儀式性的意義
3.1 儀式與文化
對于不同地域的民眾而言,生存模式決定了其地域文化,而具有一定周期性的儀式,在不斷的發展中會逐漸形成一項程序化的安排。而儀式除了表現其自身蘊藏的文化含義之外,也體現了發揮具體行為的實施過程的作用。
安徽花鼓燈中各種儀式性活動均受到安徽文化的影響。比如在禮儀活動中,安徽本就是一塊重禮尚義的土地,受儒家的影響,各地在人際交往方面特別注重禮尚往來和禮儀規矩。這也體現在鬧花鼓燈的活動規矩中。安徽花鼓燈在演進過程中,歷經了簡易到華美的外在蛻變,但無論外在形式如何,都未影響當地人對它的虔誠信仰和全身心投入,更沒有削弱禮儀自身的整肅行為。
花鼓燈是當地的重要民俗,同時它也是凝結民間禮儀的載體。因此,花鼓燈的互拜和互訪是村際間重要的禮物流動和互惠,是人際關系往來和情感交流的密不可分的媒介。即便是在困難時期,民間奢侈的煙、酒、糖、點心,在花鼓燈面前反倒成了附屬品。因為當地的風俗習慣和節日特定的時空情境,常年來,演變出了固有的實物交換規律,禮物、情感的交換促進了當地密不可分的社會關系。
3.2 安徽花鼓燈儀式性的未來思考
首先,建立傳承體系。以老藝人為重點,做好傳承工作,鼓勵帶徒傳藝,培養花鼓燈傳承人。恢復大規模春會賽燈會和廟會賽燈會,舉辦藝術節、抵燈、賽燈、燈歌、鑼鼓、舞蹈晚會等民俗活動,彰顯“淮河派藝術風格”的文化內涵。更為重要的是加強傳播、組織藝人授課,把花鼓燈保護置于田野之間、民眾當中、城市村落之中,由群眾自由參加和選擇,將文化保護成果與群眾分享,從而使文化保護成為地方政府的職責所在,成為民眾自己的份內事。
其次,設立“因舞制策”的發展機制。蚌埠地區和淮南地區先后頒布了《蚌埠市保護和發展花鼓燈、泗州市藝術的規定》《淮南市關于保護和發展花鼓燈藝術的條例》,在保留花鼓燈這一非物質文化的響應下,走訪花鼓燈重點流行區域,訪問花鼓燈藝人和群眾,掌握花鼓燈的基本隊伍、場地情況,收集音像資料及實物,制定了指定專人保護等措施,使民間舞蹈得以保留下來。但是,花鼓燈這樣一種民間文化,在社會文化的不斷更迭中也面臨嚴峻的考驗,尤其是隨著老一輩民間藝術家的過世,鑼鼓技藝、舞蹈韻律這些能夠充分體現花鼓燈獨特魅力的技藝也逐步失傳。因此,完善的法律法規是文化發展的重要保障。
4 結語
花鼓燈作為淮河文化中獨具魅力的一部分,有著它自己的獨特個性,從不同的視角出發,使花鼓燈在文化空間里擁有獨立的傳承和傳播方式。花鼓燈雖然從文化藝術層面進行傳播,但在社會秩序規范和與神與人的對話中,也用風俗文化的方式,發揮了儀式性的規范行為作用。伴隨著花鼓燈在當代化多元發展,以及由外而內的現代觀念融入,從而實現無論處于何時、某種境遇下、與怎樣的思想觀念和精神意識碰撞,它都可以很好地保持本體的屬性,真正地成為中華文化的傳統精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