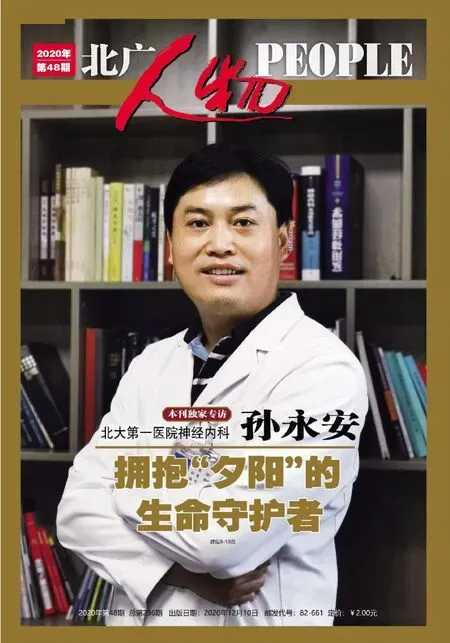新冠疫苗守護者趙振東:率真是學者應有的風骨
倒下前在研發一線已作戰兩百多天
11 月30 日,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召開趙振東事跡報告會。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期間,53 歲的趙振東與時間賽跑,夜以繼日地堅守疫苗研發一線,連續作戰200 多天。9月16 日,他從長沙參加完學術會議返京后,倒在了首都機場T3 航站樓,次日凌晨不幸離世。疫情期間,他赴國藥中生等公司調研,評估新冠疫苗生產車間風險,提出風險點及防范建議。不僅如此,他還完成了國藥北京公司、武漢公司以及科興公司的生物安全聯合評估。據報道,就在去世前兩天,趙振東還剛去武漢,執行了一次新冠滅活疫苗生產車間生物安全聯合檢查任務。
在課題組師生交流的微信群里,趙振東發給學生們的參考文獻從未間斷。王蓓打開群聊,趙振東最后一次給大家傳送文獻的時間,定格在9 月16 日17 時36 分。這是他從長沙返京前,在機場給學生們的最后“留言”。離他“倒下”,只有不到三小時時間……
敬畏科學不通人情世故
“趙老師曾說,余生只有兩個追求,一是多培養幾個年輕人,二是用畢生所學真正為醫學事業做點貢獻。”王蓓是趙振東課題組的研究助理,也是跟隨他13 年的學生。她回憶,農歷新年前兩天,趙老師接到北京市科委新型冠狀病毒抗病毒藥物篩選任務,剛剛放假的他們又被趙老師一個電話叫回實驗室。
“趙老師說,你們要明白,現在是要打仗,和時間賽跑,今年就別回去過年了,以后有的是機會。”王蓓說,此后,趙振東帶領他們開始了長達半年的艱苦科研攻關,中間一天沒歇過。七個人的實驗室,開展了疫苗研發、中和抗體篩選、復制子體系的構建和抗病毒藥物的篩選。“那段時間,好幾次我都累得想哭。而50 多歲的趙老師,除了實驗室工作,還參加科研攻關組疫苗研發專班的工作,白天晚上連軸轉,從沒喊過一句累。他總說,進度可以再快點。”“你給我(對新冠病毒的新特性)下一個最完整的定義,這個定不好怎么開展下面的工作?”這是在武漢召集的一次緊急會議中,中國醫學科學院病原生物學研究所研究員趙振東發言的第一句話。趙振東的發言照例有些唐突。“他的對面都是院領導,但還是習慣性的直奔主題。”中國醫學科學院病原生物學研究所副所長任麗麗和他一起開會,至今仍記得他站起來發言,慣有地縝密、嚴謹。趙振東是與眾不同的,他開會從不說“暖場”的客套話,那些“大家做了很多不錯的工作”“前面領導的觀點我同意”等等的發言,與他的率真“絕緣”。

在報告會上,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院校長王辰院士說:他是一個真實的人。對趙振東教授最好的紀念,就是讀懂他的精神,致敬他不平凡的人格。“他的表達和我內心對科學家應該堅持的價值觀是契合的,我當時就想協和人就應當有這種直截了當的勁兒。”
基于專業的判斷,怎么想就怎么說,是學者該有的風骨。趙振東一向如此。他的妻子王斌不止一次被好意提醒:你回家勸勸老趙,他在會上的發言實在是太直了,一點也不給別人留情面,那會得罪很多人的,以后還得在圈子里“混”。
趙振東卻絲毫未改。趙振東離開的七十多個日日夜夜里,王斌滿腦子都是他在家里改論文、看文獻,或是在沙發上滔滔不絕和電話那頭的學生、專家、技術人員做學術討論。
“他和同事們討論問題總是直奔主題、堅持己見,甚至是毫不掩飾的批駁。”王斌說,“有時我都覺得難堪。”漸漸地,王斌理解了他:對科學的敬畏,讓趙振東不通人情世故。
在科研的問題上、在真知面前,趙振東不會拐彎抹角。趙振東曾對王斌說:對于科學研究,一是一、二是二,別人怎么看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在正確的路上走下去,明明有問題卻不指出來,那就是對科學的不負責任。
總能“切中肯綮”讓趙振東常被邀請做評審專家。沒有“杰青”“長江”的頭銜,趙振東當然不是被拉去“充門面”的。
“很多人喜歡請他,因為他說真問題、他把丑話說在(研究)前頭。”任麗麗告訴記者,大家都明白這是對課題的極大推進力。
討論科研時,趙振東一激動就會站起來,左手抄兜,右手在空中劃出有棱角的折線,他一米八的個頭,讓鮮明、嚴謹、思辨的學術觀點騰空而降。

“他的發言從來都是邏輯非常清晰的。”任麗麗回憶:“他會說,‘我認為有以下幾點,第一、第二……’給大家‘捋條條’,順著他的思路,再難推進的工作、再千絲萬縷的‘結’都能理順。”或許,這就是疫情襲來,疫苗研發專班將極重要的技術支持組組長的重任交給趙振東的原因。
對于科學的求真,讓趙振東勇敢,不僅讓他勇于直言、更讓他勇于面對致命病原體。“在傳染病病原體傳播途徑不清楚的情況下,很多同志心里害怕感染,這是通病。”中國醫學科學院病原生物學研究所所長金奇說,但每當遇到這種情況,趙振東都挺身而出。
對人民對科學愛得深沉
去南京、上海采集H7N9 病毒樣本,去新疆采集脊髓灰質炎病毒樣本……“追捕”高致病性病原體的旅程中,趙振東始終在出擊的第一線!
趙振東是國內少有的從事病毒免疫學研究的人。眾所周知,免疫學熱門,但由于健康需求,大多研究集中于腫瘤免疫,與疾病相關。與病原免疫相關的研究變成了“燈下黑”。
“他在細分領域的成績是‘大咖’級的。”任麗麗說,“他的離開讓我們國家在這個領域失去了一位堅守者。”
2009 年,趙振東開啟了病毒與細胞自噬的研究,彼時國際上也鮮有研究。他的學生、現在已是首都醫科大學副教授的王繼說,短短3年,團隊揭示了丙型肝炎病毒誘導細胞自噬效應及其分子調控機制,并發表了系列高水平論文,在國際上頗具影響。
是學者也是醫者。趙振東離世后,妻子王斌整理他的微信才得知,他十多年來一直與一個先天免疫缺陷的孩子和父親保持聯系。
“我都告訴你800 遍了,不能等感染嚴重了再去治療,要盡快用丙種球蛋白,一定要把IgM(一種抗體)補上來!”定格在2019 年10 月的這條微信,字里行間凝結著醫者替患者的焦急。
趙振東對這位父親的焦急卻從不透露給生病的孩子,而是給孩子定目標,激勵他。他對孩子說:“現代醫學還沒有到能徹底解決你的問題的時候,你要學習一些醫學知識,了解、堅強、積極尤為重要。”
對人民、對科學,趙振東愛得深沉。“最好的懷念,是理解他。”王辰說,他的精神在這個時代里是難得的。
真專家、真學者是什么樣?趙振東用他最看重的科研人員的身份給出率真的回答:替國家操心、為人民憂心,無論是日常還是遇到重大事件時,勇于為國家、社會、民族挺身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