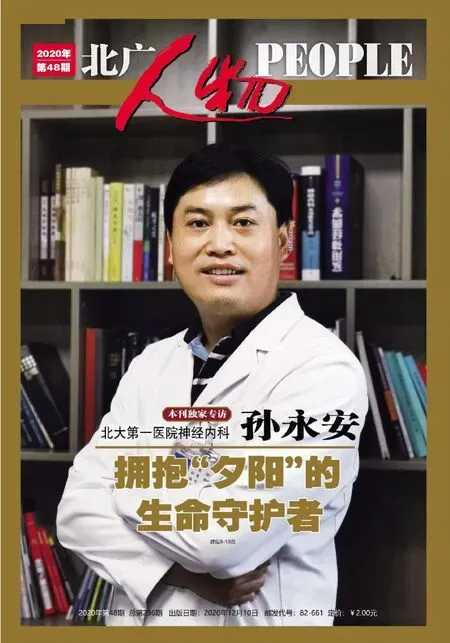京劇的誕生與“同光十三絕”(下)
木匠


七、時小福
時小福(1846-1900 年),名慶,別名小馥,字琴香,一字紉之,號贊卿,寓名“綺春堂”(位于宣南朱茅胡同),小福乃是其藝名,江蘇吳縣(今蘇州)人。工青衣。
時小福12 歲隨父母來到北京,拜在四喜班名旦鄭秀蘭的“春馥堂”中,從徐阿福學習昆旦兼皮黃青衣。滿師后,經常在春臺、四喜、三慶各班演出。后為四喜班的臺柱之一,時人曾把他的《三娘教子》與孫菊仙的《御碑亭》放在一起,稱為“四喜光緒二十五年班二絕”。
時小福的嗓音高亢,但又不失委婉,時有“天下第一青衣”之譽。他不僅于清光緒十二年(1886 年),入選了升平署,更首開了以旦角演員的身份出任精忠廟廟首的先河。小福戲路極寬多,常演的有《陽關折柳》《小宴》《彩樓配》《三娘教子》《桑園會》《二進宮》《汾河灣》《武家坡》《探寒窯》《祭塔》和《南天門》等,其反串小生戲《孝感天》《雁門關》和《打金枝》等,亦都很受時人的推崇。
據傳:時小福酒量很好,晚年演戲,常愛用白酒飲場。彼時,一位御史常來聽小福的戲。這位御史也是一個愛酒之人,總是一邊聽戲,一邊飲酒。一次,小福演到劇中人要喝酒時,竟然跳到臺下,將御史之酒一飲而盡,然后又回到臺上,繼續演戲,令場內觀眾大笑不止。
當年,小福在北京的寓所,位于宣武區朱茅胡同,堂號綺春。他的八個徒弟,皆以“仙”字排名,這八位也跟其師一樣嗜酒,且個個都是海量,時人謂之“醉八仙”。小福生日時,“八仙”必定都會來給他祝壽,時有“八仙慶壽”之說。
小福不光戲唱得好,為人也極是古道熱腸。1875 年1 月12 日,同治皇帝駕崩,清廷的規定:停止一切娛樂活動100 天,不準動任何響器。這對演一天有一天吃喝的戲班來說,等于是拆了灶臺。京城許多小戲班都倒閉了,即便是如四喜、春臺、三慶這樣的名班,也只能開一半“戲份”。時,四喜班班主梅巧玲依然硬撐著門面。五六十天以后,他已傾盡其積蓄,眼看就再也支撐不下去了。這日,梅巧玲來找時小福,難過地說:“眼看我們已經傾家蕩產,我怕是熬不過去了,不如就將戲班解散了吧。”為幫助梅巧玲支撐戲班,時小福也已經拿出了自己的大半積蓄,他說:“四喜的處境我也清楚,只是四喜現在能成為京城的名班之首,靠的是日積月累,含辛茹苦,如今若散去,日后怕是再難成今日之氣候。如果大哥執意要解散四喜班,小福便冒昧了,愿將四喜班接過來。”就這樣,小福將偌大的一個四喜班接了過來。此時的他,堪說是“受命于危難之際”。但話好說,畢竟事艱難,他先是變賣了自己的全部家產,又典當了自己的行頭,最后,連當年贈送給夫人的錦盒也端了出來。這才終于讓四喜班挺過了那段難挨的日子。
光緒二十五年(1899 年)冬的一天,他應朋友之邀,到某王府唱堂會。戲單上有出《五花洞》,誰知原定來唱這出戲的演員臨時有事沒來,時小福非常生氣,為不使主人掃興,他決定親自粉墨登場,代為演出。主人很高興,為表感謝,在戲演完后,給來唱戲的演員們擺了一桌上好的酒席。不料,時小福竟因心情的關系飲酒過量,第二天就病倒了,雖經很多名醫診治,但始終未見好轉。轉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時小福連驚帶嚇,終在1900 年5 月17 日病逝于北京,享年只有54 歲。
八、梅巧玲
梅巧玲(1842-1882 年),他亦是梅蘭芳的祖父),原名芳,正名芳普,字筱波,一字雪芬,號慧仙,別號蕉園居士,自號梅道人,寓名“景和堂”(位于宣南李鐵拐斜街),故又稱景和堂主人,綽號胖巧玲。祖籍江蘇泰州鳳凰墩鮑家壩。工花旦。
梅巧玲幼時家境貧寒,8 歲時,曾被過繼給一戶姓江的人家,后幾經輾轉販賣。11 歲時,被福盛班班主楊三喜買下,習昆旦和皮黃青衣。楊三喜向以虐待徒弟出名,巧玲在他門下,可謂受盡了百般折磨,據說他的掌紋都被楊三喜給打平了。兩三年后,他又拜在了四喜班的名旦羅巧福的門下,習花旦。羅為人甚是仁厚,課徒授藝亦極認真,且從不打罵徒弟。他不僅出資為梅巧玲贖了身,還將他帶回家中,悉心培育,終使其成才。
梅巧玲藝成后,即露頭角,他不僅扮相雍容端麗、表演細膩逼真,念白文雅脫俗,京昆俱佳。戲路亦是極寬。早期京劇,青衣和花旦的界限還是明顯的,而他于本工花旦戲外,青衣、昆旦戲也無所不能,遂漸為四喜班的臺柱之一,三十幾歲,就成為了四喜班班主。
他常演的劇目有《盤絲洞》《閨房樂》《梅玉配》《浣花溪》《虹霓關》《胭脂虎》《玉玲瓏》《彩樓配》《龍女牧羊》《乘龍會》《五彩輿》《德政坊》《四郎探母》《雁門關》《得意緣》《二進宮》《百花亭》和《密誓》等。另外,還有昆曲戲《百花贈劍》《刺虎》《思凡》《折柳》《小宴》《絮閣》等。
梅巧玲也同其師羅巧福一樣,為人極是仁厚。其時,有一揚州籍探花出身雅愛皮黃的謝御史常和他一起研究字音、唱腔。兩人交情很深。謝探花一生為官廉潔,兩袖清風,所以晚景不是很好,梅巧玲知他家的日子過得艱難,就不時地會拿出些錢來,幫他渡過難關。但他每次拿到了錢款,不論數目多少,都會親筆寫一張借據,送到梅家。這樣,好多年下來,總共積欠了梅巧玲三千兩銀子。謝探花病逝后,在揚州會館設奠,梅巧玲親往吊祭。
梅巧玲吊祭完,就拿出一把借據給謝探花的長子看了,謝的長子看完,就不勝惶恐地說道:“這些欠款,我們都認,只是目前實在沒有能力還上……”梅巧玲搖了搖頭說:“我可不是來要賬的,我和令尊是多年的至交,令尊的去世讓我非常傷痛。我今天過來,除了祭拜,還有就是要了結這件事。”說完,就把那些借據都放在靈前的白蠟燭上燒了。隨事,又從自己的靴統里取出二百兩銀票交給謝的長子,說是奠儀。然后,就黯然登車而去了……
九、劉趕三
劉趕三(1816-1894 年),名保山,別名遷升,字韻卿,號芝軒,寓名“寶身堂”(位于宣南韓家潭),祖籍天津。工丑行,有“天下第一丑”之稱。他自小讀書就很用功,不到20 歲,已頗有文名。奈何屢考不中,乃由業余愛好京劇下海成為專業演員,初學老生,藝宗張二奎,入京后,先搭在永勝奎班(譚鑫培之子譚小培亦當時亦搭在此班)唱戲,后入三慶班,從郝蘭田學藝,常演的劇目有《金水橋》《打金枝》《三娘教子》《桑園會》《武家坡》《天水關》等老生戲。因當時京城老生名角如林,遂改丑行。
他嗓音清亮、響堂,念白清脆爽利,做、表傳神,所演人物無不幽默風趣,又因為他有較高的文化修養,常能于臺上現抓詞,插科打諢、借題發揮,嘲諷權貴,抨擊時弊,可謂“一身是膽,鐵骨鋼腸,從不知權勢為何物”,是以大受戲迷們的歡迎。可以說是正是由于他的出現,改變了過去丑行“重念不重唱”的狀況。
享名后,各班爭相聘請,有時竟同在三四個戲班唱戲,趕場演出,是故時人有諷其為“趕三”者,他非但不以為意,反而取了“趕三”為其藝名。人們常呼其為“趕三兒”,晚年則稱其為“老趕”或“趕公”。其扮演的《請醫》中的劉高手、《連升店》中的店家、《絨花記》中的崔八、《拾玉鐲·法門寺》中的劉媒婆、《普求山》中的竇氏、《探親》中的鄉下媽媽和《思志誠》的老媽兒等,都為一時之冠。
他還有一大創舉,就是在演《探親》時,騎真驢上臺,驢名“墨玉”又名“二小”。他這頭驢的飼養員當時還是個孩子,姓李,乳名鎖兒,由于每天跟他上戲園子看他演出,后來竟也成了一位名演員,即丑角李敬山。
十、楊鳴玉
楊鳴玉(1815-1894 年),名阿金,字儷笙,號鳴玉,乳名娃子,因排行第三,故人亦稱其為“楊三兒”祖籍江蘇揚州甘泉縣。工昆丑。他自幼入蘇州科班,初學昆生,后改為昆丑。藝成進京,先搭在和春、雙奎、老嵩祝成等班,后搭在四喜班唱戲,直到老邁,無法再上臺演戲。他的昆丑戲,功底十分深厚,文武皆精,每戲均有絕妙。其代表劇目,武有《盜甲》《問探》等,文有《借靴》《測字訪鼠》和《風箏誤》等。另外,他演的《教歌》《拐兒》《下山》《活捉三郎》《蘆林》《驚丑》《掃秦》《相梁刺梁》《拾金》《打花鼓》《蕩湖船》和《思志誠》等,亦都堪稱是一時之杰作。
由于他為人耿直,藝術高超,名聲遠播,甲午戰爭后,李鴻章代表清廷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時諺有云:“楊三一死無昆丑,李二先生是漢奸”。
十一、余紫云
余紫云(1855-1910 年),原名金梁,字艷芬,號硯芳,乳名昭兒,寓名“勝春堂”,曾先后居住宣南石頭胡同和李鐵拐斜街,祖籍湖北羅田。工青衣。
他是余三勝之子,京劇老生余派的創始人余叔巖之父。自幼隨父來京,入“景和堂”從梅巧玲習花旦,并私淑胡喜祿習青衣。其戲路很寬,尤精蹺工。同光年間,搭四喜班,經常演出《彩樓配》《三擊掌》《趕三關》《梅龍鎮》《梅玉配》《祭江》《玉堂春》《蘆花河》《打金枝》《孝感天》《金水橋》《二進宮》《虹霓關》和《宇宙鋒》等戲。他的琵琶彈得也很好,演《昭君出塞》,自彈自唱,享譽一時。
余紫云的為人也極耿直,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 年),因不應堂會,而得罪了某巡城御史,不得不告別舞臺。以后,改以鑒賞古董為生,終成一位古玩鑒定大家。在他告別舞臺后,亦常有青年旦角演員登門請益,其中尤以王瑤卿受益最多。
十二、朱蓮芬
朱蓮芬(1836-1884 年),原名延禧,字水芝,號福壽,寓名“紫陽堂”(位于宣南櫻桃斜街),蘇州人。工昆曲。
朱蓮芬幼年時,曾入昆曲科班,習昆旦,其昆曲戲尤以《思凡下山》和《刺梁》最為著名,后又學了皮黃花旦,文武昆亂,各有所長。同治年間,入四喜班,與名丑楊鳴玉合作之《烏龍院活捉三郎》,與名小生王楞仙合作之《奇雙會》,都曾享譽于一時,其他如《小放牛》《秋江》等戲,載歌載舞,亦深為廣大戲迷所推崇。
又,朱蓮芬還很擅長書畫,書學著名書法家潘祖蔭,偶為祖蔭代筆,幾可亂真。得者莫不以為是祖蔭真跡,如獲至寶,加以收藏。其子朱桂秋,初學老生,后改學花旦,亦曾是名振一時,能繼父業。
十三、郝蘭田
郝蘭田(1832-1872 年),字什么?號什么?均未查到,只知他是安徽懷寧人,清末著名京劇老旦演員,也是后來被譽為“京劇改革家”的“通天教主”王瑤卿的外祖父。
他原是徽戲演員,初習青衣,后工老生。早年,嘗以《祭風臺》(也就是《借東風》)中的孔明,而聞名皖中。
他大約是在道光、咸豐之間來的北京。因與程長庚是同鄉,便搭在了三慶班唱戲。入班后,初演《天水關》,飾孔明一角,聲容并茂,氣度高古,一炮而紅,后便在班中與盧勝奎一起,在連臺本戲《三國志》中,分飾孔明一角了。
郝蘭田作為一名老生演員,那他后來怎么又和譚鑫培的父親譚志道一起,被視為是“京劇老旦的奠基者”了呢?
原來,在當時三慶班中,各行當都是人才濟濟,唯缺少一名好的老旦演員。于是,他就自告奮勇地改唱了老旦。
因為他是以老生改行唱的老旦,是以在他老旦的唱腔中,融入了不少老生唱腔的韻味,沒想到他這種在當時來說,可謂是獨一無二的老旦唱腔,竟然大受觀眾的認可,他也便成為了當時京班中最有名的老旦之一。甚至可以說正是由于他這種老旦唱法的出現,才使原在京劇中不怎么受重視的老旦這一行當,地位一下子提升很多。
另外,郝蘭田自從唱上老旦以后,不到一年,凡是老旦應工的戲,就沒有他不會的了。其中,尤以《釣金龜》《四郎探母》《探寒窯》《行路哭靈》《滑油山》《目連救母》《游六殿》《徐母罵曹》和《遇后·龍袍》最為拿手。
后學者有謝寶云、龔云甫等。龔氏也是先學的老生,后改的老旦,并首開了以老旦戲唱大軸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