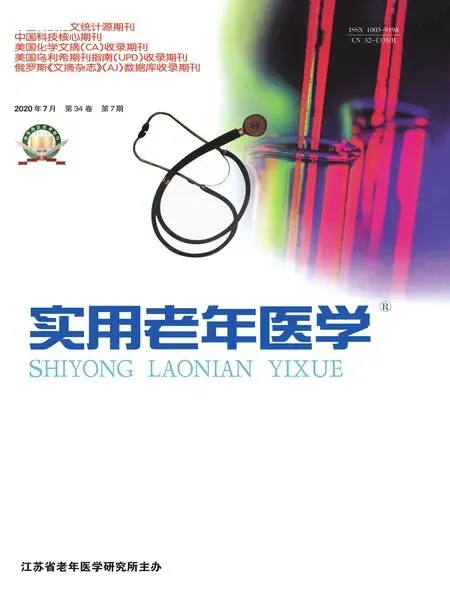關注認知障礙的血管因素診治,是腦卒中防治的基石
徐俊 施炯
中國作為腦卒中大國,近20年來全面推動質控建設,特別是腦血管病急性期診療技術綜合應用使腦卒中病人醫療質量綜合指標提升了3.4%,1年新發血管事件下降了2.7%,1年致殘率下降了2.0%[1]。因此,持續質量控制的效果評價體系必然納入卒中后認知障礙(PSCI)的全面管理內容。突出認知障礙和卒中的整合干預理念,能更有效地指導醫師對PSCI進行規范管理,強調卒中病人的早期篩查評估,規范診治用藥和及時轉診管理,提高病人的生活質量和生存時間,降低復發風險,其中需要明確以卒中病人門診就診為抓手,這對我國老年人群尤其重要[2]。
卒中的防治指南同樣適用于PSCI,控制卒中高危人群的高血壓、DM、高脂血癥等心腦血管病變可以減少卒中的發生,是PSCI預防的基石[3]。除了對高血壓、DM、高脂血癥這些慢性疾病的長期科學管控,還應積極改善生活方式,如合理膳食、適當運動、戒煙、戒酒等。多模式干預也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盡管2017年美國心臟協會/美國卒中協會(AHA/ASA)工作組提出將對無癥狀腦血管病的管理作為卒中的一級預防策略,但對腦內已存在無癥狀梗死或腦白質病變但尚未發生卒中的高危人群的高血壓治療目標值,以及是否啟動抗PLT治療尚無確切的推薦意見。其中,腦小血管病(cerebral small vessel disease,CSVD)成為腦血管病和認知障礙領域研究的“新寵”,不是因為CSVD約占缺血性腦卒中的20%~25%,而是腦內小動脈、微動脈、毛細血管、微靜脈和小靜脈的功能退化和病變是腦血管和認知障礙共同的病理基礎。早期識別和多維度、多層次評估中國CSVD人群的認知功能,特別是注意/執行功能、記憶、語言和視空間功能等4個核心認知域在內的認知功能成套神經心理學量表的標準化工作尤為重要[4]。加強神經影像學標志物研究有助于更準確地對PSCI分型,其中動脈自旋標記灌注成像(artery spin labeling,ASL)、磁敏感成像(susceptibility weighted imaging,SWI)、彌散張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動態磁敏感對比增強(dynamic sucstability contrast,DSC)等新技術進一步提高了對常規MRI難以檢測的腦低灌注、神經網絡損傷和微出血等腦損傷的早期識別水平,因此,應盡快建立標準化參數和檢測流程。
定期評估認知功能應作為卒中防治質控體系的重要模塊,進行持續健康培訓,從病人首診開始,貫穿卒中管理的全程。目前對PSCI的臨床防治主要參考血管性認知障礙(VCI)或癡呆的防治策略,缺乏針對PSCI防治的縱向臨床研究,包括藥物治療、康復治療(包括軀體康復和認知康復)及多模式干預等。而今后,在PSCI的臨床研究開展前,需先建立規范的PSCI臨床研究模式:包括入組標準(涉及PSCI的診斷、卒中前認知評估)、結局評估(涉及認知評估方法、混雜因素的影響)等。PSCI的高度異質性決定了針對不同PSCI類型/認知領域損害的臨床分型需進行分層研究,為PSCI病人提供精準的預防及治療證據[5]。
PSCI人群中,遺傳性腦小血管病(hereditary cerebral small vessel disease,HCSVD)導致的認知障礙應引起重視。既往認為伴皮質下梗死和白質腦病的常染色體顯性遺傳性腦動脈病(cerebral autosomal dominant arteriopathy with subcortical infarcts and leukoencephalopathy,CADASIL)、伴皮質下梗死和白質腦病的常染色體隱性遺傳性腦動脈病(cerebral autosomal recessive arteriopathy with subcortical infarcts and leukoencephalopathy,CARASIL)、遺傳性彌漫性白質腦病并軸索球樣變(hereditary diffuse leukoencephalopathy with spheroids,HDLS)等單基因CSVD臨床罕見,但掌握其臨床特征,有助于早期識別并及時干預[6]。而遺傳因素作為卒中和認知障礙共同的病理機制之一,開展大樣本中國卒中人群遺傳易感關聯分析,發現易感風險基因位點,對個體臨床發病風險預測有一定的參考意義。霍勇等[7]長期從事伴有Hcy水平升高的“H型高血壓”研究,發現與常規降壓治療相比,中國H型高血壓病人使用葉酸添加治療可進一步降低卒中風險21%,并且更有效降低缺血性腦卒中風險24%,降低心血管復合終點事件風險20%。總Hcy水平升高是認知功能損害和癡呆的一個密切但可干預的危險因素。
陶帶花等[8]連續隨訪腦梗死病人6個月的認知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發現老年病人PSCI發生率更高,且累及多個認知領域。這種定期隨訪有助于提高卒中病人服藥依從性。研究提示,病人的服藥依從性隨時間推移而下降,而認知功能障礙可能降低了病人服藥依從性,對病人和家庭成員的健康培訓可能有助于提高病人服藥依從性[9]。
其他治療手段,如經顱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TMS)、經顱直流電刺激和虛擬現實技術等無創性腦刺激康復新技術初步展現了對PSCI人群的治療潛力,應盡快開展針對不同類型PSCI病人的認知康復訓練方案,以及研發小巧化、信號整合化、模塊化、智能化和任務導向化的可穿戴設備,積極開展藥物和非藥物治療方法及其干預機制的對照隨訪研究,推動非藥物治療以及智能化可穿戴式設備在腦卒中防治體系中更廣泛的應用[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