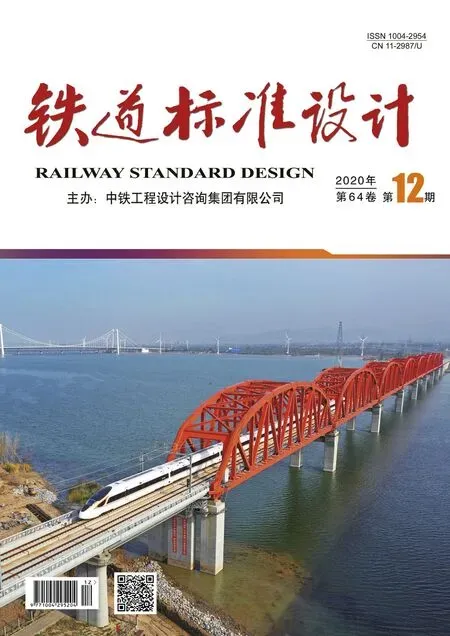考慮多土層的波-流荷載下跨海橋梁樁基動力響應分析
潘 良,祝 兵,張家瑋,康啊真
(西南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院,成都 610031)
樁基礎具有承載力高、基礎沉降小等優點,且樁的布置方式靈活多變,設計時可通過調整樁的數目及布置來滿足橋梁結構的使用性能要求,因而在橋梁工程中廣泛應用[1]。其中跨海大橋所處的海洋環境十分惡劣,設計使用年限內承受著風、浪、流、潮汐、地震等多種環境荷載作用,波流力作為工程設計的控制荷載[2-3],尤其對于承受上部結構的樁基而言更是主導荷載,它嚴重影響整個工程的造價、安全性以及工程的使用壽命。一旦樁基結構遭到破壞,整個海洋工程結構將會蒙受不可估量的損失。因而研究波流力對樁柱結構的作用是很有必要的。
對于小直徑樁柱所受的波浪力,工程實際計算中仍采用Morison公式。樁基結構在波流荷載下的動力響應分析中,趙暉[4]采用Winkler彈性地基梁模型模擬樁-土動力的相互作用,由解析法給出了埋置圓樁在波-浪-流場下的動力響應。沈錦寧[5]將樁離散成多質點系,用水平土彈簧計算土抗力,研究了波浪作用下單樁基礎的動力響應。胡丹妮[6]利用Ansys軟件建立樁-土三維有限元模型并引入p-y曲線修正,計算波浪荷載對樁基的動力響應。周靜姝[7]用Ansys軟件建立樁-土三維有限元模型,計算實際工程中波浪荷載對多土層樁基的響應。付鵬[8]采用三維數值分析方法,建立了考慮流固耦合的三維樁-土模型,來模擬波浪對樁及海床的直接作用。大多數研究并未考慮到波浪與流的相互作用及KC數對水動力系數的影響,以及多土層土體下的樁土相互作用。
本文基于Morison方法得到不同參數的波-流荷載,根據實際工程利用Abaqus有限元軟件建立樁-土相互作用模型,來研究波-流荷載作用下,樁基礎分別在實際多土層土體與單土層土體情況下的動力響應,以及不同波流荷載工況下單樁與群樁響應隨荷載參數的變化,為實際工程計算提供參考。
1 工程概況
本研究依托在建甬舟鐵路金塘特大橋的基礎土層和水文條件[9]。金塘特大橋全長8 722.65 m,跨海段長5 188.265 m,其中金塘水道上為公鐵合建雙塔懸索橋(112+224+1 050+238+42) m。橋址處為臺風影響區,強風天氣天數多。年平均波浪高1.14 m,最大波高6.1 m。
索塔墩位處水深49 m,金塘航道橋立面與索塔墩位處群樁樁基布置見圖1。其中,群樁由34根單樁與承臺構成,樁柱沿縱橋向分為4排,中間兩排各9根,前后兩排各8根,排間距9 m,每排中,樁心距為9 m,單根樁長129 m,樁徑4.5 m,樁基混凝土采用C50。
2 模型建立
現針對施工階段單樁與索塔墩下群樁建立實際情況下的多土層模型,以及單土層模型a(土體全為土層1粉土性質)、單土層模型b(土體全為土層2粉砂性質)、固接模型(不考慮樁土相互作用,在泥面高度處固接樁體)作對比分析。三類單樁模型土層示意見圖2。

圖2 三類單樁模型土層示意
2.1 材料與接觸設置
樁基彈性模量為3.4×104MPa,密度為2.5 t/m3。土體采用摩爾-庫倫模型。在Abaqus中采用分區功能劃分土層并賦予其對應的性質,由上到下按土層序號設置材料參數、接觸摩擦屬性與預應力側壓力系數。樁側與各土層土體接觸均設置為面-面接觸,以樁基為主面,土體為從面,法向接觸類型為硬接觸,切向摩擦為罰摩擦[10]。各土層土體相關物理力學參數如表1所示。
2.2 網格劃分
單樁模型土體尺寸為150 m×150 m×260.43 m;群樁模型土體尺寸為760 m×760 m×260.43 m。單樁樁長129 m,直徑4.5 m,埋深86 m,入水深度43 m。樁基與土體均采用C4 D8單元,并在樁土接觸區域細化土體網格,保證接觸處土體網格尺寸小于樁身網格。單樁樁頂自由,群樁各組成樁的尺寸同單樁模型,頂部有承臺固接約束。建立單樁、群樁模型如圖3所示,總體網格數單樁模型約13萬個。研究中采用的簡化群樁模型與未簡化的群樁模型進行了計算對比,誤差在1%以內。為了提高計算效率,采用簡化后的群樁模型計算,簡化后的群樁模型總體網格數約18萬個。

表1 土層物理力學參數
2.3 波-流荷載計算
計算波-流荷載的方法有多種[11-12],本文不考慮波浪力的非線性[13],采用有流參與的Morison公式計算圓截面樁受到的波流荷載,并參考JTS145—2015《港口與航道水文規范》,根據KC數選取不同工況下對應波流荷載的水動力系數Cd,Cm。其中KC數根據式(1)計算,Umax為表面水質點最大水平速度,T為周期,D為圓柱樁直徑。土體上施加對應49 m水深的靜水壓力,并在地應力平衡分析步采用導入應力場的方法。

(1)

圖4 波-流荷載沿樁分布
利用Matlab計算考慮波流相互作用的樁基波流力。對于群樁,又考慮了不同組成樁間的波流荷載相位差。圖4為計算得到的單樁某一波流荷載沿樁分布情況。圖5為群樁各組成樁的編號與波流荷載入射平面示意。本文計算采用隱式瞬態分析步,忽略前段的瞬態響應,取最終的穩態響應為結果。
單樁與群樁所有波流荷載工況參數范圍根據甬州鐵路金塘大橋橋址處水文資料擬定。

圖5 群樁布置形式與波流荷載入射示意
3 不同土層模型的影響
3.1 不同模型的動力響應
為了解四類模型的單樁在相同波流荷載下的響應差異,設定波流荷載周期為5 s,波高1.8 m,流速1.0 m/s,計算四類模型的穩態響應。如圖6(a)為四類模型穩態時樁頂參考點沿波流向位移Y的時程變化,由圖可見多土層模型與單土層模型a穩態時樁頂位移幾乎重疊,且位移峰值與幅值均大于單土層b模型,明顯大于泥面處固接模型;前三類模型樁身最大主應力出現在樁基迎波流向的泥面稍下處,固接模型最大主應力在泥面固接處,以各類模型樁身最大主應力為參考應力S,如圖6(b)為四類模型穩態時最大主應力的時程曲線,前三類模型最大主應力時程曲線幾乎重疊,其峰值均大于固接模型。
圖7為四類模型穩態時,以泥面處為零點,沿樁身的彎矩內力包絡圖,泥面固接模型的最大彎矩遠大于前三類模型,多土層模型、單土層模型a、單土層模型b的樁身彎矩包絡圖只在泥面下稍有區別,單土層模型b在泥面下彎矩較小,主要是土體彈性模量較大,下部樁身位移較小。

圖6 四類模型樁頂位移、樁身最大主應力時程曲線

圖7 四類模型穩態時樁身彎矩內力包絡圖
實際上通過對比四類模型,發現多土層模型、單土層模型a響應參量值差異基本在0%~5%以內,即令整個土體等同于多土層情況下的表層土,對單樁水平波流荷載下的響應影響很小,此結論是在表層土占實際樁體埋深約25%時得出的。單土層模型b對比多土層模型相差較多,主要是該實例中第二層土體性質與表層土體差異較大,如彈性模量相差近1倍。固接模型與多土層模型相比其他兩類模型結果差異更大,這是因為固接模型以泥面處的固接約束替代實際泥面下的樁-土相互作用,大大增加了橫向剛度。
3.2 不同模型穩態響應的統計值差異
令波流荷載波高1.8 m,流速1.0 m/s,計算8個不同周期(5,6,7,8,9,10,11,12 s)工況下四類模型的穩態響應。對穩態時樁頂位移與樁身最大主應力選取至少5個周期的時程數據,得到對應工況下峰值的平均值,并分別作為統計值Ymax和Smax,令圖7彎矩包絡圖的最大彎矩值作為對應工況的樁身最大彎矩統計值Mmax。
如圖8所示,不同模型在相同波流荷載下的響應存在一定差異。對比多土層模型結果與固接模型結果,多土層模型樁頂位移約為固接模型的2~3倍,最大主應力約為固接模型的1.3~1.5倍,樁身最大彎矩在固接模型的68%左右。對比前三類模型,多土層模型、單土層模型a的樁頂位移、樁身彎矩及最大主應力相差很小,單土層模型b除了最大主應力(波浪荷載對樁身重力作用平衡下的最大主應力影響較小),樁頂位移與樁身最大彎矩均同多土層模型、單土層模型a有明顯區別。
三類模型中多土層模型模擬實際的土層分布,單土層模型a土體采用表層土體,其中表層粉土土層厚度只占樁基入土深度的24.4%,但是兩者結果十分接近,單土層模型b采用的粉砂土層為實際樁基泥面下的第二個土層,厚度占樁基入土深度38.5%,其與多土層模型結果差異較明顯,一是因為粉土土層與粉砂土層土體參數差異較大,二是實際情況下粉砂土層在樁基下部較深的位置,對樁基響應的影響相對于表層的粉土土層小。
4 波-流參數的影響
4.1 周期影響
為研究不同波流參數對樁基動力響應的影響,以多土層模型作為研究模型進行不同波流參數的動力響應計算,并以固結模型作為對照。令,波流波高1.8 m,流速0 m/s,周期為5~12 s,計算得到多土層模型與固接模型的穩態響應,并按上節方法得到各參量統計值。圖9為兩類模型的樁頂最大位移Ymax,樁身最大主應力Smax與樁身最大彎矩內力Mmax隨波流周期的變化。可見Ymax,Smax,Mmax三個統計值均隨波流周期增加而非線性減小,除了樁身最大彎矩外,多土層模型樁頂位移與樁身最大主應力均大于固接模型。

圖9 多土層模型與固接模型響應峰值隨周期的變化規律
4.2 流速影響
令,波流周期5 s,波高2.2 m,取流速分別為0,0.5,1.0,1.5 m/s。如圖10所示,兩類模型的Ymax,Smax,Mmax值在選取的流速范圍內結果改變較小,但有先下降后上升的趨勢,其中位移增幅在30%以內,應力增幅在25%以內,彎矩增幅在10%以內。

圖10 多土層模型與固接模型響應峰值隨流速的變化規律
4.3 波高影響
令,波流周期5 s,流速為0,分別取波高2.2,2.6,3.0,3.4,3.8,4.2 m。如圖11所示,兩類模型的Ymax,Smax,Mmax值幾乎都是隨波高線性增加。
固接模型與多土層模型的結果對不同參數變化有著相同的規律,Ymax,Smax,Mmax隨波流荷載周期的增加而非線性減小,隨流速增加先減小后增大,且增幅較小,隨波高線性增大。多土層模型除了樁身彎矩遠小于固接模型外,其樁頂位移與樁身最大主應力均大于固接模型。

圖11 多土層模型與固接模型響應峰值隨波高的變化規律
5 群樁效應的影響
相比單樁,群樁效應主要來源于兩方面,一方面是上部樁與樁之間相互影響使得波流場改變,導致波流場對每根樁的荷載改變;一方面是下部土體應力狀態相比單樁不同,多個樁之間擠壓土體產生的應力相互影響與疊加。本文利用Abaqus樁-土接觸模型模擬下部土體群樁效應。
5.1 荷載周期與入射角對群樁的影響
本文中群樁基礎方案實際相對樁距S/D=2(S為樁心距,D為樁徑),不同波流入射角情況下,不同樁柱上的波流荷載都存在固定相位差[14-15],利用Matlab編程計算圖5布置形式下不同樁上的波流時程荷載。選取0°,15°,30°,45°,60°,75°,90°共7個入射角工況,其中波流荷載周期9 s,波高2.6 m,流速1.0 m/s。圖12為兩類模型的樁頂承臺處位移與樁身最大主應力隨入射角的變化曲線。可見兩個模型的響應均隨入射角增加而增大,多土層模型比固接模型的位移和應力更大。

圖12 群樁在兩類模型位移、應力隨入射角的變化

圖13 群樁在兩類模型的位移、應力隨周期的變化曲線
令入射角為0°,波高2.6 m,流速1.0 m/s,設置5,7,9,11 s四個不同周期的工況。如圖13所示,兩類模型承臺處位移與樁身最大主應力并非隨周期單調變化,呈現不規律性,除了有限體積土體模型對整個結構頻率的微小影響外,作用在各排樁上的波流力存在相位差異,通過樁頂承臺約束,導致整個群樁所受波流力合力并未呈現單樁那樣隨周期變化的規律。
5.2 波流荷載群樁效應的影響
一般工程計算中未考慮各樁柱對上部波流場的影響,即流場群樁效應。本文的計算忽略承臺對上部波流荷載的影響[16]及波流橫向力[17],通過引入群樁效應系數考慮上部群樁效應,并與未考慮上部群樁效應的結果作對比。
對應設置工況下的相對樁距與KC數,參考文獻[18-22]關于雙樁、三樁串并聯的群樁效應系數及九樁串聯群樁的實驗結果,計算S/D分別為1.5,2,3時各組成樁的群樁效應系數,令波流荷載入射角0°,周期9 s,流速1 m/s,波高2.6 m,表2為相對樁距S/D=2時各組成樁的群樁效應系數。

表2 相對樁距S/D=2時各組成樁群樁效應系數
圖14為群樁多土層模型與固接模型在考慮上部波流場群樁效應與未考慮群樁效應情況下,承臺處位移與樁身最大主應力隨樁間距的變化。

圖14 兩類群樁模型位移與應力隨相對樁距的變化
相對樁距S/D值較小時,樁列對波流的阻塞效應使樁處流速增大,樁頂位移與最大主應力均大于未考慮上部群樁效應的結果,且在S/D=1.5時差異更加明顯。而在S/D=3時,考慮上部群樁效應的結果偏小,這是因為組成樁的間距增加,存在前方樁對后方樁的遮蔽效應,使得群樁效應系數小于1,群樁合力小于各單樁上力的疊加。隨著相對樁距的增加,組成樁周圍的流場更接近獨立單樁,群樁效應逐漸減弱,兩種響應也逐漸趨同。對比固接模型,群樁效應造成的響應差異,沒有多土層模型明顯,是因為群樁效應引起的波流荷載大小改變較小,而群樁固接模型剛度較大,相應地響應差異也變小。
6 結論
根據實際工程中的樁基及土層信息建立樁-土相互作用模型,采用Morison方法得到不同參數下的波-流荷載。對比研究了波-流荷載作用下樁基礎在不同土層模型的動力響應,以及不同波流荷載工況下單樁與群樁響應隨荷載參數的變化,具體結論如下。
(1)波流荷載作用下的單樁動力響應,如樁頂位移、樁身最大主應力與樁身最大彎矩均隨波流周期增加而非線性減小;隨波流波高增加線性增大;隨流速增大先減小后增大,且增幅較小。
(2)單樁多土層模型相比單土層模型,波流荷載下的動力響應差異很小;較深處土層性質對波流荷載下單樁動力響應的影響很小。
(3)群樁位移與應力響應隨周期變化規律不同于單樁,本文布置形式的群樁,位移隨入射角增加基本呈線性增加,樁身最大主應力先增加后減小。
(4)考慮上部流體群樁效應后得到的響應與未考慮時的響應在相對樁距S/D為1.5或2時前者更大,相對樁間距為3時后者更大。實際群樁施工設計可簡化土體性質等同為表層土體,在較小樁間距情況下不可忽略上部流體群樁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