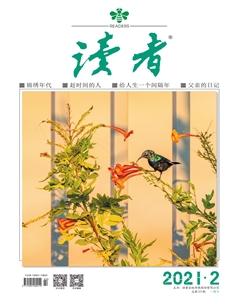馬糞爭奪案

這個案子發生在1869年4月6日。原告請了兩名幫工,到馬路上撿馬糞。他們倆從晚上6點干到8點,在馬路上共堆了18堆馬糞。馬糞堆起來以后,因為太多不好搬運,兩位幫工就回去取車,準備第二天來搬,但他們并沒有在這18堆馬糞上做任何標記。
第二天早上,案中的被告看見了這些馬糞,就問附近巡邏的人:這些馬糞有沒有主人?有沒有人要把馬糞運走?巡邏的人說不知道。被告聽了以后,覺得這些馬糞沒有標記,也沒有主人,就把馬糞運回自己家,撒到了自家的田里。
到了這天中午,兩位幫工帶著車過來,發現馬糞沒了,一問之下,才知道原來是被告運走了。于是雙方發生爭執,最后鬧到法庭上。
鼓勵創造財富,還是鼓勵對財富做標記
在法庭上針鋒相對的,有這么幾種觀點。
一是“溯源說”。有人主張,馬糞真正的主人是馬,也可以進一步說,馬糞屬于馬的主人。但問題是,馬的主人把馬糞丟在路上,就說明他放棄了對馬糞的所有權。
二是“位置說”。被告主張,馬糞掉到馬路上,就成為馬路的一部分,而馬路是公家的,所以誰見了馬糞都可以拿走。原告讓幫工把馬糞堆起來,只是改變了馬糞所在的位置,并沒有改變它的所有權,因而馬糞不歸原告所有。
三是“標記說”。法庭上也有人主張,關鍵看原告有沒有給馬糞做標記,如果沒有做標記,那就不能怪別人把馬糞運走了。
四是“勞動說”。原告堅持認為,是幫工們花費了工夫,才把馬糞堆積起來的,所以馬糞應該歸原告所有。
各方好像都有道理。但哪種觀點更正當呢?如果你是法官,會把馬糞判給誰?
鼓勵人們創造財富,社會才會越來越好
事實上,一點兒馬糞,判給誰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案件會對后代產生怎樣的影響。設想一下,有兩個村子,發生了同樣的案子,唯一不同的是,第一個村子把馬糞判給了原告,也就是堆積馬糞的人;第二個村子把馬糞判給了被告,也就是那個看見馬糞就把馬糞運走的人。這兩個村子,過50年、100年后,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可以設想,在第一個村子里,由于把馬糞判給了創造財富的人,那么村民就會有這樣的預期:凡是經過人類勞動的成果,都是財富;凡是財富,就都有主人;有主人的財富是受到法律保護的。要尊重別人的財富,不能見到就拿走。只要有這樣的共識,這一共識又變成傳統,那么在這個村子里,人們就用不著花太大的工夫來保護自己的財富,他們因此也會更積極地去創造財富和積累財富。50年、100年后,這個村子就會走向富足。
在另一個村子里,法官把馬糞判給了被告,那么村民就會形成另外一種預期:只要是沒人看管的東西,就可以隨便拿走。于是,順手牽羊的行為就會大增,有產者花在看管財富上的努力就會變大,大到足以抵消財富本身的價值。人們不僅會喪失創造和積累財富的積極性,即便創造和積累了財富,其價值也會被保護財富的努力抵消。50年、100年后,這個村子就會走向貧困。
當年的法官,就是根據這個思路,把馬糞判給原告的。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這個判決意味深長。
公正背后是效率考量
尊重別人的財富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的公正觀,但其背后,是對效率的考量——保護產權的努力是會消耗資源的,這種消耗越大,資源的凈值就越低;社會的道德規范越是能夠幫助減少這種消耗,社會財富的積累就越多。
在生活中,很多人討論什么才是公正的,背后其實很可能是在對效率做出考量。
我們不能隨便把人投進監獄,除非給他一個公正的審判,否則就是不公正的——這背后的效率考量是:如果人力資本會受到隨意的破壞,人們就不會有積極性去積累自己的人力資本,懶惰和無知就會成為世界的常態。
我們不能隨便拿人家的東西,除非給出合理的補償,否則就是不公正的——這背后的效率考量是:如果可以隨便拿別人的東西,就不會有人積極地去愛護、積累自己的財富。
交通肇事者應該負責任,否則就是不公正的——這背后的效率考量是:如果交通肇事者不需要負責任,交通狀況就會非常混亂,效率就會降低,馬路的價值就會消失。
當我們討論公正的問題時,背后的含義往往是:這是符合效率標準的。往往是那些讓每個人都有積極性去積累財富的規則,或者那些讓社會能夠健康發展的規則,才是公正的規則。也就是說,因為有效,所以公平。
當別人在討論到底是公平重要,還是效率重要的時候,學過經濟學的人明白,公平背后往往是效率的考量,不是對單個人的效率的考量,而是對整體社會長遠發展的效率的考量。公平和效率,往往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三秋葉摘自中信出版集團《薛兆豐經濟學講義》一書,小黑孩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