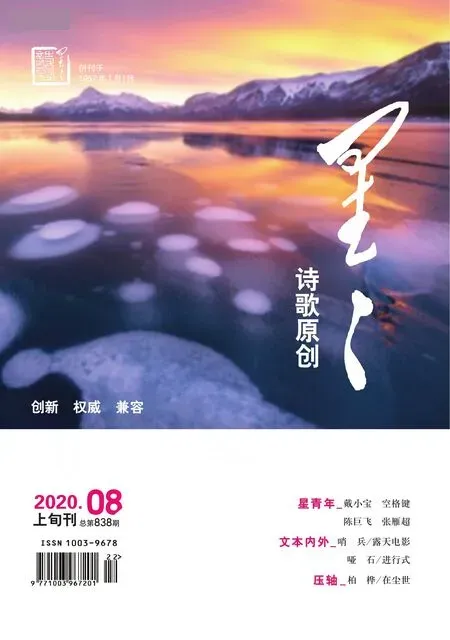在塵世(組詩)
柏 樺
永 恒——紀念我的舅舅楊嘉格和一個電工
五十年前,我的舅舅帶我去重慶一個電工家吃過一頓午飯,那電工儀表含蓄溫柔,炒的京醬肉絲令我終生難忘;在那個炎夏的正午,我甚至立刻改變了我對重慶酷暑的印象。
故事沒有繼續,記憶卻從未停止……
我這一生,只是一個善于根據劇本
表演的演員嗎?我突然發揮出來了——
那是重慶臨江門千門萬戶中的一戶——
世界的舞臺來到一個電工之家,頂樓,
正午,我看見了陽光下的嘉陵江……
重慶的夏天風涼,因一盤虎皮青椒
一盤松花皮蛋,一盤京醬肉絲……
重慶的夏天安逸,因我們三人的午餐,
我十五,舅舅三十五,電工二十五。
“廚師因某個夢而發明了這個現實。”
電工!你正是這個永恒現實的廚師。
人生因多年后幾人相憶在江樓——
最后的幻覺,我們無酒便不眺望……
下午,養老院
在養老院,人除了坐著
還能做什么呢?等待那
無盡的下午點點來消磨
而生命對于下午已晚了
可越晚人越愛反復訴說
血流得慢,人重習走路
風吹來,人已沒有感覺
一生詞與物終是人遺物
永日不可暮?而人是誰?
某人少年時耕耘臉且白
某人老了,洗衣手亦潔
悲哀是因天氣引起的嗎?
此地如北歐,冬日漫長
人坐著,懷念年輕的太陽
煙與重
一
洗碗、曬被、削梨、吃酒……“這就完啦?”
你再想想,該以“啦”結尾,還是“了”。
……電扇葉可旋轉出風,可削斷鉛筆。
一分硬幣可買一顆糖,可用其邊緣磨平指甲。
你做的面條真好吃呀,可朋友終歸要分手的。
看看那石橋鋪的煙囪吧,張奇開說:
她最后留給人世的形象是煙……
二
箱子再重對于內心重的人來說,也是空的。
東亞人何來金眼,重白化病人的眼似金非金。
鳥兒比蝴蝶重,很自然,鳥兒沒有蝴蝶逸樂。
好重!二十個春天生活,二十把梳子梳過。
聽力與邏輯有關聯嗎?大學畢業坐火車回家,
他感到前途的沉重。終于到了孫女上學的秋天,
牛皮紙包書聲音好聽,星期天沒有重人。
霧的小知識
一個詩人米沃什說霧一早就散了
他在花園里干活……
一個詩人聶魯達說在霧的童年
他誕生了翅膀和傷心……
還有個詩人桑德堡說霧來了
在港口,踮著小貓的腳……
曹操騰蛇乘霧,秦觀霧失樓臺
在江南白居易花非花,霧非霧;
胡蘭成與朋友或愛人白日游冶,
夜里說話,每每說到霧重月斜……
關于霧,我們還知道些什么呢?
霧都倫敦有孤兒,霧都重慶生寒夜,
你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
我從霧里來,要到霧里去。
愛在說話
春天的蘋果樹下,山峰的白雪下
有一個藍色國家帶來斜坡的遠思——
長夜將盡外出偷馬,下一代青年懂嗎?
我不當書商,我怎么會去寫小說
現實的檢票口也是超現實的檢票口
瑪麗娜的電話線也是張棗的電話線
好難,從挪威到捷克,從捷克到中國
“專橫的鄉間!電報線!”——
不是電話線。活死人總是一個女人……
破曉起床的人總是孤獨的人。
人為渴望平靜才需要吶喊嗎?
他用詩殺了三個人,用謝謝再殺一個人。
最后又來了一個人,他為聽
“抽屜關上的聲音——愛在說話”
蘭波繡像
“告訴我,什么時候才能把我送到碼頭。”
——蘭波臨終語
人的一生
短的瘋,長的痛。
你別了發卡
我抹了發蠟
唉,埃塞俄比亞……
一曲微風能換什么呢?
換取她的襪子!
可不知哪一天。等著吧——
童年的燕尾服像一只悲傷的燕子
管理員夫人帶鼻音,露出兩顆牙
一切都已經等不及了
如果《元音》重寫于布魯塞爾多好
“奧米茄眼里有紫色的柔光!”
唉,埃塞俄比亞……
在塵世
黑夜里亭子飛了起來,多么令人驚恐
那時,我們已不在了,只余聲音留存
那時,我們又變成了什么?去了何方?
燈光靦腆,人將飲茶,世界破曉在即……
我想起一個人,十年前坐在我的左手邊
莫喪氣,那人,你怎么可能會孤單呢?
在塵世,無論芬芳還是難聞還是無味
每秒的生氣都試探著我們生命的官能!
上街,你總感覺是第一次外出,為什么?
和她在一起,你就心跳加快,為什么?
巴黎手風琴,羅斯手風琴,中國手風琴……
活在人群里我分辨不出我呀,川音的
視唱練耳卻讓我脫穎而出——比利時——
你在哪兒啊?在成都玉林嗎?在塵世。
惋 惜
日落時分,纖維桌布會發出閃光。
小紙箱里不見了解剖學書籍,
只有六本連環畫,兩張風景照片
一陣風,我從嘉陵江橋頭歸來
夜行驛車剛駛入上清寺郵局
(巴烏斯托夫斯基到重慶了嗎?)
真巧,迎面有一個小腳手架
有一格木頭窗戶,但沒有樹蔭
水泥地面的室內亮得雪白呀
流水嘩嘩不停……她來自北京……
四十七年后地理作廢,人在哪里?
那醫生之子每逢酒后雙目放光!
他會聽懂我這句偷來之詩:
五十九歲的我為十二歲的我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