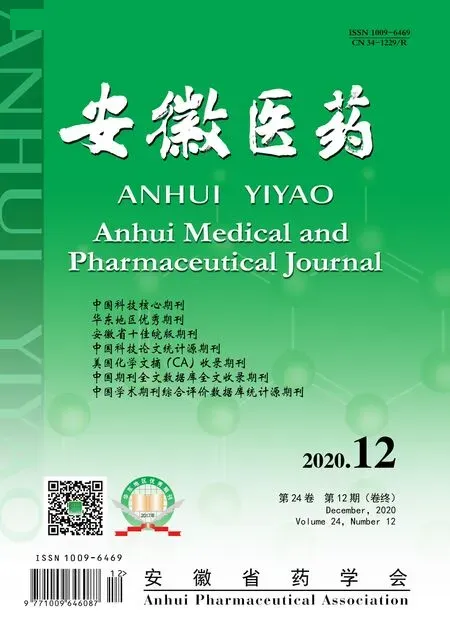動脈瘤性蛛網(wǎng)膜下腔出血后遲發(fā)性腦缺血發(fā)生機(jī)制的研究進(jìn)展
劉昊楠,李愛民
作者單位:南京醫(yī)科大學(xué)連云港臨床醫(yī)學(xué)院神經(jīng)外科,江蘇 連云港222000
在全世界范圍內(nèi),腦卒中的發(fā)生率仍居高不下[1]。在中國,腦卒中已是中國人目前第一大死亡原因[2-3]。顱內(nèi)動脈瘤破裂所致的動脈瘤性蛛網(wǎng)膜下 腔 出 血(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aSAH)是一種嚴(yán)重的腦卒中亞型,一般由看似健康的個體突然發(fā)作,預(yù)后一般不良[4]。遲發(fā)性腦缺血(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DCI)是aSAH后的一種并發(fā)癥,又稱癥狀性腦血管痙攣,表現(xiàn)為無法歸因于其他原因(如腦積水、再出血或癲癎等)的新的局灶性神經(jīng)功能損害出現(xiàn)或格拉斯哥昏迷指數(shù)(Glasgow Coma Scale,GCS)評分削減兩分或更多,頭顱CT平掃可幫助診斷。DCI發(fā)生機(jī)制復(fù)雜,常致使病人病情惡化或生活質(zhì)量降低,對其發(fā)生機(jī)制的了解有助于更好地防治DCI。現(xiàn)將近年來DCI發(fā)生機(jī)制的研究進(jìn)展綜述如下。
1 腦血管痙攣
腦血管痙攣是指在CT血管造影(computeriz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CTA)、磁共振血管造影(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MRA)或數(shù)字減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等影像學(xué)檢查中觀察到腦的大的動脈收縮。有研究者[5]將腦血管痙攣稱為“DSA顯示的血管痙攣”,以區(qū)別于癥狀性血管痙攣(即DCI)。在蛛網(wǎng)膜下腔出血(subarachnoid hemorrhage,SAH)后有高達(dá)70%的病人發(fā)生腦血管痙攣。而DCI僅在30%的病人中被觀察到,且并不總是位于腦血管痙攣的血管分布范圍內(nèi)[5]。因此,DCI可以在沒有腦血管痙攣存在的情況下發(fā)生,這種現(xiàn)象可能是由其他因素驅(qū)動的。尼莫地平作為唯一經(jīng)美國食品藥品監(jiān)督管理局批準(zhǔn)的預(yù)防SAH后DCI的藥物,對腦血管痙攣并未表現(xiàn)出突出療效。盡管如此,最近許多臨床試驗都是以腦血管痙攣為目標(biāo),以期預(yù)防DCI。在動物研究表明內(nèi)皮素受體在腦血管收縮中的作用后,人們對內(nèi)皮素受體拮抗劑克拉生坦進(jìn)行了一項隨機(jī)臨床試驗,簡稱“CONSCIOUS試驗”[6],發(fā)現(xiàn)腦血管痙攣顯著減少。然而,這項研究并未表明疾病發(fā)病率、死亡率或結(jié)局預(yù)后差異有統(tǒng)計學(xué)意義[5-7]。盡管這些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但它們表明腦血管痙攣并不是導(dǎo)致SAH后DCI的唯一因素。
2 微循環(huán)障礙
除了在腦實質(zhì)外較大的血管上發(fā)生腦血管痙攣外,腦實質(zhì)內(nèi)小的血管同樣有所改變。在腦實質(zhì)內(nèi),發(fā)生在小動脈和毛細(xì)血管水平上的變化主要包括大腦自動調(diào)節(jié)、神經(jīng)血管偶聯(lián)以及血腦屏障功能的破壞。相比于顱內(nèi)較大血管發(fā)生的腦血管痙攣,微循環(huán)障礙在臨床上通過血管造影或經(jīng)顱多普勒(transcranial doppler,TCD)檢查并不易被發(fā)現(xiàn)[8-10]。研究發(fā)現(xiàn),尼莫地平對較大血管發(fā)生的痙攣沒有顯著影響,但它能夠抑制小動脈的收縮[11],這可能是尼莫地平治療DCI的一種作用機(jī)制。
腦血流量的維持依賴于腦自動調(diào)節(jié)和神經(jīng)血管偶聯(lián),兩者在SAH后都受到干擾。大腦的自動調(diào)節(jié)使得在動脈血壓發(fā)生大幅度變化時腦血流量仍能維持穩(wěn)定,而神經(jīng)血管偶聯(lián)允許腦血流量發(fā)生局部變化以適應(yīng)不同程度的神經(jīng)元活動。在SAH后觀察到動脈壓的波動導(dǎo)致腦血流量的較大變化,表明腦自動調(diào)節(jié)功能受損[11]。而神經(jīng)血管偶聯(lián)功能的紊亂則與神經(jīng)血管單元水平的損害有關(guān),神經(jīng)血管單元由內(nèi)皮細(xì)胞、周細(xì)胞、平滑肌細(xì)胞、神經(jīng)元和膠質(zhì)細(xì)胞組成。在正常生理條件下,神經(jīng)血管單元會引起微血管擴(kuò)張以應(yīng)對較高的神經(jīng)元活動。然而研究表明,在SAH后這種神經(jīng)血管偶聯(lián)發(fā)生了逆轉(zhuǎn),不再是引起血管舒張,反而是導(dǎo)致血管的收縮[12]。逆轉(zhuǎn)的神經(jīng)血管偶聯(lián)引起的血管收縮可導(dǎo)致缺血性損害,有可能表現(xiàn)為DCI。平滑肌細(xì)胞和周細(xì)胞的活化可致使微血管收縮和局部低灌注,這種收縮可能是SAH后大量血管活性物質(zhì)釋放的結(jié)果,這些物質(zhì)沿著血管系統(tǒng)到達(dá)更小的血管,引起小血管自身生理狀態(tài)變化,這些變化包括一氧化氮通路的改變、氧化應(yīng)激反應(yīng)、細(xì)胞黏附分子及炎癥改變[10]。在血腦屏障水平上,已經(jīng)顯示了一些促進(jìn)腦水腫和神經(jīng)炎癥的改變。SAH后觀察到的毛細(xì)血管形態(tài)變化包括:血管腔內(nèi)皮突出和星形細(xì)胞終足腫脹從而壓縮血管腔,緊密連接打開,基質(zhì)金屬蛋白酶破壞基底膜[10,13],其中許多變化可能是長期存在的。綜上所述,SAH后腦的缺血性損傷與微血管系統(tǒng)損傷有關(guān)。
3 微血栓形成
微血栓可在大腦中引起相應(yīng)的微梗死灶,從而對神經(jīng)功能產(chǎn)生不利影響。許多研究表明SAH后病人凝血和纖溶系統(tǒng)發(fā)生改變[8,14],這些改變可能與微血管痙攣密切相關(guān),因為微血管痙攣后,將引起血流動力學(xué)的紊亂以及血管內(nèi)皮細(xì)胞功能障礙,這些都是引起血栓形成的重要因素。此外,SAH發(fā)生后,病人血小板活化水平升高,并且有研究發(fā)現(xiàn)DCI病人中存在微血栓形成的現(xiàn)象,這表明血小板活化水平的升高可能與DCI的發(fā)展相關(guān)[15-17]。DCI病人中出現(xiàn)的神經(jīng)功能障礙也可能是微血栓形成的結(jié)果。尼莫地平作為SAH后預(yù)防血管痙攣的推薦用藥,已被證明能影響SAH后的纖溶活性,這種作用可能與促進(jìn)大腦內(nèi)微小血凝塊的分解[15]有關(guān),這也是目前認(rèn)為其對DCI治療的另一機(jī)制。
4 皮質(zhì)擴(kuò)散性抑制
皮質(zhì)擴(kuò)散性抑制(Cortical Spreading Depolarization,CSD)是指從起病區(qū)域向四周傳播的緩慢的去極化波,并伴隨有大腦皮層電活動的擴(kuò)散性抑制、代謝紊亂、以及細(xì)胞內(nèi)外離子穩(wěn)態(tài)的顯著破壞[18-19]。這種破壞可能導(dǎo)致滲透失衡,引起神經(jīng)元腫脹和大量神經(jīng)遞質(zhì)釋放。細(xì)胞內(nèi)外離子濃度梯度的轉(zhuǎn)變致使相鄰神經(jīng)元網(wǎng)絡(luò)之間的功能障礙和腦電靜息,這種損害作用將會持續(xù)至擴(kuò)散性抑制停止。
CSD與微血管系統(tǒng)的改變有關(guān),這種改變包括微血管收縮和逆轉(zhuǎn)的神經(jīng)血管偶聯(lián)[18]。CSD后的微血管收縮有可能經(jīng)由低灌注的發(fā)展而來并進(jìn)一步加重腦損傷。這表明CSD與DCI的發(fā)生有所關(guān)聯(lián)[20],大多數(shù)SAH病人存在CSD,并且可以在沒有腦血管痙攣的情況下發(fā)生[21]。CSD很可能在SAH后的DCI的發(fā)生中發(fā)揮作用,但它是一個關(guān)鍵機(jī)制還是其他機(jī)制的伴隨作用目前尚不確定。目前針對動物實驗的研究,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一些關(guān)于SAH后CSD潛在機(jī)制的假說。動脈瘤破裂后,蛛網(wǎng)膜下腔的葡萄糖、一氧化氮和氧氣水平降低,鉀和血紅蛋白水平升高[19]。這些改變可以導(dǎo)致神經(jīng)元去極化,釋放高濃度的神經(jīng)遞質(zhì),進(jìn)一步改變離子穩(wěn)態(tài)從而引起CSD產(chǎn)生。此外,CSD與癲癎之間似乎存在某種聯(lián)系,因為這兩者都會在SAH后出現(xiàn),并且具有某些相似的特征,比如代謝需求增加、神經(jīng)血管偶聯(lián)逆轉(zhuǎn)和血腦屏障功能障礙[22]。鑒于SAH后CSD的高發(fā)生率及其預(yù)測DCI發(fā)展的能力,可以將CSD作為靶點(diǎn)來預(yù)防DCI。目前這些實驗大多正在動物模型中進(jìn)行,有望未來在SAH臨床治療中得到應(yīng)用。
5 炎性反應(yīng)
以往認(rèn)為中樞神經(jīng)系統(tǒng)在免疫上擁有特權(quán),但是近年來許多研究都對這一觀點(diǎn)提出質(zhì)疑[23-24]。動脈瘤破裂后,炎性反應(yīng)隨之發(fā)生,一些研究已將其與DCI聯(lián)系起來[25]。臨床研究主要集中于對腦脊液和血漿標(biāo)志物的識別,以預(yù)測DCI的發(fā)生。這些研究著眼于外周血中的炎癥標(biāo)志物,如白細(xì)胞介素-6、C反應(yīng)蛋白、白細(xì)胞介素-1受體以及血液學(xué)指標(biāo)(如白細(xì)胞增多和貧血)。也有人提出使用白細(xì)胞計數(shù)、中性粒細(xì)胞/淋巴細(xì)胞比值、血小板/淋巴細(xì)胞比值或其他生物標(biāo)志物來估計DCI發(fā)生風(fēng)險[26-28],但這些指標(biāo)是否可行還需要更大規(guī)模和更高質(zhì)量的研究來驗證。
SAH后中樞神經(jīng)系統(tǒng)內(nèi)的炎性反應(yīng)起始于動脈瘤破裂,血液進(jìn)入蛛網(wǎng)膜下腔并釋放信號,從而促進(jìn)炎性反應(yīng)。紅細(xì)胞代謝產(chǎn)物釋放入蛛網(wǎng)膜下腔,可作為被固有免疫細(xì)胞識別的損傷相關(guān)分子模式。血紅素可以被血紅素氧合酶代謝,并產(chǎn)生具備生物活性和促炎作用的化合物。為了防止這種有害的作用,結(jié)合珠蛋白可以結(jié)合血紅蛋白并阻止其代謝。之后血紅素和其他紅細(xì)胞降解產(chǎn)物可以與固有免疫細(xì)胞上的模式識別受體結(jié)合,特別是小膠質(zhì)細(xì)胞。這樣的模式識別其中一種受體是Toll樣受體4,它與DCI的發(fā)生和不良結(jié)局相關(guān)。還有一種在DCI和血管痙攣中發(fā)揮作用的損傷相關(guān)分子模式是高遷移率族蛋白B1[29],它在SAH后由壞死細(xì)胞和激活的免疫細(xì)胞釋放。這些分子在激活大腦的炎性反應(yīng)中起著重要作用。
對SAH后小膠質(zhì)細(xì)胞作用的研究發(fā)現(xiàn),小膠質(zhì)細(xì)胞在DCI的發(fā)生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SAH后小膠質(zhì)細(xì)胞作為腦內(nèi)主要炎癥細(xì)胞發(fā)揮著重要作用,這些細(xì)胞的耗損可以削減神經(jīng)元細(xì)胞的死亡。與外周巨噬細(xì)胞近似,小膠質(zhì)細(xì)胞可以分化為促炎或抗炎表型。一些研究發(fā)現(xiàn),中性粒細(xì)胞和巨噬細(xì)胞在SAH后進(jìn)入蛛網(wǎng)膜下腔,并可進(jìn)一步促進(jìn)炎性反應(yīng)[30]。其他研究表明,中性粒細(xì)胞不會直接侵入蛛網(wǎng)膜下腔,而是通過分泌細(xì)胞因子影響中樞神經(jīng)系統(tǒng)的免疫應(yīng)答[31]。另外,SAH后,腦膜淋巴系統(tǒng)和類淋巴系統(tǒng)也發(fā)生改變,對腦脊液的流動和廢物的清除產(chǎn)生影響,這些系統(tǒng)的損傷可能也會引起DCI的發(fā)生。事實上,中性粒細(xì)胞的降低會減少組織炎癥和血管痙攣的發(fā)生。然而,各種免疫細(xì)胞之間的相互作用十分復(fù)雜,尤其是幾種主要的免疫細(xì)胞及其產(chǎn)生的細(xì)胞因子,他們之間的相互作用仍需進(jìn)一步研究。
6 結(jié)語
DCI的存在降低了aSAH的治療效果。長期以來,腦血管痙攣被認(rèn)為是DCI發(fā)生的主要機(jī)制,然而最近的研究發(fā)現(xiàn)還有其他機(jī)制,主要包括微循環(huán)障礙、微血栓形成、CSD和炎性反應(yīng)。各種機(jī)制之間可能是互相聯(lián)系,而非各自獨(dú)立的關(guān)系。對DCI發(fā)生機(jī)制的研究,將有助于發(fā)現(xiàn)防治DCI的新的靶點(diǎn),降低aSAH病人并發(fā)癥的發(fā)生率,改善aSAH病人的預(yù)后和生活質(zhì)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