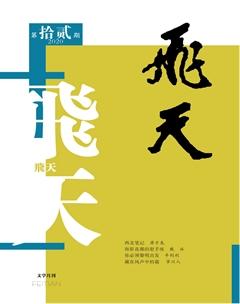陌上花開緩緩歸
馮麗君
到處都是花兒,鮮亮的金盞菊、或白或粉的格桑花、嬌艷的天竺葵、皎潔的百合,還有密匝匝的紫藤,一朵壓著一朵,一穗挨著一穗。謫仙人曾詩云,“紫藤掛云木,花蔓宜陽春。密葉隱歌鳥,香風留美人。”小小的紫色花羽,滿載希望的蜜露,伸展了翼,在夢幻的花幕上輕舞。
被滿眼的花迷住,眼睛已經不夠用了,迫不及待地拍下一朵又一朵,一樹又一樹。道路蜿蜒,芳草鮮美,落英繽紛,花兒一路陪伴,走走停停,在她們無聲的邀約下,腳步輕快,笑語飛揚,而忘路之遠近。是誰說的,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曲折地接近自己的目標,一切筆直都是騙人的。果然,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活潑爽朗的孔雀草在這里舉行盛會,花田一片接著一片,間或有人行棧道穿越其中,亭臺木閣坐落其間。如果不是耳邊時有牛哞聲,幾乎忘了身處鄉村。
平頭溝村終于到了。這是一次始于偶然的相遇,一路上馬主席心心念念一定要帶大家來看一看的地方。在一次有關崇信未來發展的論壇上,他聽到有人提起崇信的平頭溝把窯洞改造為養牛場,帶著對窯洞的感情,對舊物利用的欣喜,欣然前往平頭溝。在那里,他遇見了梁老爺子。此次相遇后不久,就有了《平頭溝的朝氣》這篇文章。現在,我們也與平頭溝相遇了。
“有人嗎?”我們拍著梁老爺子的院門,一頭頭牛在用木柵欄圍起的平坦開闊的空地上徜徉,院子中間還有一個倒置的藍色“L”型掛鉤,固定著圓筒形黃色大毛刷。這是做什么的呢?我按捺住好奇,隔著不高的柵欄門繼續往里看。庭院右側是三間磚瓦房,門上掛著布簾。
“那不就是窯洞嗎?”旁邊有人一指,“看,里面還有牛呢。”
“有人嗎?”院落很安靜,牛兒們撲閃著大眼睛也在觀察著我們,仍是一臉平靜。瓦房的門開了,一位身材頎長挺拔的老爺子走了出來。他頭戴寬檐草帽,鼻梁上架著石頭眼鏡,下頜留一把花白的山羊胡,手拿一柄旱煙鍋。
“梁老爺子,我來看你了。”馬主席笑著打招呼,我們跟著問好。梁老爺子把我們迎進院門,大家開始拉家常,從年齡到家庭,從日常生活到經濟收入。我也問出了我的好奇。
“你問這個啊,就是給牛洗澡,蹭癢癢的。”
“今年81歲,都四代同堂了。孩子們都在外面打工,上學。兒子平常也回來,過年的時候兒孫們就都回來了。”
“孫子說,爺,我給你數錢,數著數著就把錢這么一塞,順到自己口袋里了。重孫子護我吶,說是太爺的錢,不許拿。”老人家說著與兒孫相處的趣事,連皺紋里都盛滿了蜜酒。
“養的都是基礎母牛,國家給買的牛。每個月還給我給著600元,都叫牛吃了,牛能吃的很。窯洞也給加固了,窯洞都養牛了,牛的生活環境好了,心情也好了,長得也好。”
“不是說遠抓蘋果近抓牛,當年脫貧靠勞務么。今年我已賣了兩頭牛,這三年掙了近十五萬元了。”老爺子的胡子都抖擻著精神氣。“老爺子,您比我能掙啊,您太厲害了!”“你們和我不一樣,你們是給國家打工,給人民造福呢。”“老爺子,您太會說話啦。”大家哈哈大笑。“我每天聽廣播,看《甘肅日報》哩。”真是一位睿智風趣的老人,很難想象他81年都是在農村度過的。
“運動褲、運動鞋都是兒子孫子給的,這件白馬褂是老婆走的前一年做的,已經穿了四年了”。老人用平緩的語調和我們聊著往事。
“一直抽旱煙。煙袋啊,也是老婆子做的,一直用。”我看到墨綠色的煙袋正反面分別繡著花兒,一朵像桃花,一朵像石榴。
走出梁老爺子家門,陽光干凈,清風和暢。道路旁孔雀花田里幾位老人在長椅上曬著太陽,憶著過去,說著現在,想著明天。
告別平頭溝村,我們離馬峽鎮越來越近了。
馬峽因村東石峽形似張開的馬嘴,故名馬嘴峽,簡稱馬峽。為古代關中通往隴西的要道,歷史上曾是屯兵、儲糧、養馬、造車之地。此地中草藥種植歷史悠久,素有“千年藥鄉”的美譽和“隴東藥庫”之稱。因盛產的大黃色澤好、氣味濃、藥力佳而被譽為"大黃之鄉"。所產獨活以其根條粗肥,肉質好,斷面茬白、無柴質、氣味芳香濃郁,品質好,順利通過國家地理標志認證。
川穹、黃芪、黨參、板藍根……資料上寫著本地境內野生藥材達263種,隔著車窗看漫山野花,月光藍、珍珠白、丁香紫、薄荷綠……每一朵花心是否都有一顆懸壺濟世的仁心,每條根系是否都訴說著對生命至誠的禮贊?我不得而知。
馬峽順義中藥材種植農民專業合作社到了。這哪里是農民專業合作社?說它是現代企業也不為過。除了靠近大門的場院,一眼看去,綠草如茵,一眼看不到頭。遠處,有數十位頭戴草帽、紗巾勞作的身影散入其中,星星點點。
“大家看到的這一片都是獨活。”給大家做介紹的是一位魁梧大漢,我得仰著頭看他。陽光在他的臉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記,古銅中透著微紅。我注意到了他的手,骨節粗大,皮膚似被粗砂礫打磨過。
“這個時節得除草,都是附近的農戶,按天計費,滿工還有200元獎勵哩,一個月下來,滿工的就有2600元收入。有請假的、還有下雨不能做活,差不多一個月就是2000到2400。”
“還有土地流轉的收入,加入合作社的,還有分紅呢。干活的收入是另算的。”
我們到晾曬風干區、交易大棚,一個個看過來,不斷的刷新著我對農村合作社的認知,真是大手筆啊。
“以前我們都是散戶,各種各的。化肥也不會用,多了少了都不行,少了長不好,多了賣的時候又說重金屬超標,不要了,大家又不懂這個。過去大家都是房前屋后攤開一曬,不操心,要么藥材被霜凍了,要么就是發霉了,烏龜殼上找毛——白費勁。”
“有幾年藥材收的貴,大家一看,就啥賣的貴種啥。種的多了,過兩年這個價格又跌了,那個的價格又起來了,哪頭都趕不上。再加上不合人家標準的,壞了的,都賤賣了,掙不了錢不說,還白貼錢。”說起過去,他搖搖頭。
“現在?現在是財神爺摸腦殼——好事臨頭,大不一樣了。這個合作社就是劉建華帶頭弄的,他收了20多年藥材了,販運、加工、銷售都熟得很,是個老藥商,還認識很多藥材技術人員。他牽頭,郭向明把他們深溝村的向陽中藥材專業合作社也帶過來了。蒼溝村的龔跟錄,七零年的,就我是地地道道的農民,學著種,種著學,用了四年時間也把自己變成大黃種植示范戶了。”說著合作社里這一個個的能人,大漢的聲音都洪亮許多。
“大家一看,龔跟錄能成,跟著學,努把力,咱也能成。現在是藥材技術有人教,藥材銷售不發愁,藥材種植有甜頭。后面還在建的有中藥材飲片加工車間、質量檢測中心。我們還有三期工程,冷鏈儲藏庫、物資配送中心都是要建設投入使用的。對,政府扶持,社企聯建,用個時髦的詞說,我們也要走向產業化啦。”大家都為他語氣里的豪情逗笑了。
“等再過三年,大家再來看看,我們真就成隴東藥材重鎮了。”一定來,一定再來!大家和他握著手,贊嘆他講解的精彩,對大家的真誠,對未來的信心。剛才爽直的漢子,倒有些羞意了,膚色更紅了。
臨上車前,我注意到廠區縱橫的綠化帶里竟沒有波斯菊、百日草、千日紅等常見綠化花卉的身影,倒是一根根光滑無毛、根莖粗壯、葉片寬大的植株郁郁芊芊,別有生機。稀疏處有幾株長有鋸齒形葉片,花白色,乍看很像滿天星,花瓣細密團簇的植物。“這種的什么花啊?”我問道。“那是大黃,有幾朵花的是獨活。”大家全笑起來了,原來不識廬山真面目啊!
她們生長在這里,茂盛得自在坦蕩。識也罷,不識也罷,她們不言不語,卻自有遼闊的心。她們是一片朦朧的寂寥與溫馨,是一片成熟的朝氣與希望。心靈與鄉野就是她們的領地。
一路向南。
天水,天河之水。
沿途花影重重,風光無限。到達目的地了,下車抬眼遠望,還來不及收拾旅途的勞頓,腦海中已浮現這樣幾句詞:“碧山錦樹明秋霽。路轉陡、疑無地。忽有人家臨曲水。竹籬茅舍,酒旗沙岸,一簇成村市。”這就是甘江村了。
到了村口,只見“甘江村休閑觀光兩日游”的大型廣告,影視攝影基地、溫泉水月、篝火晚會、滋補柴火雞、山野民宿……免費接送,價格不貴,一個人198元。圖文并茂,很是誘人,如果時間允許,我倒是真想在這鄉野林間體會“明月別枝驚鵲,清風半夜鳴蟬”的清雅,感受“笙歌散后酒微醒,深院月明人靜”的寂寥。
這里林草豐美,家家門前院內都是秀雅的園林,香花滿徑,柴門初開。大家四散開來,自由漫步。家家布局不同,或恬或雅、或野或秀,大樸若拙、大簡若繁,你總能遇到最合自己心意的院落,每一家都有主人匠心獨運的設計和精妙絕倫的搭配。這里早已不是我遙遠記憶里灰矮土墻、斑駁木門、昏暗破舊、泥濘小路構建的鄉村世界了。在與村支書的交流中,他最引以為傲的就是甘江村里家家戶戶庭院屋舍的設計,在最初的時候就提出了審美的要求,盡量遠離艷俗,遠離矯情。
一行人走走停停,不用去尋找詩和遠方了,這里就是遠方,這里俯首皆是詩。人靜,人靜。風動亭亭花影。
“手抬高一點,腰再軟一點。”是誰的笑語打破了這片寧靜。原來已走到了花圃種植基地,這里也是影視攝影基地,幾對新人在晨光中拍照。綠草茸茸,女子身姿曼妙,著西式婚紗或中式禮服,或晶瑩如雪、或嬌艷如桃,或鮮艷如火,或飄逸如云,“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男兒風華正茂,清新俊逸。配合著攝影師,笑著鬧著,留下陽光燦爛的故事。“臉慢笑盈盈,相看無限情”,眼睛里都是瑰麗的光芒。遍綠野,嬉游欣戀,不負青春。
沿著十里花廬徜徉,小徑彎彎,花田起伏,秋千伴景,蕩椅徐搖。綠塘搖滟,蓮蕊有香,潭水盈盈,清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不禁就想起了“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此情此景讓人早已不辨這到底是“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響”的江南,還是“六出飛花入戶時,坐看青竹變瓊枝”的北境。我們隊伍中最淡定的男士也放下了矜持。“來、來,幫我在這拍幾張照片。”選好姿勢,準備開拍時,還不忘叮嚀:“一定要拍好看些。”
“今天沒帶孫子啊?”村長和幾位忙著披紗巾的阿姨打招呼,旁邊還有一位大叔正忙著固定手機支架。“我家的上幼兒園了”。“今天姥姥領著呢,兩家換著帶”。原來是本村的村民。擦身而過時,我才注意到阿姨們是在用手機拍抖音小視頻呢。待走過去了,還能聽見大叔說:“把絲巾揚起來好看。準備好就開拍了。”看來大叔不僅搞服務,還兼職參謀。走遠一些了,我回過頭,阿姨們已經拿著扇子開始起舞了。真好,讓人不禁感慨:但是夕陽無限好,何須惆悵近黃昏。
花燃山色里,柳臥水聲中。走了一路,花兒也笑了一路。這里,每一棵草,每一株花都把自己深深扎進樸素的鄉土中,真實地展現著對生命的真誠,凝聚著鄉村鮮活全新的韻味。“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在這“本土本真本味”中,我甚至能清楚地看見。當我不得不離開它,我會怎樣想念它,我會怎樣想念它并且夢見它。
緩緩歸,緩緩歸。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