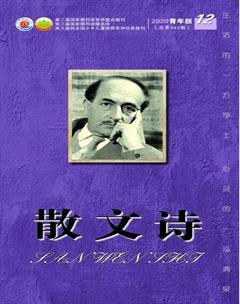牛
沈凡
關于以往,我至今戀戀不忘的是,鄉村耕耘的一種古老、久遠的情懷。
童年的時候,老家那里也沒有幾家養著牛,后來,我聽奶奶說,在我出生之前,我們家是養牛的。她說,那時她經常帶著我哥哥在鄉間小道上放牛,我的哥哥就坐在牛背上,脖子上掛著一塊餅,邊走邊吃,像極了唐詩里的小牧童。我一直對這個場景念念不忘,也想坐在寬大厚實的牛背上,掛著一塊餅,餓了就吃一點,牛不時的哞哞聲粗糲、低沉而溫柔,穿透四季的曠野。在這個牛背上,遠離了大地,也遠離天空,那是童年的一種燦爛和體驗,是我未曾遭逢的禮遇。
我對這些牛充滿著深深的真摯之情,在這片亙古的黃土地上,它們為我們犁開了太多文明的溝壑,為我們抵御了太多的飄搖和繁霜。每一只成年的水牛身上都帶著低沉、古老的意味,在村莊間緩慢移動,像是先天的悲劇英雄,而當它們還是小牛犢的時候,又是那么的靈動歡快,充滿著年輕的靈氣。我知道,在它們長大、變老的過程中,一定是肩負著一種與人類息息相關的宿命,所以,一切才如此沉重。每次見到那些黝黑粗壯的水牛,看見它們晶瑩、深沉、流動著水光的眼神和滿是干涸污泥的牛角與四蹄;看見它們在廢黃河的高堤上緩慢、沉重地移動,偶爾甩動尾巴;看見它們在夏日的傍晚,靜靜地從池塘里起身、上岸,攪起河床的污泥……我都會涌起一種深沉的情感,這群生靈不應該承擔人類千年耕種的痛苦和執著。
我不知道從何時起,它們開始了這樣的宿命。文化考古學發現,史前時代的家畜養殖業中,牛的馴化要比馬的馴化早得多,在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遺址中,都發現有許多牛骨,可見新石器時代我國養牛已比較普遍。在那些遙遠的歲月,被馴化的牛不僅作為一種食物來充饑,它們在遠古先民蒙昧、原始的心理中還有著神秘復雜的巫教意味和祭祀情感。
牛是古人圖騰崇拜的主要對象之一。《中國原始社會史》中寫到“大小涼山彝族在祭祖和送祖先靈牌時,要組織男性青年背牦牛尾巴,邊歌邊舞,敘述人類的起源,祖先的遷徙,名曰牦牛尾巴舞。這可能是模仿圖騰的舞蹈形式,反映了對圖騰的信仰和頌揚”。《孝經·援神契》中記載,“神農氏……宏身而牛頭,龍顏而大唇,懷成鈴,戴玉理。”又據《史記·五帝本紀》記載,炎帝是“人身牛首”,這位古老偉大的先祖,被世代的人們以人身牛首的神秘形象口耳相傳,最終記載在了歷史的文字中。我們不難看出,作為被馴化的最先一批家畜,牛在原始文化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而商人以玄鳥為圖騰,周人以巨人足跡為圖騰,他們禮器的紋飾圖案卻不是自己的圖騰而是饕餮紋,這未必就能夠說明那饕餮紋比本族的圖騰更具有某種意義或神力,但至少可以看出其具有著另一番神圣的意味。而據李澤厚先生的研究,他基本上認為饕餮紋是一種抽象了的牛頭圖案,是遠古民族圖騰崇拜的殘留,他在《美的歷程》中總結道,“以饕餮為代表的青銅器紋飾具有肯定自身、保護社會‘協上下、‘承天休的禎祥意義。”
與圖騰崇拜并行不悖、相輔相成的是祭祀文化。“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商周時代的文化核心之一就是祭祀文化,而周人設祭,以牛為犧牲,稱為太牢,屬于最高等級的祭品。《詩經·周頌·我將》敘述了周武王起兵討伐殷商前的祭祀活動,“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禮記·曲禮下》也說:“凡祭……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在這種神秘幽遠的祭祀文化、心理之下,至少遠在周代就有了專門為國家養牛的人和單獨開辟的牧場,《周禮·地官》中就有“牛人”“牛田”的記載,“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代國之政令”,“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
史前時代,那一系列的原始活動讓牛具備了神秘復雜的文化內涵,在先民的心中具有無與倫比的神性。而在春秋戰國時期,牛開始代替人力耕田,其功能由肉用、祭祀轉為拉車耕地,牛身上所具備的神性慢慢變成了人間的煙火氣,它們從祭壇和圖騰走回大地,代替生產力再次解放的古人默默耕耘。每次想到這里,我都好像看到一幅畫卷:在蔚藍的天空下,群山環繞,一頭黝黑粗壯的水牛和一個老人在大地上一步一停地犁地,然后沿著那條鄉間小道,緩慢、蒼茫地向我走來,天地開合,萬物久遠……這一走,飄搖壯烈的遠古圖騰變成了活生生的血肉。
從第一批野牛被馴化起,這一類群此后的宿命就被徹底決定下來了,經由原始的圖騰與祭祀文化,它們最終慢慢變成了這片大地上每一個村莊古老、緩慢的耕耘情懷,不管是那高高在上的神圣祭品,還是炊煙繚繞下那群拉著鐵犁、承受牛鞭的普通生靈,它們都替人類安放了許多進化過程中的龐大、艱澀。
我想,許多年以后,等我日漸蒼老不再年輕,我就回到故鄉,待在故鄉的村莊,種幾畝地,養一頭牛,偶爾牽著它走過秋日的田埂和路口,把許久不用的鐵犁放進糧倉深處。希望那時還會有幾個老朋友,在些許時日里能走過遙遠的路程來看我,我們一同撫摸著牛亮麗柔順的毛發,談論它的健壯。如果還有精力和興致,我會騎在牛背上,西出函谷,拜訪一些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