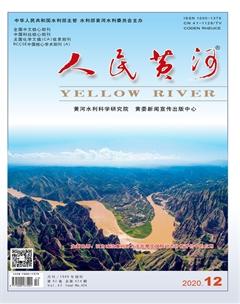從《黃河史話》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黃河航運
張嵩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政權更迭最為頻繁的時期,經歷了魏、西晉、東晉以及南北朝。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黃河航運在北方水上交通中占據著極為重要的地位,無論是黃河的上游部分河段,還是黃河中下游河段,都一定程度有著航運的開發利用。黃河流域作為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經濟的中心,歷史上黃河航運的開發利用意義重大。由辛德勇創作的《黃河史話》一書以生動形象的語言,系統描述了中華民族祖先認識、開發利用黃河的歷史過程以及黃河河道的變遷,并闡述了黃河開發對中國歷史發展的重要影響。
《黃河史話》一書中提到,魏晉南北朝時期黃河中下游的水上交通較為發達,具備了良好的航運開發條件。在這一歷史發展階段,黃河中下游地區的自然生態環境保護較好。在東漢末年,曹操為了強化黃河與鴻溝水系的溝通聯系,開發了貫通南北五大水系的航運系統。在北方政權穩固、曹魏建國之后,多次開發利用黃河航運,具體包括整修千金渠、疏通洛河水域、整治三門峽與峽谷棧道、治理白溝與修建利漕渠等。這些圍繞黃河以北的航運開發維護措施促使黃河與海河水系之間的聯通變得更加順暢,極大方便了各地的航運交通運輸。曹魏時期擁有一大批優秀的治水專家,像鄧艾主張黃河航運要從北向南持續開拓發展,要積極修建溝渠,保障黃河與淮河之間的水運暢通;而陳勰則在曹操任命其擔任都水使者職位時,大力修建、維護千金渠,以此推動黃河與洛河漕運聯系,充分保障黃河航運的重要地位。
西晉時期加大了對黃河航運的維護力度。首先是對黃河上游航運的深入開發利用,晉尚書刁協之曾孫刁雍利用薄骨律至沃野間的黃河河道運輸軍糧,得到了朝廷的高度認可。北魏孝文帝也極力倡導開發黃河航運。雖然說這一時期黃河航道變得較為險峻,發展水運有著較大的危險性,但是孝文帝仍然挺身而出,要在黃河上行船督察,這種君主沖在前線的行為對推動中華民族黃河航運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北魏孝文帝針對黃河航運的開發,科學制定了詳細的規劃整治內容。公元497年,孝文帝來到長安,五月 “己丑, 車駕東旋, 泛渭入河”(《高祖紀下》)。北魏孝文帝經三門之險, 一路去探索連接關中地區與關東地區的黃河航道。雖然說最終以黃河為中心的航運交通美好藍圖未能夠真正在北魏孝文帝手中有效實現,但也引起了后續統治者的高度關注和認可,并為接下來的黃河航運發展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黃河作為溝通東西的重要樞紐,潼關以下河段的航運開發利用是極為頻繁的。三門峽及其以東峽谷河段是這一段航道上的瓶頸,一定程度阻礙了黃河航運的順利開展。就如《水經注》記載的一樣:“自砥柱以下, 五戶已上 ,其間百二十里,河水竦石杰出……其山雖辟, 尚更湍流,激石云洄,澴波怒溢,合有十九灘。”為了有效降低黃河三門峽及其以東峽谷河段的航運風險,當時開展了以下幾方面工作:第一,漢武帝遣監運大中大夫趙國、都匠中郎將河東樂世,帶領五千兵士去整治河灘,事見《五戶祠銘》。這一階段修鑿過程中留下了大量的石刻題記,我們可以從中尋找到當時人們修建整治黃河河道的相關證據。第二,北魏時期的河東太守番系提出過要在其所轄地區進行開發修建水渠,以此來降低關東糧食西運途中經 “砥柱之險,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的航運風險,然而最終還是不了了之。在這之后,還有人提出需要進行開鑿褒斜道,即“山東從沔無限, 便于砥柱之漕”,但是也沒有獲得成功。第三,為了促使洛陽與長安地區之間漕運之船能夠有效避開黃河三門峽及其以東峽谷河段水路航運的艱險,晉武帝提出要開辟新航道,也就是后面所設想的在現代陜縣南山地區選擇谷底開鑿渠道,然后將黃河的水引出來,經過南山,最終流入到洛河支流,這樣一來就能夠實現黃河與洛河的水運相互聯通。然而,根據《晉書》的記載,我們只能夠知道該設想的開河地點,卻難以準確考察了解到挖掘河渠的具體走向,最終是否完全順利完工也是一個謎。
伴隨著時間的不斷推移,全國政治經濟中心開始移出關中地區,雖然說北方政權仍然在決議實施對黃河三門峽以東峽谷河道的修建治理,但是該區間的航運開發利用不再是國家根本所在,朝廷更加關注對洛陽以東的洛河、黃河航道以及黃淮間水道的有效連接,朝廷派遣多人開發疏通這些水域,黃河中下游地區的水運開發占據了更為重要的地位,而黃河下游開發利用最為頻繁的就是漕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