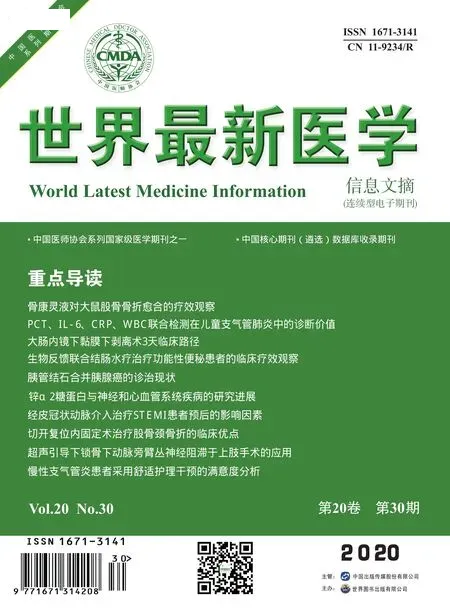劉鐵軍教授論治慢性非萎縮性胃炎驗案
韓佩珊,宮嘉蓮,楊新月,呂丹,劉鐵軍
(1 長春中醫(yī)藥大學,吉林 長春;2 長春中醫(yī)藥大學附屬醫(yī)院,吉林 長春)
0 引言
導師劉鐵軍教授,行醫(yī)40 余載,雖已年逾花甲,仍然堅持每周6-7 次門診,一直從事肝脾胃病的臨床診療,通讀歷代名醫(yī)經(jīng)典背誦經(jīng)方,年診治患者近2 萬人次,經(jīng)驗豐富,效如桴鼓[1,2]。三因制宜是祖國醫(yī)學的基本理論之一,通過因時、因地、因人制宜的法則,根據(jù)氣候、地域、環(huán)境、職業(yè)、體質等差異,作為立法處方的重要依據(jù)[3]。劉老認為在疾病診治過程中,要把握病本,靈活制宜。
筆者有幸跟師學習3 年,收獲頗多,現(xiàn)整理劉老經(jīng)驗如下,以饗同道。
1 因時制宜
因時制宜主要是結合氣候變化特點來選方用藥。如《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中記載“冬傷于寒,春必病溫,春傷于風,夏生饗泄;夏傷于暑,秋必痎瘧;秋傷于濕,冬生咳嗽”,“春夏養(yǎng)陽,秋冬養(yǎng)陰”便提出了時氣致病的理論,根據(jù)傳統(tǒng)的天人合一理念,人體臟腑氣血也受時令及六淫影響而有盛衰變化。生理情況下人與自然處于動態(tài)平衡之中,消長相應,收藏相和,病理情況下應依據(jù)人體的狀態(tài)結合時氣之變動。
人作為自然界的一員,自然也要經(jīng)歷四季更迭,順四時之氣而動方能合于道。無論是人或證都要順應四季交替變化,劉鐵軍教授提出在辨證論治基礎上,用藥可參考春選麻黃,夏用石膏,秋添參冬,冬藏附子。其選方用藥旨在于響應四時變化之勢,未病先防,已病防變。春季為陰中之陽,屬于陰向陽轉變的過渡階段,如果此時患病,多可選用麻黃等辛溫解表藥,以開肺瀉邪,助陽氣得復。夏季為一年中陽氣最盛之時,病患易在患病的同時產生明顯的實熱之癥,故多選用石膏、滑石、寒水石等大寒之品以抗衡熱邪。秋傷于燥,多于肺相應,辨治多加入潤燥不可或缺的沙參、麥冬。《通俗傷寒論》記載“秋燥一證,先傷肺津,次傷胃液,終傷肝血腎陰”。冬日陰盛則寒,其陷于陰證者,多于用附子以回陽救逆。正如明·吳綬撰《傷寒蘊要》所云“附子,乃陰證要藥”。
案例:霍某,男,50 歲,2019 年11 月5 日初診,患者自述間斷性胃脘部隱痛4 年,近日外感風寒后上癥加重伴噯氣8d。現(xiàn)癥見:胃脘部隱痛,得溫則緩,噯氣,汗出濕冷,時有身癢,乏力,惡寒,手足涼,矢氣少,納眠可,小便正常,大便不成形,質黏,1-2 次/d。舌淡苔白,脈滑。自備胃鏡提示:慢性非萎縮性胃炎,Hp(+)。中醫(yī)辨證:胃脘痛病(胃陽虛弱,表衛(wèi)不固證);西醫(yī)診斷:慢性非萎縮性胃炎。處方:黃芪30g,桂枝15g,白芍10g,生姜10g,大棗20g,甘草15g,黨參15g,生白術20g,防風15g,附子10g。予處方5 劑,水煎取汁450ml,150ml 日2 次早晚飯后溫服。復診時患者胃脘部隱痛減輕,手足涼緩解,上方黃芪加至50g 繼服7 劑,胃脘部隱痛改善,乏力及手足涼減輕,余癥轉輕。
2 因地制宜
受地貌、風土、民俗、生活條件等因素影響,不同地域的人有不同的體質,因此在疾病防治過程中應注意相關因素的考量。如金元四大家結合地理環(huán)境及體質差異,形成了不同派別。如寒涼派的劉完素,認為北方之地四季分明,北方之人身體強壯腠理致密,在飲食上多食膏脂、嗜酒,日久趨于化熱,故推崇寒涼之法[4]。劉老認為,在地域上,東北地區(qū)雖說夏日炎炎,但寒冬凜冽,春秋乍暖還寒,故脾胃病多虛寒;在飲食習慣上,多食膏脂、蔥蒜、咸菜或腌制品、嗜煙酒、飲濃茶,日久易積痰化熱,臨床中多見脾胃病合并脂肪肝、高血壓的患者,正如古人云“魚生火,肉生痰,蘿卜白菜保平安”,全面調控飲食習慣有利于正氣驅邪。
在脾胃病論治中,針對脾胃虛寒者善用溫中之法以顧護中州,在使用寒涼藥物之時也注意不過偏寒熱,注重配伍。在患者咨詢服藥期間飲食指導時,劉老編了一些通俗易懂的順口溜“大便黏,少吃鹽,大便臭,少吃肉,脾胃滿,吃半碗”,他還會根據(jù)患者個體情況,囑托低鹽清淡飲食、戒煙戒酒、少飲濃茶、不可食用蔥、蒜、辣椒、羊肉等辛散之物,從而因地辨體施治。
3 因人制宜
《時病論》中提及“體有陰、陽、壯、弱之殊”,患病本身就是正不勝邪的過程,而人體正氣系之性別、年齡、職業(yè)、起居、體質、情緒等多重因素綜合作用。對此劉老特意指出情緒對于脾胃病的影響。
在生物-心理-社會模式中[5],腦-腸軸指導下[6],結合當代人不斷增加的各方面壓力、生活的快節(jié)奏、作息不規(guī)律、飲食不節(jié)制,現(xiàn)代醫(yī)學提出了“胃心綜合征[7,8]”這一名詞。在祖國醫(yī)學理論中,此征體現(xiàn)了張景岳提出的“因郁致病,因病致郁”。劉老常教導我們“治病先知心,知心先治心,治心用心法,心靜病亦安”。情志失調是胃炎的一個重要誘因,情緒不佳,飲食不下的例子比比皆是。且大多數(shù)胃炎患者起初臨床癥狀不夠典型,多數(shù)內鏡下提示僅是慢性非萎縮性胃炎,但自覺癥狀較重,且隨著情緒失常而加重。情緒失常與脾胃功能失調相互影響,在本病治療中應注重心理干預。
案例:李某,女,62 歲,于2019 年9 月4 日至劉鐵軍教授工作室就診。自訴平素急躁易怒,于2017 年末結束乳腺癌化療療程后出現(xiàn)胃腸道不適,時常擔心乳腺癌病情反復或惡化而飲食難下,于當?shù)蒯t(yī)院行理化檢查無明顯實質性病變。既往乳腺癌病史6 年,慢性非萎縮性胃炎10 余年。現(xiàn)癥:胃脘部脹滿疼痛,時有烘熱汗出,頭暈目眩,嘔惡頻頻,胸悶氣促,不欲飲食,夜間多夢易驚醒,大便秘結,小便短赤。舌暗,苔黃,脈弦滑。中醫(yī)診斷:胃脘痛病(痰火擾心證);西醫(yī)診斷:慢性非萎縮性胃炎、乳腺癌。處方:柴胡15g,半夏10g,紫蘇子15g,桑白皮30g,大腹皮30g,青皮10g,赤芍20g,香附20g,桃仁25g,通草15g,陳皮15g,牡蠣20g,龍骨20g,茯苓20g,大黃3g,黨參10g,黃芩15g,桂枝15g,大棗10g,生姜10g,甘草20g。予處方5 劑,配合心理疏導,服藥后患者胃脹改善,嘔惡頻頻減輕。復診在原方中減半夏、紫蘇,將龍骨、牡蠣增至30g。三診患者自覺睡眠及情志有所改善,頭暈目眩、胸悶氣促緩解。故在原方的基礎上辨證加減治療2 個月,期間患者飲食及體重增加,精神狀態(tài)復常,余癥基本消失。
4 討論
三因制宜的診治原則體現(xiàn)了整體觀念、天人合一的傳統(tǒng)中醫(yī)的思想,反映出辨證論治的個體性和針對性,在臨床實踐中能夠綜合時、地、人全面分析,常能取得較好的臨床療效。結合當代社會背景,在脾胃病辨治中,進行藥物、飲食及心理等療法干預,靈活運用中醫(yī)三因制宜理論,更加切合當代醫(yī)療個體化治療的原則,對疾病的預防、治療、養(yǎng)生和保健都具有較強的臨床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