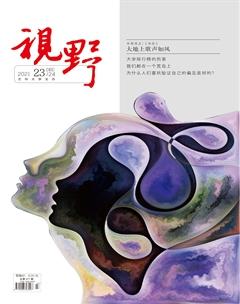《詩經》有什么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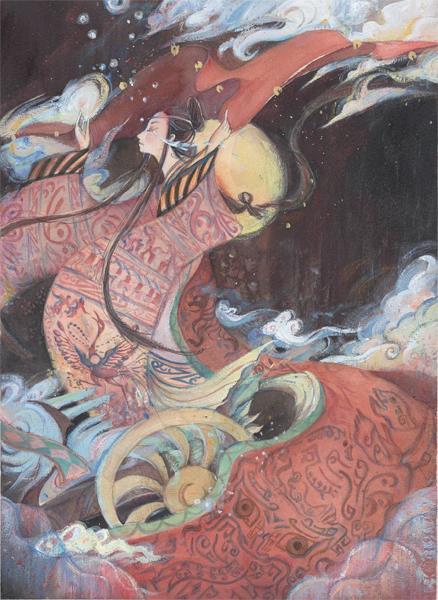
在世界歷史上,有一件絕可注意的事件,那就是距今兩千五百年左右的時候,地球上的四大古文明區(印度、中國、古希臘地區,還有包括了埃及和巴比倫的小亞細亞文明區),突然不約而同地都唱起歌來了。它們唱的歌和早先不同,其內容都是詩。這些詩有兩種形態,一種是史詩,一種是抒情詩。在印度和古希臘是以史詩為主;在小亞細亞一帶是抒情詩為主,我們現在還可以看到的《舊約》全書里面的“雅歌”,本身就是非常美妙的抒情詩,和中國的《詩經》很相似,特別是和《詩經》中的“風”很相似,可以看作是小亞細亞的“詩經”。我們中國的《詩經》主要是抒情詩形態,叫做“詩言志”,而不是“詩敘事”。雖然也有敘事詩,但不是《詩經》的主體,《詩經》的主要內容都是“言志”。言志者,“在心為志,發言為詩”。這個“志”是指內心的感動、感情,不能狹隘地理解為“志氣”“志向”。如果要翻譯出來的話,它相當于英文的will,也就是“意愿”的意思。所以中國古人說《詩經》是“情動于中而形于言”,是“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
如果你要問我“詩歌有什么用處”,我確實也說不清楚。從物質的角度來看,詩歌也許是沒有什么用。也許沒有詩,糧食還是會有的,鋼鐵也是會有的,肚皮還是會吃飽的,但就是沒有靈魂上的趣味。一個人是不是經過詩歌的陶冶,他在氣質上是絕對不同的。所謂氣質,似乎也很難說得清楚,但是你和一個人交談,不到三分鐘就一定能感覺出來的那個東西,就是他的氣質。這就是詩歌的用處。
詩歌最大的用處,就是使你自己快樂,包括兩種快樂:一是你自己寫出一首好詩,你會感到快樂;還有就是你讀到一首好詩的時候,也會感到快樂。而這種快樂是不可替代的。我最厭惡一種流行的比喻,是說什么“流沙河老師這幾天給我們講詩,送來了一道豐盛的晚宴”。天哪!那個晚宴算個什么嘛——它吃完了就全都排泄出去了!詩歌藝術不是什么“晚宴”,不可能讓你吃飽。詩歌這個東西,是所有自我娛樂活動中最高級的,它可以讓你進入一種不可替代的心境和感受之中。實際上,詩是對我們起潛移默化的作用。任何一首詩,都很難收到什么現場效果,不是說讀了哪一首詩,你的覺悟就提高了,突然就懂得了很多東西。詩是慢慢浸潤你,慢慢地改變你的靈魂,使你變得有趣味,變得高雅起來。詩歌的價值就在這里。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在農場搞體力勞動,有時挑的東西很重,一邊挑,一邊就在心中默讀一些詩歌(因為不敢讀出聲來,讀出來就是“封資修”,馬上就要挨批判),這樣可以減輕痛苦,其作用就相當于毒品一樣,只不過這種“毒品”不害人,也不害己。至于詩歌是不是有其他的什么偉大作用,什么革命要不要詩歌,這些問題都和詩歌無關。詩歌就是一種娛樂,一種高尚的自我娛樂,在自我娛樂的同時,也可以娛樂他人,這種娛樂不是什么其他的“亞文化”可以代替的。
我們中國,自古以來就非常重視“詩教”,孔夫子也好,孟夫子也好,他們在教學生的時候,都經常引用《詩經》上面的話,孔子說是“不學《詩》,無以言”。這個“言”,當然是指你說的話比較文雅,也比較有趣味,顯得有根據,能表現出你這個人有比較好的文化背景。孔子說詩歌有四種作用,叫“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興”就是起興,用來引發大家的某種興致;“觀”是觀察,就是你可以通過詩去了解種種社會現象;“群”是親和力,可以用詩來吸引、喚起那些有相同或者相似的思想感情的人;“怨”就是抱怨、發牢騷,通過詩來訴說自己的痛苦。無論“詩言志”也好,“不學《詩》,無以言”也好,“興、觀、群、怨”也好,都說明遠古的中國人,對詩歌的態度還是比較現實、比較功利主義的。到了隋唐以后,中國詩歌就超越了這種視角,更加注重詩歌的藝術性,注重意境,注重音韻之美和語言之美。
大家可能會提出一個問題:在秦始皇時代不是曾經焚書嗎,這些詩是怎么傳下來的呢?是的,《史記》上對秦始皇焚書這件事,記得清清楚楚——秦始皇采納了他的丞相李斯的建議:“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他第一個要燒的就是《詩》。你別看他是個暴君,他是很敏感的,就是不讓人們去讀詩,因為人讀了詩,趣味就會變雅,而秦始皇不要你的什么“雅”,他要的是炮灰,是為他賣命的戰士,所以他堅決要燒詩。你們看一下那些秦始皇兵馬俑,全部是那種“武棒槌”,一幫兇狠之徒!不知各位的觀感如何?反正我絕不認同。
為什么燒了之后還有詩呢?你們是不是在誹謗我們的秦始皇同志呢?不是的。當時的法律確實非常嚴厲,規定各家各戶都必須交出來,你要是不交,查出來就要被懲處,《史記·秦始皇本紀》里面寫得很清楚:“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但是有些東西,是殺不死、燒不掉的。而且,詩歌還有個最大的特點,就是能夠背誦,能夠吟唱,你把寫在竹簡上、木條上的燒了,它還可以記在腦袋里面。漢初甚至有一個叫“伏生”的老大爺,濟南人,九十多歲了,還可以用古音背誦《尚書》,漢朝政府就派人去請他教授,然后記錄下來。《詩》不僅可以背誦,也還有一些底稿被人們偷偷保留下來,秦朝亡了以后,到了漢代,政府一鼓勵獻書,各地都有人把自家原來悄悄藏起來的書拿出來了。最初被獻出來的《詩經》,就是齊、魯、韓三家偷偷收藏的版本,它們系統不同,互有出入,而且解釋也不同。后來出現得最晚的,是北海郡太守毛亨拿出來的版本,大概他是根據他的家族中流傳下來的版本整理的,這個版本就被稱為“毛詩”。后來大家開會鑒定,把四個版本的詩一比較,發現最好的版本就是“毛詩”,所以今天我們讀的《詩經》三百零五篇,固然都是孔夫子修訂過、刪改過的,但是這個版本是毛亨的版本,也就是我們后來通稱的“毛詩”。
《詩經》原來不叫“詩經”,在最早的時候,就叫“詩”。當我們說“詩言志”的時候,“詩”是專有所指的,也不一定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詩經》中的這些作品。因為這些詩最早有很多,經過多次編輯、刪減,才成為“詩三百”,就是現在流傳的“毛詩”三百零五篇,它是由孔夫子整理、潤色,編出來教授弟子的。到了漢代,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漢朝的官方利用“詩三百”來貫徹它自己的意識形態,就把它稱為“經”——經者,常也,意即永恒不變的道理——就是由官方把它定為講大道理的經典。“詩經”由此得名。從這個時候開始,漢儒——就是漢代的那些經師們,就支配了《詩經》的解釋權。漢代的這些經師,包括很有名的鄭玄,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缺點,就是在講詩的時候,不是首先把詩當作詩,而是當作一種意識形態,當作一種推行禮教的手段,給詩附加了很多解釋,而那些解釋不是這些詩本身的內容。這個現象一直延續到宋代。以朱熹為首的宋代儒生們,雖然對漢代的一些解釋做出了修正,但他們仍然沒有跳出利用詩歌來推行教化的這個框框,因此仍然忽略了詩的本意,尤其是朱熹,他把很多一般的愛情詩都認為是“淫亂之作”。所以,宋儒們的解釋很多也是不可取的。
(摘自四川文藝出版社《流沙河講<詩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