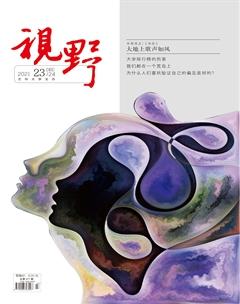修行的本質是什么?
蔣勛

尋找修行的凈土
這幾年很喜歡清邁,沒有曼谷那么熱鬧繁華。過去統治這一地區的蘭納王朝,似乎也不是大帝國,篤信南傳佛教,沒有太霸道向外征伐的野心。王國舊城方整,磚砌城墻外圍繞護城河,雖有幾處坍塌,大致都還完整。
城里許多古寺廟,許多枝葉茂密、覆蓋廣闊的大樹。一條不十分寬闊的賓河,波瀾不驚,也不洶涌,卻總在身邊,自北而南,悠悠流淌穿過城市。整個城市還保有中世紀農業手工時代的緩慢、專心、安分,有一種讓人慢下來的靜定悠閑。
初去清邁,也會對城市中心的夜市有興趣,看附近少數民族販賣各種手工藝品,銀飾的精致,木雕的渾厚粗樸。棉麻手工紡織,質料染色都有很好的觸感,剪裁成傳統衣褲,形式大方,穿著起來也非常舒適便利。瓦制陶缽、陶碗,有手拉胚的粗樸紋理,拿在手里厚實沉甸。
手工傳統在數百年間累積的經驗,像一種生態,其實常常是文化潛藏在土里的深根。土夠厚,根夠深,也才有文化的美學可言。近來大家常愛說文創產業,所謂創意,又常常是刨去厚土,斬伐了大樹的深根,替換一時短暫炫目淺根的花花草草,使文化愈來愈不長久。新失去了舊的滋養,根基不厚,或無根基,根土淺薄,創新常常只是作怪,當然也就無美學可言。
清邁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受到世界觀光的重視。當世界許多城市迅速沖向工業化惡質發展之時,這一古城,卻保留擁有著農業時代人與土地和諧相處的生態倫理,保留著多元民族豐厚的部落傳統手工技術產業,讓世界各地在城市惡質化的工業夢魘中焦慮不堪的游客、在生活里迷亂了方向的游客,來到清邁,可以坐下來,在一座寺廟庭院,或一棵大樹下,找到使自己清醒的凈土。
這幾年去清邁,常住一個月左右,不是為了觀光,而是遠離城市中心,住在城市郊外,讀書或誦經。
我住的地方在素貼山腳,鄰近清邁大學,附近是大片森林,也有清澈湖水,匯集山上巖石峽谷間沖下的雨水。冬天干季,涼爽舒適,即使夏天雨季,一陣暴雨過后,空氣中也彌漫著各種植物釋放出的香味。寺院鐘聲過后,各種蟲鳴升起,間雜著一兩聲悠長的夜梟叫聲。萬籟如此寂靜,使人可以安然入眠入夢。
或快或慢都是修行
好幾個冬季,在清邁度過,也固定住在無夢寺附近的公寓。每天清晨步行十分鐘左右,固定去寺廟誦經,有時也跟隨僧眾乞食的隊伍,一路走進商家林立的街道。
僧侶披絳黃色袈裟,偏袒右肩,赤足,手中持缽,從年長的僧侶,長幼依次排列。隊伍尾端是十歲左右的少年僧侶,還是兒童,常常睡眼惺忪,走得跌跌絆絆,引人發笑。
然而修行的路上,或許就是如此吧:有人走得穩定精進,有人走得猶疑彷徨,有人走得快,有人走得慢,然而,或遲或早,都在修行路上。一旁的譏諷嘲笑其實都無意義,反而耽誤了修行。
天光微明,修行的隊伍,如一條安靜的絳黃色河流,靜靜流入城市,一家一家乞食。商家知道僧人每天清晨乞食時間,都已拉開鐵卷門,準備好食物,準備布施。
僧人端正站立,雙手持缽,布施的人把食物——放進缽中,然后右膝著地,恭敬跪在僧人面前,聽僧人念誦一段經文。
這是清邁美麗的清晨,是僧人與商家共同的功課。這也是許多人熟悉的《金剛經》開頭的畫面啊!沒有想到,原始佛陀久遠以前行食的畫面,還日復一日可以在清邁的清晨看到。
我在此時,心中默想經文的句子: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祗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清邁像是舍衛城,祗陀王子大樹庇蔭的花園,給孤獨長老供養的道場,佛陀因此機緣,為一千兩百五十位學生上課,說了一部《金剛經》。
所有義理的開示演說之前,記錄者描述的只是一個如此安靜美麗的畫面:佛陀穿著袈裟,手中拿著一個碗,進入舍衛城,一家一家乞食。從一家一家得到布施,再回到原來的處所。吃飯,吃完飯,收好衣服,收好碗,洗腳,在樹林下鋪好座位。
沒有說任何道理,沒有任何教訓、開示,只是簡單樸素、實實在在、按部就班的生活。穿衣,乞食,吃飯,洗碗,洗腳,敷座……像每一個人每一天做好自己的家務瑣事。
日復一日的修行
一件簡單的事,做起來不難,可以日復一日,成為每一天例行的公事。每天做,卻不覺得厭倦、煩瑣;每一天做,都有新的領悟:每一天都歡喜去做:這會不會就是修行的本質?
像將近三千年前舍衛大城的乞食隊伍,像今日清邁僧眾依然維持的行乞,像商家依然信仰的清晨的布施,右膝著地,聆聽經文的虔誠,都是不難的事,但是每一天做,每一天歡喜地做,或許就是修行的難度吧。
現代文明是不是恰好缺少了這樣簡單而又可以一再重復的信仰?
傳統手工作坊分出經緯,認真織好一匹布帛,傳統農民耕作,播種、插秧、收割,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守著小小一個本分,不斷求精進,沒有妄想,因此可以專注。
清邁小食攤上老年的婦人認真把青木瓜切成細絲,認真在一個石缽里把花生仁搗碎成細粉,都不是難度高的事,但是如此專心,沒有旁騖,可能重復了三十年,因此那動作里就有使人贊嘆的安靜專一。
在清邁的時間,每天清晨到無夢寺散步,也變成例行的功課。我在寺廟繞塔誦經,僧人持竹掃帚清掃廊下落葉,或在樹下洗碗,也只是實實在在的生活。
無夢寺樹林間有一尊佛頭,仿佛低頭沉思,垂眉斂目,微笑宛然,卻又如此憂愁悲憫。四方信眾,常有人偶然來此徘徊,撿拾落花,供養在微笑佛像的四周。
我每一日清晨,來此靜坐,等候陽光照亮微笑。身軀失去了,手、足都不知流落何方,肉身殘毀如此,然而微笑仍然安靜篤定。這樣的雕刻若是在歐洲,大概會被謹慎修復,珍惜收藏,視為藝術珍品吧。
然而,我日日與此微笑相處,看信眾把花放在微笑前供養,看信眾離去時臉上都有一樣的微笑。陽光樹影娑婆,在一世一世的劫難毀壞中,有成,有住,當然也有壞、空。“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金剛經》的偈語清楚明白,成、住、壞、空,都在時間之中。
放到博物館的藝術,是妄想物質停止變化,是妄想把生命制作成標本吧。然而在東方,在佛教信仰里,美,不禁錮在博物館;美,像生命一樣,要在時間中經歷成住壞空。
或許,無夢寺殘毀的微笑,被陽光照亮,被雨水淋濕,青苔滋漫,蟲蟻寄生,落葉覆蓋,隨時間腐蝕風化,他也在參悟一種“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的漫長修行吧。
如果有一天此身不在了,希望還能留著這樣的微笑。
(阿紫摘自湖南美術出版社《舍得舍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