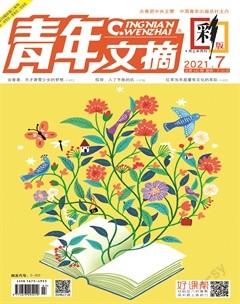娛樂偶像,為什么那么容易“塌房”
莫非
如果說掀起“愛豆”選秀熱潮的2018年是“偶像元年”,那2020年就應該稱之為“塌房元年”。“房子塌了”是飯圈術語,原意指粉絲所追的偶像明星有了戀情,后來擴展為偶像被曝光的各種負面新聞。據網友不完全統計,整個2020年各類負面新聞“纏身”的偶像超過了38位,其中七成以上是通過選秀出道的“愛豆”。在可預見的未來,娛樂圈“塌房”,將成為常態。
“以前的明星,都是一位一位地出道,現在的明星,都是一批一批地出道。”2020年年末,在某檔網絡綜藝節目上,一位嘉賓吐槽,“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成團出道的那一天,就是人生巔峰,從此就開始走下坡路。”這句話形象地總結了最近幾年偶像選秀類節目火爆、“愛豆”大批量出現,而其中的絕大部分人又會很快因為負面新聞或沒有作品而失去曝光率,迅速被悄無聲息地遺忘的現實。
2020年,幾乎每個月都有咖位不同的年輕偶像發生“塌房”事件,從戀愛曝光到負面新聞,從人設崩塌到淪為“法制咖”,簡直可以做一個“塌房”月歷:2020年2月,國內疫情嚴重時,上海破獲一起口罩詐騙案,犯罪嫌疑人被曝是曾參加過選秀節目《以團之名》的藝人黃智博;5月,因《聲入人心》為人所知的仝卓,在直播時自曝偽造應屆生身份參加高考,被逐出演藝圈……中國偶像行業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
一開始,普通觀眾還像“瓜田里亂竄的猹”,每出現一次爆料,哪怕不認識當事人,也會饒有興致地搜索相關新聞。慢慢地,大家對這些“瓜”也失去了興趣,因為大家發現,對于不關心愛豆領域的人,這些名字中幾乎沒有“出圈”的。出道時間短、缺乏代表作的年輕偶像們,只是靠粉絲撐起話題量,而粉絲之外,根本無人關心他們。
“一出道就垮掉”成為常態的背后,是偶像工業越來越低的試錯成本。雖然早在2004年,《超級女聲》就開啟了國內的初代選秀熱潮,但確切地說,如今內地占主流的偶像產業是基于復制日韓“愛豆模式”在2018年誕生的。《偶像練習生》的橫空出世,讓資本大量涌入這個新鮮領域,同質化的選秀節目一個接一個。無論演員、網紅,還是歌手、舞者,都想通過做“愛豆”獲得紅利。平臺需要流量,公司需要短期價值,“愛豆”需要一夜成名,這個領域自然被拔苗助長成了“快消品”。一個偶像倒下了,仍有無數人可以替代,“割韭菜”拼的是速度,而非質量。
同為韓國練習生出道的藝人張藝興,在2020年選秀節目《少年之名》中說了一句實話:這兩年選秀節目太多了,掏空了優質練習生的存量,哪兒還有好苗子。張藝興的評價標準是“能力素養”,而從“偶像自覺”上看,這些半路出家者,也未必對偶像所擔負的責任有明確的認知。這種“愛豆”供不應求的現象,導致了整個市場都出現過于寬容的傾向。
哪怕是粉絲,在不斷遭遇“塌房”事故后,也開始改變最初的想法。調查顯示,超過半數的人明確表示自己所追的偶像“塌過房”,甚至有14.6%的人表示曾塌過三次以上的房。而在最早孕育偶像產業的日韓,包括戀愛在內的“偶像失格”是非常嚴重的行為,沒有人是為了看偶像和其他俊男美女談戀愛而埋單。
另一方面,偶像遵從的是“出名要趁早”,20歲之前參加選秀者比比皆是,這些被網友戲稱為“九漏魚”(九年義務教育漏網之魚)的低齡選手,大多沒有成熟、正確的三觀,進入娛樂圈后容易“誤入歧途”,或被翻出以往的“黑歷史”。之前,由央視舉辦的選秀節目《上線吧,華彩少年》,為了確保參賽者的素質,就首次增加了筆試環節,并把參賽標準“熱愛中華文化,堅定文化自信”“積極陽光、正能量、遵紀守法”“具有良好的個人品質和職業道德”打在了公屏上。
在V R技術迅猛發展的當下,一些平臺甚至開始瞄向了虛擬偶像選秀,樂華娛樂打造了二次元女團A-S O U L,正式入局虛擬偶像產業,愛奇藝則推出了《跨次元新星》,30位虛擬選手參與才藝競演。雖然不是血肉之軀,但至少可以“永不塌房”。
//摘自《鳳凰周刊》2021年第3期,本刊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