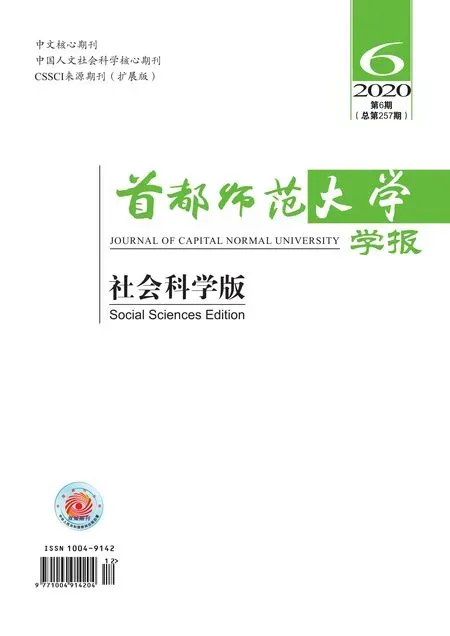國家與地方視野下的運河工程
——以唐—元時期練湖為中心的討論
孫景超
運河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水利工程之一,其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地位與影響早已為學界所認知。全漢昇在《唐宋帝國與運河》中指出:“運河自隋代開鑿后,與唐宋帝國勢運的盛衰消長,著實是非常密切的。”①全漢昇:《唐宋帝國與運河》,商務印書館1946年版,第126頁。對于運河及相關水利工程的研究,也早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②相關研究進展情況可參見王云:《近十年來京杭運河史研究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2003年第6期;高元杰:《20世紀80年代以來漕運史研究綜述》,《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15年第1期;盧勇、馮培:《20世紀以來大運河水利史研究的反思與前瞻》,《中國農史》2019年第5期。
其中水利史學界關注于運河工程的歷史變遷、工程技術效用與水利環境變化等方面;歷史學界的研究側重于歷代運河的變遷、漕運的興廢及影響、區域水利開發的史實復原與評述等問題。相對而言,選擇運河水利工程尤其是具有樞紐性作用的重點工程作為具體個案,深入探討并針對其實際運轉過程及各類變遷影響要素的研究仍然偏少。練湖是大運河上重要的節點工程之一,自東晉修筑以來,歷史上幾經興廢,其變化過程可謂復雜。對于唐代以來的練湖,學界已有相當的研究成果,但縱觀這些研究多偏重于討論練湖的興廢變遷及其漕運功能,①主要有蔡泰彬:《明代練湖之功能與鎮江運河之航運》,《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1970年第2期;施和金:《練湖興廢及其農田水利土壤改良》,《華中師范學院研究生學報》1980年創刊號,收入《中國歷史地理研究》,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費每爾(Eduard B.Vermeer):《一個人工湖泊的興亡:公元300—2000年中國江蘇的練湖》,王利華主編:《中國歷史上的環境與社會》,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版;張俊飛:《唐朝以來練湖的興衰與漕運興廢之關系探析》,《華北水利水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從區域水利與地方史的角度出發討論影響練湖變遷的各類要素及其具體表現的文章仍不多見②筆者所見對此進行專題討論的僅有凍國棟:《唐五代“練塘”資料中所見的“強家”與“百姓”——隋唐五代江南地方社會個案研究之一》,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3輯,武漢大學文科學報編輯部編輯出版,2006年;國外學者的研究,森田明《清代水利社會史研究》(鄭樑生譯,臺北編譯館1996年版)中有練湖一篇,討論了明末清初練湖地區的盜湖問題。。在練湖的歷史變遷中,自唐至元是一個關鍵時期:在此期間,練湖的水利功能完成了從灌溉為主向以蓄水濟漕為主的轉變與定型;作為一項在地化的水利工程,在練湖興廢變化與功能轉型的過程中,國家漕運、區域水利與地方強家大姓等多重因素間的矛盾始終存在并互相影響,使得練湖成為一個多重要素共同影響、宏觀與微觀互相呈現的典型案例;練湖地區豐富的水利文獻資料,亦為呈現這個案例奠定了堅實的史料基礎。③除歷代正史資料與方志外,練湖地區還有為數眾多的水利志書,材料較為集中的有黎世序編:《練湖志》(“故宮珍本叢刊”第266冊,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湯諧等編:《練湖歌敘錄》(線裝書局2004年版),江蘇省國營練湖農場《練湖志》編寫辦公室編:《練湖志》(內部發行1988年)。明清時期的練湖,水利爭議更加頻繁,文獻材料更為復雜,但細究其內容,卻只是歷史故事的延續而已。故而本文選擇唐—元時期的練湖水利為視角,探討在傳統水利工程中國家與地方的多重互動關系。
一、練湖的歷史變化
練湖位于今江蘇丹陽境內,是一處久負盛名的水利工程。關于練湖的起源,史籍多以為始于東晉陳敏。南朝宋顏延年記曰:“晉陵郡之曲阿縣下,陳敏引水為湖,水周四十里,號曰曲阿后湖。”④蕭統編,李善注:《文選》卷22《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054頁。另按,今本《水經注》無此文。南朝陳顧野王《輿地志》云:“練塘,陳敏所立,遏高陵水,以溪為后湖。”⑤顧野王著,顧恒一等輯注:《輿地志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43頁。按:此條輯自《太平御覽》卷66。這一記載在唐代《元和郡縣圖志》中得到確認與擴展:“練湖,在(潤州丹陽)縣北一百二十步,周回四十里。晉時陳敏為亂,據有江東,務修耕績,令弟諧遏馬林溪以溉云陽,亦謂之練塘,溉田數百頃。”⑥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卷25《江南道一》,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592頁。可見練湖之名至遲在唐代已經出現。文獻中又有其他如
“開家湖”“丹陽湖”等稱呼,如明人議論云“先秦時居民疏告官司,議將開姓田地筑梗潴水,得免旱潦,始名開家湖”⑦張國維編:《吳中水利全書》卷20《曹胤儒練湖說》,“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78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745頁。,又或云:“宋建炎間,值世亂,練兵于湖內,因號為練湖”⑧黎世序:《練湖志》卷10《軼事》,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85頁。,對練湖的名稱、來源別有說法。清代《丹陽縣志》所云“練湖,晉郗鑒所鑿塘,練兵以備陳敏者也,故名練塘”⑨光緒《丹陽縣志》卷2《山水》,“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頁。,其說與眾不同,且只此一例,當不可信。
練湖修筑之初,其功能為單一的蓄水灌田。又因風景秀麗,曾引來文人雅士游幸,宋文帝時得名為“勝景湖”,謝中郎(謝萬)、昭明太子等一時才俊于此皆有詩文典故。但在當時,練湖規模不大,聲名不甚彰顯。自唐代中期開始,練湖的知名度開始迅速上升,歷代正史言江南運河者多提及練湖;至明清時期,練湖甚至躋身于“天下之五湖”之列,“饒州之鄱陽,岳州之青草,潤州之丹陽,鄂州之洞庭,蘇州之太湖,此為天下之五湖”[10]程登吉原著,沈元起譯白:《言文對照幼學瓊林讀本》卷1《地輿》,上海廣益書局1936年版,第12頁。。其轉變原因,正是由于練湖成為了歷代運河中不可忽視的重要水利工程。
自隋代建立起全國范圍內的大運河體系后,練湖作為江南運河鎮江段的水柜,其重要性日益上升。在唐代中期以前,練湖已經承擔了灌田、濟運與泄洪等多重功能,“每正春夏,雨水漲滿,側近百姓引溉田苗。官河水干淺,又得湖水灌注,租庸轉運及商旅往來,免用牛牽。若霖雨泛溢,即開瀆泄水,通流入江。”也正在此時,練湖開始受到地方圍墾的影響,“比被丹徒百姓筑堤橫截一十四里,開瀆口泄水,取湖下地作田”,其結果自然是影響到練湖水利功能的發揮,“自被筑堤已來,湖中地窄,無處貯水,橫堤壅礙,不得北流。秋夏雨多,即向南奔注,丹陽、延陵、金壇等縣良田八九千頃,常被淹沒。稍遇亢陽,近湖田苗,無水溉灌。所利一百一十五頃田,損三縣百姓之地”①盧憲:《嘉定鎮江志》卷6《地理》,“宋元方志叢刊”第三冊,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2369頁,亦見于《全唐文》卷370。。唐代宗永泰二年(766),轉運使劉晏、刺史韋損等重新修復,“增理故塘,繚而合之,廣湖為八十里”②李華:《潤州丹陽縣復練塘頌并序》,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779,中華書局1966年版,第4111頁。。經此治理,練湖面積擴大為周回80里,相關的水利設施如湖堤、斗門、涵閘等皆完備,“今已依舊漲水為湖,官河又得通流,邑人免憂旱潦”③盧憲:《嘉定鎮江志》卷6《地理》,“宋元方志叢刊”第三冊,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2369頁。。練湖也發展成為集灌田、濟運與滯洪于一體的綜合性水利工程。
唐末藩鎮戰亂,練湖的水利設施被破壞,居民又墾湖為田,“前唐末兵亂之后,民殘湖廢。安仁義取斗門余木以修戰備,自此近湖人戶耕湖為田”。南唐昇元五年(941),丹陽令呂延禎再次重修,“為材役工,于古斗門基上,以土堰堰捺及填補破缺處”,使練湖的水利功能得到一定的恢復,“自今歲秋后不雨,河道干枯,累放湖水灌注,使命商旅舟船往來免役牛牽;當縣及諸縣人戶請水救田,臣并掘破湖岸給水”④盧憲:《嘉定鎮江志》卷6《地理》,“宋元方志叢刊”第三冊,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2369頁。。
北宋結束五代十國分裂局面后,東南漕運關系到國計民生,練湖的地位也更加突出。宋哲宗紹圣年間,知丹陽縣蘇京主持開浚練湖,“募民浚湖,復度地之宜,易置斗門十數,以時潴泄。是歲不知饑繼。是湖水有余,公私兩便”⑤俞希魯編纂,楊積慶等校點:《至順鎮江志》卷7《山水》,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86頁。。徽宗宣和年間,漕臣孟庾等浚常州鎮江運河,對練湖亦有補葺。兩宋變革之時,練湖亦曾被侵占。紹興初年,“堤岸弛禁,致有侵佃冒決,故湖水不能潴蓄,舟楫不通,公私告病。若夏秋霖潦,則丹陽、金壇、延陵一帶良田,亦被淹沒”。但南宋偏安東南后,江南運河重要性大大增加,練湖隨即得到修復。紹興七年(1137),兩浙轉運使向子諲、丹陽知縣朱穆等人重修,“增置二斗門,一石,及修補堤防,盡復舊跡,庶為永久之利”⑥脫脫等:《宋史》卷97《河渠七》,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2404-2405頁。。此后乾道、淳熙、嘉定、淳祐、景定年間,均有興筑。經過多次重修改建后,練湖的水利格局有所變化,“宋紹興時,中置橫埂,分上下湖,立上、中、下三閘。八十四溪之水始經辰溪沖入上湖,復由三閘轉入下湖”⑦張廷玉等:《明史》卷86《河渠四》,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107頁。。由此使得練湖穩定地分為上下兩湖,上湖水高于下湖水數尺,下湖水又高于運河水數尺,上湖蓄水為下湖補充水源,下湖蓄水接濟漕運,歷代又陸續添設埂、涵、閘等設施控制水流,實現了對練湖水利的精準控制。
元代統一江南之初,社會秩序未復,練湖又被侵占圍墾,“豪勢之家于湖中筑堤圍田耕種,侵占既廣,不足受水,遂致泛溢”,但很快在元世祖至元末年得到修復,此后在成宗大德年間、英宗至治年間及泰定帝時期,練湖均得到興修,管理制度也日益完善。至治年間修治工程完成后,為加強管理,對舊有湖兵進行添補,“練湖舊有湖兵四十三人,添補五十七名,共百人,于本路州縣苗糧三石之下、二石之上差充,專任修筑湖岸。設提領二員、壕寨二人、司吏三人”。對于練湖的管理維護,由當地地方官員負責,“除關本路達魯花赤兀魯失海牙總治其事,同知哈散、知事程郇專管啟閉斗門”⑧宋濂:《元史》卷65《河渠二》,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1635頁。。
至明清時期,隨著漕運制度的日益完善,練湖與運河的關系更加密切。同時對練湖的盜墾之風也愈演愈烈,至明末清初,練湖上湖多已墾辟成田,圍田、灌田與濟運之間的矛盾,也更加激烈突出。清末漕糧改由海運后,漕運停罷,練湖也再無人過問,很快被全部辟為農田。

圖1 練湖圖
縱觀練湖的變遷,其功能主要圍繞灌田與濟運而變化。唐代以后雖以蓄水濟運為主,但灌田的功能始終存在,由此導致兩者間的矛盾也始終存在,正如清人所總結:“自晉唐迄今,廢興不一。要而論之,用之之法有三:一曰灌田,一曰濟運,一曰半以灌田,半以濟運。”①盛符升:《練湖考》,賀長齡輯:《皇朝經世文編》卷104《工政十》,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3665頁。同時練湖在整個太湖流域的水利格局中,也承擔著攔蓄上游來水的重要功能。雖然在某些時期其水利功能有所偏重,但在大多數時期,練湖仍是集蓄水、灌田、濟運多重功能于一體的綜合水利工程。
二、多重利益的博弈
練湖的出現,肇始于其所在區域農業開發的需要;唐代以后其水利功能發生變化,則是由國家漕運與運河水情決定的。在宏觀上,它與唐代以來經濟重心轉移引發的國家漕運有密切關系;在中觀層面,受到江南地區尤其是鎮江一帶區域農田水利發展的影響;在微觀層面,又與練湖周邊的民眾利益不可分割。練湖的歷史變遷,體現了多重要素博弈的過程。
1.國家漕運
練湖的重要地位,首先在于其與漕運的重要關系。自唐代開始,隨著北方政治中心與南方經濟中心的分離,漕運南方財賦與糧食到北方成為歷代中原王朝面臨的頭等大事。“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②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53《食貨三》,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365頁。。沿至宋代,這一趨勢繼續保持并不斷加強,“至道初,汴河運米五百八十萬石。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石”③脫脫等撰:《宋史》卷175《食貨上三》,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4251頁。。南宋時期偏安東南,運河成為其軍國命脈之所在,鎮江一帶運河地位上升,“昔者南徐特一郡耳,四方之舟至者有限,則一斗門足以通之。今天子駐蹕錢塘,南徐實在所北門,萃江、淮、荊、廣、蜀、漢之漕輻輳于此,過客來往,日夜如織”①盧憲:《嘉定鎮江志》卷6《地理》,“宋元方志叢刊”第三冊,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2373頁。。至元代,“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眾,無不仰給于江南……(江南之糧)至于京師者一歲多至三百萬余石”②宋濂撰:《元史》卷93《食貨一》,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2364頁。。元代雖有海運,但運河仍發揮重要作用。有鑒于此,歷代都對運河沿線的水利設施予以特別的重視。
江南運河的開鑿與形成,經歷了漫長的歷史時期。早期運河多利用天然河流與湖泊來溝通,如《越絕書》所記:“吳古故水道,出平門,上郭池,入瀆,出巢湖,上歷地,過梅亭,入楊湖,出漁浦,入大江,奏廣陵。”③李步嘉校釋:《越絕書校釋》卷2《吳地傳》,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32頁。其時運河在江陰漁浦一帶入長江以達廣陵,尚未經過鎮江一帶。后世方志往往將鎮江附近的運河追述至秦鑿丹徒曲阿,但無從確認。從文獻記載來看,至遲到六朝時期,鎮江一帶已經有運河及相關水利工程如丁卯埭等,“晉元帝子裒鎮廣陵,運糧出京口,為水涸奏請立埭,丁卯制可,因以為名”④王象之撰:《輿地紀勝》卷7《鎮江府》,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413頁。。《南齊書》亦記:“丹徒水道入通吳會,孫權初鎮之。”⑤蕭子顯撰:《南齊書》卷14《州郡上》,中華書局1972年版,第246頁。其時為避開長江風浪險惡,運河主線乃在鎮江西南的破岡瀆與上容瀆一線。《至順鎮江志》引《建康實錄》記:“吳大帝赤烏八年,使校尉陳勛作屯田,發屯兵三萬鑿句容中道,至云陽西城,以通吳會船艦,號破岡瀆,上下一十四埭。上七埭,入延陵界;下七埭,入江寧界。于是東郡船艦不復行京江矣。晉、宋、齊因之。梁以太子名綱,乃廢破岡瀆而開上容瀆……至陳霸先,又湮上容瀆,而更修破岡瀆。”⑥俞希魯編纂,楊積慶等校點:《至順鎮江志》卷7《山水》,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79頁。按:此處引文與今本《建康實錄》文字略有不同。隋平陳統一后,平毀南朝建康城,原以建康為中心的破岡瀆等運河也被廢棄。隨著江南的政治中心轉移至揚州,隔江相對的京口(鎮江)地位也開始凸顯。煬帝大業六年(610),“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廣十余丈,使可通龍舟”⑦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鑒》卷181,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5652頁。。隋開江南河,奠定了鎮江地區運河的大勢,并延續至今。

圖2 鎮江府全境水利圖
世人印象皆以為江南水鄉澤國,而鎮江一帶地勢相對高仰,水源困難,練湖正是鎮江段運河重要的水柜,“京口漕河,自城中至奔牛堰一百四十里皆無水源,仰給練湖”⑧盧憲:《嘉定鎮江志》卷6《地理》,“宋元方志叢刊”第三冊,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2365頁。。歷代多傳說“湖水放一寸,河水漲一尺”,尤其在冬春水涸之時,練湖對于補充運河的水源意義重大。故而在鎮江地區乃至整個國家漕運的水利格局中,練湖的地位與作用顯得尤為突出,“鎮江之水利以漕河為先,漕河以丹陽為先。丹陽居丹徒、金壇地之中,受練湖之水以濟運也。故丹陽之漕河,以治練湖為先”①姜寶:《鎮江府水利圖說敘》,《練湖志》卷7《書敘》,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28頁。。
隨著練湖地位的上升,對它的管理與維護也就更加頻繁。為維持練湖的水利功能,歷代不斷加以修治,“繇晉及唐迄于今(元),廢而復壞而修者不可勝紀,每一役輒劇勞甚費,乃克底于定”②張國維編:《吳中水利全書》卷24《陳膺重修練湖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78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903頁。。練湖自唐代開始進入歷代正史的記載,此后《宋史》《元史》《明史》“河渠志”皆有其專篇內容。基于練湖對鎮江段運河的重要濟漕作用,歷代政府不惜動用國家與地方兩級的財力與人力,來對其進行修治與維護。如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總領錢良臣修丹陽練湖橫壩及諸斗門函,“計用民力二十一萬六千二百九十有七,糜錢二千一百三十一萬四千八百有奇,米一萬八千八十一石”③張國維編:《吳中水利全書》卷10《水治》,“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78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336頁。。景定三年(1262),知丹陽縣趙必棣修筑練湖岸埂,“支撥安邊太平庫會子二萬二千五百七十一貫,及平江府支米五萬石,收買竹木,雇募人夫”④張國維編:《吳中水利全書》卷10《水治》,“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78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337頁。。元代至治年間的一次修治,“浚練湖夫三千人,九十日畢,人日支鈔一兩、米三升,共該鈔萬八千一十四錠二十兩,米二萬七千二十一石六斗”⑤宋濂撰:《元史》卷65《河渠二》,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1634頁。。泰定三年(1326),任仁發、毛莊等人疏漕渠浚練湖,“差倩本路及常州、平江、建康、江陰五路夫萬五千二十二人,工六十日,糜錢六十二萬七百二十緡,米萬八千九百石有奇”⑥張國維編:《吳中水利全書》卷10《水治》,“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78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338頁。。在這些修治活動中,皆投入了巨大的人力與財力;而運河與練湖修治通常是捆綁在一起的,目的正是為了維持通過鎮江運河的漕運。
2.區域水利
練湖坐落在丹陽境內,作為在地化的運河水利工程,除了承擔運河水柜的重要職能外,還在區域水利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其影響范圍主要是練湖周邊的丹徒、丹陽(曲阿)、金壇等縣。練湖的出現與變化,與這一地區經濟開發及水利格局的變化密切相關。
秦漢時期,江南地區基本還停留在“火耕而水耨”的自然經濟狀態,《史記》載:“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埶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⑦司馬遷撰:《史記》卷129《貨殖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270頁。經過數百年的開發,至南朝宋元嘉年間,三吳地區開始呈現繁榮景象,“江南之為國盛矣……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饑”。尤其是江南地區所在的揚州最為發達,“揚部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⑧沈約撰:《宋書》卷54《列傳第十四》,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540頁。。延至唐宋,隨著人口的大量南遷與農業、水利的進步,完成了經濟重心的遷移,由此奠定了江南地區在整個中國的經濟重心地位。
鎮江地區雖屬于傳統的江南地區,但因其地勢較高,水利特點與蘇州為中心的江南低地區不盡相同,除了部分低洼地區需要防備洪澇災害外,多數地區更要著眼于蓄水防旱。東晉以前因水利不興,該地農業仍較為落后,“舊晉陵地廣人稀,且少陂渠,田多惡穢”⑨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卷25《江南道一》,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592頁。。其主要水利措施是修筑塘壩,自六朝時期開始,這一地區的塘壩的修筑已經比較普遍,如南齊建元三年(481),蕭子良曾論及:“(丹陽郡)舊遏古塘,非唯一所。而民貧業廢,地利久蕪。近啟遣五官殷沵、典簽劉僧瑗到諸縣循履,得丹陽、溧陽、永世等四縣解,并村耆辭列,堪墾之田,合計荒熟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頃,修治塘遏,可用十一萬八千余夫,一春就功,便可成立。”[10]蕭子顯撰:《南齊書》卷40《列傳第二十一》,中華書局1972年版,第694頁。這里提到的舊遏古塘,顯然是早已有之,東晉張闿曾在此立曲阿新豐塘,“時所部四縣并以旱失田,闿乃立曲阿新豐塘,溉田八百余頃,每歲豐稔。葛洪為其頌。計用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二十功”①房玄齡等撰:《晉書》卷76《列傳第四十六》,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018頁。。從地方志記載來看,六朝時期寧鎮地區興建陂塘堰壩的數量,都大大超過前代,顯示出該地區高亢田及丘陵地區的進一步開發。②張芳:《寧、鎮、揚地區歷史上的塘壩水利》,《中國農史》1994年第2期。練湖也是在這一背景下出現,最初的名稱“練塘”說明其功能正是灌田。直到明清時期,塘壩水利都是鎮江地區重要的水利形式,“京口地高,所在陂塘多與田接,旱干則資以灌溉,水溢則于此舒泄,三縣(丹徒、丹陽、金壇)諸鄉無地無之”③朱霖等:《乾隆鎮江府志》卷2《山川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80頁。。
唐代以后,練湖功能以濟漕轉運為主,但在區域水利中仍發揮著巨大影響,其作為灌溉水源的功能仍然存在,“夏秋戽以溉田,冬春放以濟運,載在縣志,蓋亦從來然矣”④姜寶:《漕河議》,《練湖志》卷6《論說》,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18頁。。北宋時期兩位著名的太湖水利專家郟亶、單鍔的水利議論中,對練湖及其水利功能均有詳細討論。南宋詹體仁曾論及江南運河的雙重作用:“浙右之有漕渠,非止通饋運資國信往來而已,蘇、秀、常、潤田之高卬者實賴之。于是開漕渠,浚練湖,置斗門,為旱澇備。”⑤真德秀:《西山文集》卷47《司農卿湖廣總領詹公行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74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763頁。這一局面,一直維持到清代。
在練湖的歷史上,長期流傳著自唐代開始“盜決湖水罪比殺人”之說,在歷代水利議論中多被提及,甚至寫入了《宋史·河渠志》:“在唐之禁甚嚴,盜決者罪比殺人。”現存唐代文獻中雖未見其說,但對比唐代《水部式》等文獻的嚴密風格,這一嚴格規定有存在的可能。劉晏、韋損等人修復練湖后,“依舊漲水為湖,官河又得通流,邑人免憂旱淹”,即濟運與灌溉并舉,并未完全禁止灌田。至宋代,法令似乎有所放松,“本朝寖緩其禁以惠民,然修筑嚴甚”。從實際情況來看,仍然是濟運與灌田并重。宋元時期多次修浚練湖,其目的仍然如此,“庶幾練湖漸復其舊,民田獲灌溉之利,漕渠無淺涸之患”⑥脫脫等撰:《宋史》卷97《河渠七》,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2405頁。。北宋許元知潤州丹陽縣時,曾面臨著濟運與灌田的水利矛盾:“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為漕渠一尺,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公請借湖水溉民田,不待報決之。州守遣吏按問,公曰:‘便民,罪令可也。’竟不能詰。由是溉民田萬余頃,歲乃大豐。”⑦歐陽修:《文忠集》卷33《尚書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許公墓志銘并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02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261頁。在清代所輯的《練湖志》《練湖歌敘錄》等文獻中,歷代引(盜)練湖水灌田的記載層出不窮。顯然,區域水利中的灌溉問題,仍是練湖必須承擔的重要職能之一。
3.地方豪民
練湖自修筑之后,為瀕湖地區帶來了豐饒的利益,時人形容其情況:“幅員四十里,菰蒲菱芡之多,龜魚鱉蜃之生,厭飫江淮,膏潤數州。”⑧李華:《潤州丹陽縣復練塘頌并序》,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779,中華書局1966年版,第4111頁。圍繞著這些利益,周邊居民尤其是地方豪民展開了激烈爭奪,這也對練湖的變遷產生了重要影響。
早在唐代中期,這種利益爭奪即已經展開,“其傍大族強家,泄流為田,專利上腴,畝收倍鐘,富劇淫衍。自丹陽、延陵、金壇環地三百里,數合五萬室,旱則懸耜,水則具舟,人罹其害九十余祀,凡經上司紛紛與予八十一斷”⑨李華:《潤州丹陽縣復練塘頌并序》,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779,中華書局1966年版,第4111頁。。大族強家的圍墾,導致的結果是練湖湮廢,水利功能喪失,后由韋損等人之力方得修復。唐末五代十國時期,練湖先被兵亂,后被鄰湖居民耕湖為田,“農商失恃,漁樵失業,河渠失利,租庸失計”。從中得利的仍然只是少數地方豪強,即呂延禎所云“廢湖豐已(己)者不十余家,有湖無災者四縣之地”[10]盧憲:《嘉定鎮江志》卷6《地理》,“宋元方志叢刊”第三冊,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2369頁。,正是其真實寫照。
宋代以后,由于圍湖墾田的發展,練湖也被大面積圍墾,傳聞“湖內田畝凡十萬三千有奇”,實際雖沒有如此之大,利益仍然可觀。練湖附近的各類居民,往往從各自利益出發來改造練湖水利,“佃田之家私放湖水,冀免淹沒而利于種作也;又漁戶私開涵洞為水門,張網以取魚也。而本縣水利官力或不能禁治,于是湖遂歲歲涸,湖歲歲涸則運河無可以濟”①姜寶:《漕河議》,《練湖志》卷6《論說》,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19頁。。這種矛盾在水資源短缺的干旱季節,更容易激化。隨著南宋以后江南地區開發程度的加強,圍繞練湖的利益爭奪更為突出,由此引發的利益爭奪案件屢發,“自元迄明,往往利歸豪勢,豪去民復爭之。死于訟者不知幾人,案牘棼如,官弗勝理”②黎世序編:《練湖志》卷10《軼事》,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87頁。。清代匯編的《練湖志》載有諸多此類事件,尤以南宋時期最為密集。如宋高宗時,“有豪民鐘彥等妄捏湖系荒開,草塌盡行耕種。比有韓運使題奏官鈔回買為湖,計用道鈔四十萬貫文。立定四至,東至北岡運河為界,西至彭城雙廟為界,南至丹陽辰溪為界,北至丹徒縣華村龍頭岡為界”③丁一道:《練湖議》,《練湖志》卷6《論說》,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17頁。。宋孝宗乾道年間,“有吳太后管莊人許亮計囑運使侵佃,尋發,官司照例問罪,賠罰官鈔二千萬。比時又有吳八十,系都統司門客侵佃,亦行革罰,將吳八十刺面發配,家產沒官”。度宗咸淳二年(1266),“有豪民步十七,買囑賈平章門下四圣觀道士,在湖耕種,釘牌立賈府名色。本縣題奏將步十七家產沒官,發配真州,仍行鎮江有司起夫修筑,掘去田埂,盡復為湖”④以上均見丁一道:《練湖議》,《練湖志》卷6《論說》,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17頁。。及至元初鼎革之后,“豪勢之家于湖中筑堤圍田耕種,侵占既廣,不足受水,遂致泛溢”⑤宋濂撰:《元史》卷65《河渠二》,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1633頁。。這些案例大多數是在國家政治不穩定時,地方豪民趁機侵奪練湖造成的。
宗教寺廟在練湖也有一定的利益存在,從宋代開始,佛、道寺觀就在練湖地區獲得田產,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練湖變遷之中。宋哲宗元祐年間,“茅山道官請佃耕種,在北岡建立倉院,尋因水潦沖倒南岸。府縣踏看,折(拆)毀倉院,仍舊為湖積水。道官追度,流三千里”⑥丁一道:《練湖議》,《練湖志》卷6《論說》,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17頁。。徽宗大觀四年(1110),“臣僚言:‘有司以練湖賜茅山道觀,緣潤州田多高仰,及運渠、夾岡水淺易涸,賴湖以濟,請別用天荒江漲沙田賜之,仍令提舉常平官考求前人規畫修筑。’從之”⑦脫脫等撰:《宋史》卷96《河渠六》,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2386頁。。鎮江甘露寺很早就在練湖地區擁有大量湖田,“丹陽縣練湖莊田四十頃,宋大中祥符間,僧祖宣住持時賜,在籍三十頃”⑧萬歷《京口三山全志》卷1《田土》,“中國方志叢書”,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96頁。。清代中前期,官立普生莊戶于練湖湖濱,被圍墾的湖田成為京口護漕救生事業的主要經費來源。⑨吳滔、阮寶玉:《清中前期的京口救生與練湖興廢》,唐力行主編:《江南社會歷史評論》第十二期,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第31-46頁。這一因素的摻入,也使得練湖的興廢過程更加復雜。
三、余論
練湖作為一項公共水利工程,其興筑及后來的變遷,均與所處的歷史時代及地理位置密切相關。作為水利灌溉工程的練湖,與江南地區的經濟開發進程緊密聯系,隨著漢晉時期江南地區的農業開發向鎮江一帶高地區的擴展,以蓄水灌溉為主要功能的陂塘水利得到充分發展,練湖應運而生。宋代以后,由于江南地區人地關系的緊張,圍湖造田之風大興,練湖周邊的湖泊多被墾湖為田,“自丹陽至鎮江蓄為湖者三:曰練湖,曰焦子,曰杜墅。歲久,居民侵種,焦、杜二湖俱涸,僅存練湖,猶有侵者”[10]張廷玉等撰:《明史》卷86《河渠四》,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106頁。。在這種趨勢之下,練湖卻能屢廢屢興,則與其在漕運中的地位密切相關。
隋代大運河體系形成后,漕運在歷代王朝政治地位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練湖作為鎮江段運河水柜的地位不斷得到強化,其水利功能也轉向以蓄水濟運為主。為維持練湖的濟運功能,歷代王朝不惜投入大量的人力、財力,這與練湖作為公共水利工程的地位正相符合。比較值得關注的是,唐五代時期,修治練湖多由地方官員來動議與主持,財力也主要來自地方。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在討論唐代灌溉工程時曾指出:“工程計劃系由地方政府的官員,尤其是刺史、太守等來策動的。”①轉引自楊聯陞:《從經濟角度看帝制中國的公共工程》,《國史探微》,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頁。從宋代開始,隨著中央財政的加強,修治練湖的經費主要來自中央。顧炎武曾指出唐宋以來財政的變化:“唐自行兩稅法以后,天下百姓輸賦于州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及宋太祖乾德三年,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無得占留。自此一錢以上皆歸之朝廷,而簿領纖悉,特甚于唐時矣。然宋之所以愈弱而不可振者,實在此。”②顧炎武撰,嚴文儒、戴揚本校點:《日知錄》卷12《財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92-493頁。這種財政體制上的變化,造成地方財政能力的短絀,“今日所以百事皆廢者,正緣國家取州縣之財,纖毫盡歸之于上,而吏與民交困,遂無以為修舉之資”③顧炎武撰,嚴文儒、戴揚本校點:《日知錄》卷12《館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03頁。。財政體制導致地方政府財用不足,無力對練湖進行日常的興修和維護,也為后世練湖屢被占用埋下了伏筆。
同時,在練湖周邊地區的“強家大族”亦是重要的影響要素。這些強家大族歷代有所興替,從南朝時開始有所發展,至隋唐五代時已經在當地擁有相當的影響力,“包括家族力量、經濟實力或社會地位以及一定的政治聲望或影響力等等”④凍國棟:《唐五代“練塘”資料中所見的“強家”與“百姓”——隋唐五代江南地方社會個案研究之一》,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3輯,2006年。。這些力量在歷代以“豪強”“士紳”“富戶”等名目始終存在,并在地方事務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每當國家與地方政府力量衰弱時,練湖往往被此類人等占據為田;但當國家漕運恢復時,這些力量又被壓制,練湖也能隨之復興。
楊聯陞在探討中國古代公共工程時曾指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與地方領導力量(包括地主、商人、僧人、道士等)都是不可忽視的力量。⑤楊聯陞:《從經濟角度看帝制中國的公共工程》,《國史探微》,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頁。在唐—元的歷史時期內,由于國家漕運、區域水利與地方豪強的利益未盡一致,從而使得練湖陷入到反復興廢的循環之中;在此循環過程中,練湖的興廢與具體功能取決于當時的政治形勢與各方利益的博弈結果。在歷代正史中,多強調練湖對國家漕運的作用,而在當地方志中,又往往將灌溉功能置于濟漕之前,這種差異性描寫亦體現出其中的微妙關系。練湖在歷史上的復雜變化,典型地體現了中國古代公共工程的發展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