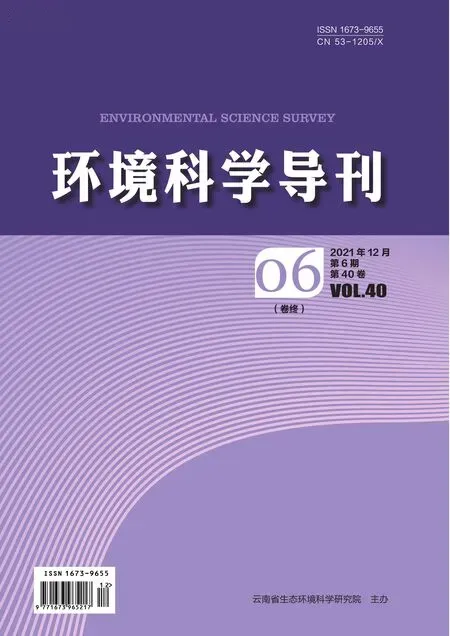云南省重金屬污染農用地風險管控對策探討
崔 靜,王 麗,和麗萍,陳異暉
(1. 云南省生態環境科學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034;2. 云南環境工程設計研究中心,云南 昆明 650034;3.中國科學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 陜西 楊凌 712100)
0 引言
“萬物土中生,食以土為本,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土壤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石,人類消耗的食物和能量99%來源于土壤,一旦農用地土壤被污染,會導致農產品中重金屬的累積,并最終轉移至人體,進而嚴重危害人體健康[1]。近年來,我國農用地土壤重金屬污染形勢嚴峻[2],耕地土壤重金屬等污染物土壤點位超標率達19.4%[3],由于農用地土壤重金屬污染進而引發農產品質量安全的問題受到了廣泛關注。有關學者的調查研究表明[4-5]:我國河北、甘肅等地區的主產作物小麥均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鎘含量超標現象,而食用這些重金屬污染的小麥導致當地居民存在嚴重的非致癌風險[6]。因此,開展重金屬污染農用地的風險管控和修復治理,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已十分迫切[7]。我國學者對農用地土壤重金屬污染修復治理已開展了大量的研究[8-11],然而,在實踐過程中發現重金屬污染農用地治理修復成本高、難度大,不利于被接受,中央土壤污染防治專項資金項目庫入庫要求中也明確,除技術應用試點項目外,原則上不予支持[12],因此探討重金屬污染農用地風險管控對策顯得尤為重要。
云南省作為全國土壤污染問題較為突出的省份之一,局部區域土壤重金屬污染嚴重,區域土壤高背景疊加人為污染,使得鎘(Cd)、鉛(Pb)、砷(As)、汞(Hg)在農用地中出現高值,且多體現為以兩種至三種污染元素為主的復合污染。楊牧青等研究了云南省新產區土壤和三七中重金屬元素的累積狀況,新產區三七葉片和塊根中的Cd、Pb、As重金屬超標嚴重,嚴重影響了三七的質量,威脅到了人體健康[13]。肖青青[14]等研究了個舊市郊雞街鎮的蔬菜重金屬含量,結果表明萵筍、青菜和薄荷Pb含量超過了食品安全限量標準。云南省作為西南地區的糧食主產區之一,其土壤和農產品生態環境安全已受到廣泛關注。當前針對云南省土壤重金屬污染農用地的研究多集中在重金屬分布特征[13-15]、污染現狀等,而針對重金屬污染農用地的風險管控措施探討的報道較少。本文在總結近年我國重金屬污染農用地風險管控防治經驗的基礎上,對云南省重金屬污染農用地在污染防治方面面臨的問題和挑戰進行梳理,旨在為扎實推進云南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保障重金屬污染農用地土壤生態系統的良性運轉提供科學支撐。
1 我國重金屬污染農用地風險管控防治經驗
農用地風險管控主要是通過農藝調控、替代種植、種植結構調整或退耕還林還草,輪作休耕、輪牧休牧以及劃定特定農產品禁止生產區域等措施,保障耕地安全利用,確保農產品安全,特別是糧食安全[16]。
1.1 農藝調控
農藝調控是利用農藝方法如選取低累積品種、調節土壤理化性質、科學管理水分等對耕地土壤中污染物的生物有效性進行調控,減少污染物從土壤向作物特別是可食用部分的轉移,從而保障農產品安全生產,實現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的目的。
在重金屬污染區域篩選低累積品種是目前國內常用的農藝調控技術之一。低累積品種的選擇對重金屬污染農用地的安全利用具有較強的實踐意義。低累積作物品種是指在相同土壤環境條件下作物可食部位中污染物積累量相對較低的品種。通過利用作物種內差異,選育同種作物中低積累的品種,從而達到污染土壤安全利用的目的。目前,我國各省份的相關學者正在積極探索適合重金屬污染土壤的低累積品種,楊惟薇[17]等研究了鉛鎘脅迫下10個來自不同產地的玉米品種對重金屬鉛和鎘的累積特性,篩選出抗性強且對鎘累積能力最弱的廣甜3號,適宜在中輕度污染農用地推廣種植。張磊[18]等基于廣西常植的10個水稻品種,研究了不同水稻類型的耐鎘特性發現,常規稻野絲占和玉絲占的耐鎘特性優于雜交稻和超級稻,該研究對廣西存在較高糧食鎘含量超標風險的意義重大。陳玉梅[19]在杭州蔬菜供應產地研究中,通過不同等級重金屬污染,篩選出鎘、鉻、銅、鋅的耐性較強且低積累的蔬菜分別為黃瓜、番茄、番茄、毛豆,該研究對杭州乃至全國蔬菜的安全生產提供了保障。譚玲[20]研究了廣州不同鎘濃度下37個菜心品種對鎘積累的差異,篩選出鎘低累積菜心品種,并確定出鎘、鉛、鉻復合污染下該低累積菜心品種對重金屬的吸收特性。
除積極探索低累積品種外,科學調理水分、調節土壤理化性質等也是農藝調控的有效措施。崔曉熒[21]等的研究發現,淹水和干濕交替兩種水分管理模式下,干濕交替能夠顯著提高水稻的生物量及產量,但同時也增強了重金屬鉛、鎘、鉻在土壤-水稻系統中的遷移能力,顯著提高了米粒中鎘的含量。土壤水分含量對水稻根際土壤中的砷、銅、鋅等含量雖然影響不大,但卻可以顯著影響水稻不同器官對上述元素的吸收積累[22]。龍靈芝[23]等探究了水分管理和磷酸鹽施用下水稻土中鎘的有效態轉化情況,結果表明田間持水量在75%時施用磷酸鹽對土壤中鎘的穩定性較好,水分管理是土壤中鎘形態轉化的主要影響因素。雖然水分調控管理具有無二次污染、可操作性強、無附加經濟投入、且有效性高等優點而備受學者關注[24],但是在實踐中單一的農藝調控措施要達到農用地安全利用的要求往往很難,探索多措施組合對重金屬污染農用地風險管控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鄒紫今[25]研究了水分管理與改良劑協同控制的6種處理方式下水稻對土壤重金屬和砷的累積情況,結果表明,從水稻產量和水稻品質安全的角度出發,碳酸鈣和濕潤灌溉、羥基磷灰石和濕潤灌溉兩種處理方式可以有效降低水稻對重金屬鎘、鉛和砷的吸收。有研究表明[26],種植低鎘積累品種,結合全生育期淹水灌溉、施用生石灰調節的方式可以有效降低水稻地上部分的含量,并提高水稻產量。
1.2 阻隔技術
阻隔技術也是常用的農用地風險管控技術之一。董如茵[27]在湖南岳陽市湘陰縣的研究發現,對油菜噴施鋅肥可以抑制根部鎘吸收從而降低油菜地上部鎘含量,噴施鋅肥是調控鎘低積累油菜安全生產的較好措施。王林等[28]通過研究比較了植物阻隔、化學鈍化及其聯合修復措施對天津市某污灌區鎘污染菜地的修復效果,結果表明種植鎘低累積品種同時聯合應用植物阻隔和鈍化修復措施,可以較好地保障污灌區鎘污染菜地的安全利用。研究表明[30],葉面噴施氨基酸螯合硒營養液肥的同時基施硅鈣肥能有效降低水稻籽粒中的鎘含量,葉面阻隔技術配合其他措施也成為現行重要受污染農用地風險管控的有力措施。
1.3 替代種植
替代種植是利用作物的種間差異,選擇種植可食部分對重金屬積累能力弱的作物替代原有的可食部分對重金屬累積能力強的作物,與低累積作物品種篩選不同之處在于其替換了耕種作物物種,適用于重金屬重度或嚴重污染的農用地。替代種植不僅可以使污染的農用地安全利用,還可以獲取一定的經濟效益。
萬壽菊是提取葉黃素的優質材料,是一種高價值的經濟作物[30]。研究表明,萬壽菊對土壤中重金屬鎘、鉛有一定的積累量,可用于云南蘭坪鉛鋅礦周邊污染農田的替代種植[31]。棉花具有較強的耐鎘特性,能夠同時兼顧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是我國中南部地區重金屬污染農用地安全利用的最佳作物之一[32]。
2 云南省重金屬污染農用地風險管控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2.1 支撐重金屬污染農用地風險管控/管理的數據有限
研究受污染農用地的污染特征,對受污染農用地實施風險管控意義重大。明確受污染農用地重金屬污染特征,在采取農用地風險管控措施時可以做到對癥下藥。姜玉玲[33]等研究了河南省新鄉市某電池廠附近污灌農田重金屬污染特征,建議將電池廠3.5km以內的污灌農田劃為嚴格管控類農用地,并按照嚴格管控類農用地要求采取相應的替代種植、退耕還林措施。截至2020年,云南省按照《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要求,已全面完成農用地土壤污染詳查工作以及耕地質量類別劃定工作,明確了農用地安全利用和嚴格管控區域,但是在實施受污染農用地風險管理中,仍面臨著難題。農用地土壤污染狀況詳查數據暫不公開造成其成果應用受限,且詳查對象僅針對常規種植糧食作物,對于云南典型高原特色農產品如蔬菜、水果、中藥材、茶葉等尚缺乏有效調查數據,管理部門難以在決策依據不足的情況下采取風險管控措施,進而影響農用地分類管理工作的推進。
2.2 現有的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或風險管控技術儲備難以滿足工作需求
從全國來看,各種重金屬污染農用地的安全利用技術或模式研究均較為活躍,且有一些技術已經得到推廣應用。但云南省的技術研發基礎薄弱,在制定土壤安全利用或風險管控方案時,沒有成熟的技術或模式可供選擇,且因各地地域環境、氣候條件,土壤性質以及土壤污染特征等條件各異,某種技術、模式的簡單引進、套搬可能存在能力低于預期或出現“水土不服”,無法解決實際問題。
2.3 受制于云南省較為落后的農業經濟,受污染耕地的安全利用或風險管控意識較為薄弱
因云南省經濟較發達省份落后,受經濟落后、知識匱乏等原因影響,老百姓在農業生產中往往會忽視土壤重金屬污染對人體健康可能造成的危害,僅從經濟、收益角度出發自主開展農業生產活動,同時又受成本、管理復雜程度的影響,對安全利用與風險管控措施的接受程度不高,不愿主動參與、實施安全利用與風險管控,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受污染農用地風險管控工作的推進。
3 云南省重金屬污染農用地風險管控對策和建議
3.1 建立農用地土壤大數據管理平臺
在云南省農用地土壤詳查的基礎上,統一匯總各相關部門的土壤與農作物調查成果,并建立相對完善的土壤與農作物(不應局限于糧食作物,應包含蔬菜、水果、中藥材、茶葉等高原特色農產品)協同監測網絡,建立土壤大數據管理平臺,實現數據動態更新,形成能兼顧預警、檢測并實施反饋的土壤質量與農產品質量協同管理體系,針對不同區域地方提出作物正負面清單,發揮農用地土壤與作物大數據在污染防治、土地利用、農業規劃與生產等領域的作用。
3.2 強化土壤污染區域人群健康風險評估研究
針對已查明的典型農用地土壤重金屬污染且農作物重金屬含量超標的區域開展基于人群健康的風險評價,結合農用地土壤重金屬污染狀況及空間分布特征,對土壤重金屬污染對人體健康造成的危害程度進行概率估計,并據此提出降低風險的方案和對策。健康風險評估不能僅僅依賴風險評估模型,還應收集區域內的毒理學資料、人群流行病學資料、環境和暴露因素等,確保健康風險評估結果科學、真實。
3.3 根據農用地質量類別劃分成果,執行農用地分類管理政策
各級地方政府應根據耕地土壤環境質量類別劃定成果,遵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壤污染防治法》《農用地土壤環境管理辦法(試行)》實行農用地分類管理。對優先保護類耕地應實行嚴格保護,在加強工業污染源治理管控的同時,管理部門應引導農戶科學施用化肥和農藥,控制高殘留、毒性大的農藥和化肥的使用,避免新增土壤污染,切實有效地保護好優先保護類耕地;安全利用類耕地,應當優先采取農藝調控、替代種植、輪作、間作等措施,阻斷或者減少污染物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質進入農作物可食部分,降低農產品超標風險。嚴格管控類耕地,主要采取種植結構調整或者按照國家計劃經批準后進行退耕還林還草等風險管控措施。
3.4 加強受污染農田安全利用與風險管控技術應用研究
安全利用措施包括農藝調控、替代種植、輪作、間作等,風險管控措施主要指種植結構調整和退耕還林還草。然而,如何通過農藝調控、輪作、間作等來實現安全利用,種植結構進行怎樣的調整可以實現風險管控,退耕還林還草應該采用怎樣的模式,因為各地污染情況不同,污染物種類各異,作物生長的條件環境差別巨大,各地的種植習慣也有所不同,所以,其他地方成功的技術難以照搬照用。各級政府應因地制宜地探索在本地具有可行性的技術方案,安排、申請專項經費或積極探索融資渠道,扎實前期調查評估工作,進行科學的、多因素的技術、模式比選,支持受污染農田安全利用與風險管控技術小試、中試實驗或示范工程,摸清技術的適用條件、實施參數,為技術推廣奠定基礎。
3.5 建立健全土壤安全利用或風險管控補助機制,引導群眾接受和實施受污染農田安全利用或風險管控
在推廣安全利用與風險管控技術時,常常會受經濟成本、管理復雜程度等因素制約,致使老百姓不愿意或無法實施安全利用與風險管控措施。各級政府應以人為本地積極探索新制度、新模式,設立專項資金,建立健全土壤安全利用或風險管控補助機制,引導群眾接受和實施受污染農田的安全利用或風險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