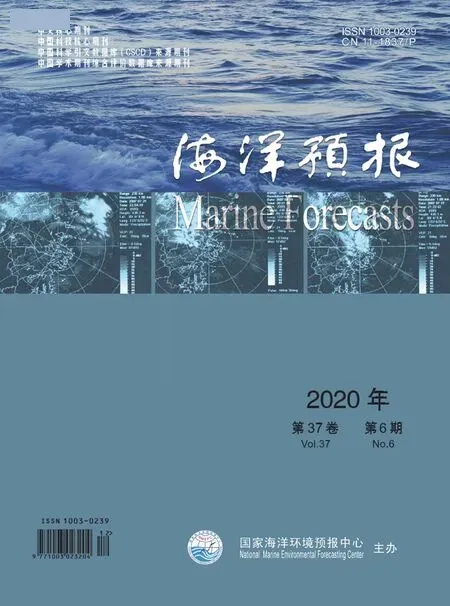浙江中南部海霧預報決策樹模型研究
俞涵婷,廖晨昕,王可欣,陳華忠
(1.椒江區氣象局,浙江臺州318000;2.余杭區氣象局,浙江 杭州311100;3.玉環市氣象局,浙江玉環317600)
1 引言
海霧是海上災害性天氣現象之一。它給近海航運、港區作業和漁業生產帶來很大影響[1]。它的復雜性給預報帶來一定的困難。在中低緯度海域,大范圍海霧以平流冷卻霧出現的機會最多,霧也最濃,成為海霧預報的重點[2-3]。海霧一般多出現在低于20 ℃的海區里,高于20 ℃時霧逐漸減少,超過25 ℃不再有霧[4]。張蘇平等[5]通過天氣研究預報模式(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ing Model,WRF)模擬得出:黃海海溫升高(0.5~2 ℃),海霧面積相應減小;升溫程度越大,面積減小的越多。在濕度較小的薄海霧區,海溫變化對穩定度影響稍大;而在濕度較大的濃海霧區,海溫變化對穩定度的影響不大。這說明了下墊面溫度、濕度、穩定度相互之間以及它們分別對海霧的影響。鄭怡等[6]對渤海沿岸的海霧分析認為:沿岸相對濕度在90%以上,近海相對濕度在80%以上,低層大氣存在逆溫層,有利于渤海海霧的生成和發展。黃健等[7]利用2000—2008 年1—5 月的資料,采用分類與回歸樹方法(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s,CART)對海霧生成前24 h 的海洋氣象條件進行分析,利用近地面預報因子,如:10 m風向和風速、1 000 hPa和850 hPa的溫度、濕度和風場等建立海霧預報決策樹模型,對不同地域海霧預報的準確率在73%以上。史達偉等[8]基于5種機器學習算法(如線性支持向量機及多層神經網絡等)對特強濃霧開展診斷,測試認為CART算法易于使用,且效果較佳。高榮珍等[9]肯定了用CART方法建立青島沿海海霧預報模型的可行性,并指出850 hPa 風向在青島沿海海霧決策樹預報模型中也很關鍵。胡波等[10]利用液態水含量和云滴粒子密度兩個參數優化了大霧估算方法,從而提高了大霧預報的準確率。
本研究通過平流霧的形成原因,結合天氣學分析方法,利用浙中南沿海海域2015—2018 年2—6月的海霧歷史觀測資料和對應的美國國家環境預報中心/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s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NCEP/NCAR)FNL再分析資料尋找海霧預報因子,計算因子具體閾值,并形成海霧預報決策樹,以期對實際海霧預報業務有所助益。
2 海霧特征及環流背景
據統計,浙江省每年霧季霧日的多少,在南北地域上具有很強的相關性,且具有明顯的系統性,即先南后北[11]。這表明整個海霧產生的氣候背景是一致的。浙中南近海霧季存在明顯的月際變化,每年的2—6月是一年中霧日最多的月份(見圖1)。張蘇平等[12]指出,浙江沿海海霧天氣形勢主要出現在入海變性冷高壓西部、氣旋和低壓槽東部、副熱帶高壓西部、靜止鋒或冷鋒前部。平流霧沒有日變化,可以維持多日。統計顯示浙江省沿海以平流霧為主[13-14]。

圖1 浙中南近海霧季的月際變化
理論上來說,海霧形成于地面偏南風并略帶風速的環境下,但從觀測實況上看,2—6 月任何風向下都有可能生成海霧,特別是在入海變性高壓后部,弱形勢場地面風一般為風速不大的偏北風情況下,生成霧的幾率反而更多(見圖2)。黃克慧等[15]提到,當背景場(一般如925 hPa、850 hPa)是西南暖濕氣流,且暖濕氣流輸送條件已具備時,不論地面是何風向都不影響霧的生成和維持。
3 研究方法與過程

圖2 一江山島2017年大霧與風向的關系
基于上述事實,由于海霧形成時天氣為一靜穩狀態,觀測數據中溫度、濕度和風場變化不大,風向、風速也難求規律;在預報上地面氣象要素的得出是基于模式產品,準確率不高。本文通過高空近地層資料探究,從模式已有輸出因子(高低空要素場)入手,通過對平流冷卻霧的本身定義推導,篩選海霧預報因子,運用CART 方法得出大陳海域海霧預報決策樹。
3.1 研究資料與數據基礎
本文將能見度小于1 km 記為有霧。選取浙江中南部大陳島海域附近二島2015—2018 年2—6 月的觀測站地面能見度和天氣現象資料進行研究。大陳島雖有近60 a 歷史資料,但多年實際研究中發現大陳島能見度觀測儀設在海拔87.2 m 的山坡頂,因海拔高度過高,大霧記錄多為山頂層云遮蓋所致,海面上實時能見度較好,觀測的大陳島大霧記錄遠大于真實海面大霧記錄。鑒于大陳島大霧記錄有誤差,本文以該海域附近站點一江山島和頭門島霧記錄為準。此二島距離較近,海拔高度都約在50 m 左右。因頭門島能見度記錄從2015 年2 月12日16 時開始,經查大陳島2015 年2 月1—12 日都無大霧天氣(大陳島霧記錄遠多于其他二島),因此2015 年以頭門島資料為準。一江山島記錄從2016年開始,之后頭門島、一江山島資料相互替換,并相應選取2015—2018年2—6月NCEP的1°×1°的再分析資料,時間間隔為6 h,通過插值方法將NCEP格點資料插值到各個站點。
3.2 候選預報因子的設計
黃輝軍等[16-17]用近地層溫差因子改進的廣東沿海海霧區域預報取得了不錯的效果。Huang 等[18]通過再分析資料和觀測資料,分析了多個預報變量,例如低層風矢量與暖濕平流、低層基本氣象要素[19]等因子作為表征海霧形成時所需的天氣形勢和外界環境。在垂直方向的溫差因子里,選取了925 hPa與1 000 hPa 的溫度差值,以及1 000 hPa 與地面2 m的溫度差值,用來反映有霧時近地層的溫度特性。研究證實了近地層1 000 hPa 與地面2 m 的溫差是有效的預報變量因子之一。本研究從平流霧定義出發:當暖濕空氣平流到較冷的下墊面上,下部冷卻形成的霧。我們用低層溫度與地面2 m 溫度的溫差值來尋找本地海霧形成時的溫差閾值,并用2015—2018 年2—6 月各層溫差值統計大霧的結果。同時,由于大霧形成需要穩定的天氣形勢,任何冷空氣的侵入[15]及近地層降水對流等新系統的入侵都會破壞大霧的天氣形勢。所以我們還需考慮大霧形成時的天氣背景:近地層的溫度結構、地面濕度、上升速度和散度等,并通過這些數值預報結果確定大霧的關鍵預報因子,并在實際預報中做出判斷。
3.3 高空氣象要素與大霧發生特征的統計分析
由于暖濕氣流經過冷地表面,本文分別選取了850 hPa、925 hPa、950 hPa、975 hPa、1 000 hPa 與地面2 m 的溫度差值;濕度是大霧形成的必要條件,選取了地面1 000 hPa 相對濕度(1 000 U)、925 hPa 相對濕度(925 U)和850h Pa相對濕度(850 U);根據天氣的穩定程度,適當的逆溫層也給大霧提供了穩定條件:選取了850 hPa 與925 hPa的溫差(T850 hPa—T925 hPa)、925 hPa 與975 hPa 的溫差(T925 hPa—T975 hPa)和950 hPa 與1 000 hPa的溫差(T950 hPa—T1 000 hPa);同時我們還選取了前后時次的925 hPa溫差(T925 hPa—T925 hPa)代表暖濕氣流本身強度對大霧的影響;從垂直速度場觀察,大霧形成后有微弱的上升運動,因此選取了950 hPa 的上升速度950vvel;大霧形成時的靜穩物理量:950 hPa 散度為D950 hPa。
圖3和圖4是根據2015—2018年資料統計的核密度圖,代表大陳航線上不同變量在有無大霧時的分布情況,縱坐標是密度,即位于此點的數據占全體數據的比例。圖3a—e 定量反映了暖濕氣流對大霧的影響,其中各個高度與2 m 地面的溫差與大霧都約為中等強度相關,各個高度與2 m 地面的溫差與大霧相關性相近。圖中也顯示有霧時比無霧時氣溫溫差向右位移了2~5 ℃,有的甚至為正值,說明暖濕氣流與地面溫度形成的溫差是大霧生成的重要因素。圖3f 是925 hPa 前后時次的溫差,它與大霧的相關性弱說明暖濕氣流本身的強弱對大霧無影響,這也更說明溫差才是形成大霧的重要因素。圖4c的相關性大于4a,說明近地層的逆溫有利于大霧形成,越低層逆溫越強越有利于大霧形成;大霧形成時需要1 000 hPa 的相對濕度基本集中在90以上,相關性為強相關(見圖4d),而大霧與925 hPa和850 hPa 的相對濕度的相關性遠弱于10 00 hPa的相對濕度;950 hPa上較弱的上升速度利于大霧的形成(見圖4e),950 hPa 上升速度與大霧的相關性高于700 hPa 上升速度。對于平流霧來說散度等物理量影響較小,不論是925 hPa還是950 hPa,散度條件對海霧的影響差別不大。

圖3 2015—2018年大陳航線不同高度與2 m地面溫差和925 hPa前后時次溫差與有無大霧的分布
4 CART決策樹算法運用及檢驗
CART 算法是機器學習中用來處理分類和回歸問題的方法[20],適用于離散型變量和連續型變量的分類。CART 決策樹的生成就是遞歸地構建二叉決策樹的過程。對分類樹來說,CART 用Gini 系數最小化準則進行特征選擇來生成二叉樹。
基于CART 決策樹算法對大霧天氣建立模型,模型的輸入變量為2015—2018 年大陳航線以上氣象要素。將之前處理好的訓練集輸入CART 算法,經過多次交叉檢驗得到決策樹。模型見圖5。

圖5 2015—2018年椒江沿海航線大霧氣象觀測要素特征診斷決策樹模型
決策樹中基本反映了前面分析的分布情況,并且更加明確了濕度是大霧形成的必要條件,沿海海面濕度需大于90才能執行該模型;其次是近地層的溫差情況;另外,低層上升速度、低層逆溫等都對大霧形成有影響。訓練集數據模型整體學習準確率為0.85。將此測試集數據運用于2019 年2—6 月的大霧數據檢驗中,成功率為0.8,模型達到不錯的泛化能力。此模型右支也相似于張蘇平等[12]的模擬結果,濕度越大時對溫度要求越低。左支則更考慮上升運動和溫差的相互影響。該模型說明了濕度是海霧出現的必要條件,而海霧形成和維持是低層相關因子相互作用、相輔相成的結果。
5 結論與缺陷
利用大陳島海域各站點2015—2018 年2—6 月的海霧歷史觀測資料和NCEP/NCAR FNL 再分析資料,通過海霧基本定義和形成所需的氣象環境條件,選取高空氣象要素對海霧預報進行分析研究。結果表明:暖濕氣流本身強弱對大霧無影響,溫差才是大霧形成的重要因素,近地層的逆溫有利于大霧的形成,越低層逆溫越強越有利于大霧形成;大霧形成時所需相對濕度基本集中在90以上;950 hPa上較弱的上升速度利于大霧的形成;散度條件對海霧的影響差別不大。利用訓練集數據參與模型建立,模型整體的學習準確率為0.85。將此測試集數據運用于2019 年2—6 月的大霧數據檢驗中,成功率為0.8。但此模型仍有一些缺陷:
(1)數據是個連續的過程:當冷空氣已下,風向突轉,霧即已消散,但此時溫度和濕度卻還沒及時降下來,數值仍高居不下;雖然經過個別人為剔除,但仍有少數出現與結論相悖的情況,會影響模型判別。
(2)由于天氣影響要素眾多,選取要素有限,并沒有選取足夠多的天氣要素來對大霧進行影響分析和判別。
(3)本文運用的數據為再分析資料,與實況有一定誤差,模型結果還需在長期實際運用中進行測試。
(4)大霧數據不夠:2 404 個數據樣本中只有283 個大霧樣本,有、無霧數據相差太大,影響模型判斷。
(5)形成大霧有眾多的充分條件,但大霧消散卻有很多充要條件。在考慮大霧預報時也需要著重考慮這些不利影響,如冷空氣的滲透即破壞大霧的穩定,強的上升速度則表示有強降水不會出現大霧天氣等。